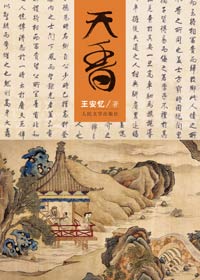天香-第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希昭从花绷上起身,四下里亮晶晶的眼睛都含了笑意,几乎开出花来。光线更匀和温润,潜深流静,这间偏屋里渐渐充盈欣悦之情。希昭想起天香园里的绣阁,早已成残壁断垣,荒草丛生,不想原来是移到坊间杂院,纡尊降贵,去尽丽华,但那一颗锦心犹在。那两个站起身,直直地鞠下躬去,蕙兰在前边推开门。院里地上花影团团,希昭走了进去。
42 遍地莲花
万历四十六年,东北边陲,努尔哈赤收复女真人各部,立国后金。开始发兵攻抚顺。抚顺守将李永芳投降,辽东巡抚李维翰派遣总兵官张承荫赴援,战死,全军覆没。边城清河,全线崩溃。自此,后金突破天险,有进发中原之势。朝廷一边紧急征税征赋,加派兵饷;一边调兵遣将,紧急起用辽东事务官员杨镐为兵部右侍郎。万历四十七年,杨镐统率四十七万大军,分四路进伐后金。开原总兵马林攻北;山海关总兵杜松攻西;辽东总兵李如柏直驱清河攻南;东南一路,由辽阳总兵刘綎、凉马佃率领,朝鲜兵协助进攻;上海人乔一琦乔公子受命游击将军,领五百朝鲜军从鸭绿江北岸宽奕口向刘綎靠近。二月天气,辽境一片冰封,连日大雪纷飞,各路兵马滞阻不前。努尔哈赤得此消息,遂定出作战计划:“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全力打击西路,包围萨尔浒营地,杜松战死,西路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则急转马头,向北而去,又打了个胜仗。东路军刘綎正行军到深河,距后金兵马所据赫图阿拉不远,努尔哈赤心生一计,举杜松部旗旌,易明军衣甲,直入军营。就在此时,乔公子率朝鲜兵迎战数十起,越大鼓河,小鼓河,堇鄂河,抵富察之野,等候刘綎、杜松会合。数日过去,无一点消息,遣一骑前往侦察,方才得知,刘、杜二部全溃!乔公子大惊,即刻改变战术,率部下转移,不料,已经重兵层层包围。边战边退,逼到鸭绿江边,又逼上滴水崖头。五百朝鲜兵尽数阵亡,乔公子亦中流矢,回顾身后尸身遍地,说一声:吾不负天子!下得马来,遥望京师方向拜三拜,坠崖自尽。乘骑名素骏,步后尘腾空一跃,跃人崖下。至此,惟有李如柏南路军得以保全,杨镐受军法处决,其余全部战死。开原、铁岭被后金占领,东北一线全面敞开,异族人的铁骑直扑中原。
乔公子死讯传到地方,上海决议建忠义祠。无论官宦世家,名绅隐逸,贩夫走卒,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张府里也出了一大份,乔公子为沪上忠烈,族人乔老爷又是张老爷生前至交,从公从私,于情于理,都有义务。张家已度过危难时刻,家道逐渐殷厚,吃穿用度而外尚有盈余。是蕙兰媳妇勤力,也是得天地时势惠顾,就当回报公益。忠义祠修在九间楼东边药局弄内,本是乔家旧祠堂。如今就在地基上重建。请画师绘了乔一琦像,供奉于正中;堂入口列石人石马两行,夹道而立;大红栋梁悬挂五色旌旗,犹如征战威势;横匾竖联不尽其数,少不了“忠”和“烈”二字。乔家人重修族谱,刻印成书,供于堂后二进楼上,题名为“藏书阁”。落成那一日,灵舟明烛,钟鼓大鸣。苏浙两地均有前来参拜者,航船泊满大沟小渠,桅帆林立。药局弄四边方圆二三里,车水马龙,人潮如涌。停课,停市,停刑,停公事,而上海寺庙,全部水陆道场,超度将军亡灵。诵经声遍起,哀哀不绝。
这一年里本还有几桩逸闻轶事,在乔公子的英雄传奇之下,不禁褪去声色。比如,嘉靖丙辰礼部郎中赵灼后人赵东曦,万历四十六年戊午科取进士,在原宅第赵家弄造园。因临河半段,就取名“半泾园”,园内多植桂树,当年刚近九月,便桂香满河,顺流而往四面八方。全城皆闻。然而却有无聊好事者,私下窃语道:此园不是吉象,因枕水之上,随波逐流,非长久之征兆!再从时局推论。女真人大胜萨尔浒,自后可说是势如破竹,虽说成化年又加筑长城,从山海关,沿运河至九连城鸭绿江,路途尚为遥远,可那异族人另有一脉,不定哪一天就渡了黄河,倒还有心弄园子玩,本就已是败象。然而,无论闲言碎语满天飞,上海似乎又兴起一轮造园子风气。礼部郎中乔炜,也在乔家弄内辟地造园子,名字就叫个“也是园”,看似谦逊,其实是倨傲,意思好比“你造得,我也造得”!不止是造园,还起庙堂。乌泥泾镇上破土起宁国寺,将黄母请进偏殿,专立黄母祠。敬一堂虽未扩建,但人数却多起来,单只一年里,皈依耶稣会就有七十二名新教民——就在这造园的造园,盖庙的盖庙,轰轰烈烈之中,京城里换了皇帝,神宗换光宗,光宗又换熹宗;改万历为泰昌,再改泰昌为天启。本来是山高皇帝远,浑然不觉,却有一变不觉也要觉,那就是,也在这一年中,到处起造魏珰生祠。那北地人魏忠贤,谁都不知道他是哪块地里的苗,刹那间四下里开花,不知道要结出个什么果子来。
接下去,天启二年,三月与十二月,地震海啸;天启三年,三月十三日地震,十六日复震;天启四年甲子科,松郡试场挤轧,文童死者十有三人,邑宰郭如闇祭文道:“人间业断,地下文修;前花未报,后果须收”——此为人祸,天灾却也不消停:二月烈风暴雨沙尘,白昼如黑夜,整整三日;五月淫雨,禾苗皆淹,大饥;七月地震;十二月复震!就好比天怒人怨,惴惴不安。免不了烧香拜佛,投了和尚投道士,耶稣会又有无数人受洗皈依。过了一年,到天启六年,祸事终显端倪。
这一日夜间,畏兀儿忽到张府,府上正操办灯奴的婚事,都以为畏兀儿是来道贺。灯奴这年二十岁,十七岁通过童试,人泮。因怜他自小无父,家世又清明,便将其父张陛生前所任廪生的额,配给了他。于是,家中又有个廪生,挟着书包,穿青布衫袍,去府学点卯。但这廪生非那廪生,灯奴至少要比父亲身长半尺,肩厚背阔,气血旺盛,是像外婆家人。远近都有人来问亲事,凡有意作亲的,必取来这家女儿的针线,由他母亲过目。蕙兰不禁好笑,是娶媳妇,又不是收徒弟!可也挡不住世人们的心愿。纠缠了整一年,最终定下乔家族中的女儿,少灯奴两岁。倒不单是女孩儿针黹好,也不止模样好,是因她从小失怙恃,随祖父母长大。蕙兰动了恻隐之心,觉着两个孩子,一是半孤,一是全孤,不容易长大,又都长得齐整周全,是一对同命人。灯奴的婚事,李大范小都来帮忙。扫房子,挂幔子,杀猪宰羊,烹酒调酱。如今,学绣的人有十数,东屋挤不下,移到厅堂,只留一隅作待客用。东屋就做灯奴的洞房。
入夜,蕙兰与李大在灯下拣花生红枣。喜期来临时撒帐用。蕙兰忽想起一件事,问李大:刚嫁入张家头一年除夕。守岁讲故事,说张家人身上有记认,要我们回房里去查!后来家中出了多少事故,也没认真搜寻,如今,张陛作古那么些年,灯奴也要娶媳妇,却还不知道那记认是什么!李大说:还不赶紧的,这一夜过去。灯奴从此就另有同眠共枕人,再近不得身了!蕙兰说:李大也说个大概方位,如此满身上下地查,都要查到天明!李大说:往腰底下查!蕙兰真就起身要去,李大却笑起来,这才知道其中有诈,逼着李大快说。李大好不容易不笑了,说:脚趾头有三节!蕙兰也笑了:哪一个的脚趾头少一节了!就在此时,畏兀儿敲门了。
门一开,畏兀儿闪身进来,蕙兰刚要说来得巧,畏兀儿却径直往里走去。蕙兰这才觉着有事,平素若不是三邀四请,他必不踏人院子的。今晚上,却是畏兀儿在前引路,穿过天井夹道,又走过院子,直接推开蕙兰屋的门。蕙兰要点灯,畏兀儿止住了,两人就站在暗影地里,幸好有月亮,从窗户投进来。畏兀儿的眼睛灼灼亮着,他说:姑娘——因是阿暆的朋友,所以还是旧称呼,姑娘,你阿暆叔出了点小事。蕙兰心里重重一沉,她晓得,倘是畏兀儿这样举重若轻的人,说 “小事”,就必有大碍,哑着嗓问:多半与东林党有涉!畏兀儿强笑一下:姑娘猜对了,东林书院遭祸,走的走,抓的抓!阿暆叔呢?蕙兰急问道。畏兀儿说:入狱是入狱,但据说未上镣铐,就还有救。蕙兰又问:在哪一地的大狱?北京!畏兀儿答。蕙兰不由一顿足:叔叔怎么跑北京去了!接着想起多年前那一夜,也是这么出其不意忽然而至,之后已有七八载没有见过,也没有一点音信。或许,就是要远行,所以专来看一眼灯奴,如今灯奴就要娶妻成亲了。蕙兰不由流下泪来。畏兀儿安慰道:姑娘安心,这就北上。探索路径,看有无法子早日脱身……蕙兰听到此。二话不说,转身进里屋,也不点灯,凑了月光,从箱底掏出两整封银子,再添几件金银钗环,又找出数幅天香园绣品,用一张包袱皮裹好。待要出去。又回来,从柜子角落摸出一个银锁圈。是灯奴幼小时,他舅叔公不知从哪个野地里寻来给戴上的,后来得着九尾龟石头,蕙兰穿了根红线绳替他系上,换下了银锁。倘他舅叔公能看着,抵得上见灯奴一面。蕙兰将东西交到畏兀儿手上:阿暆叔就拜托畏兀儿叔叔了,若能见面,就将银锁给他,告诉说,灯奴很好,已经娶亲!畏兀儿将东西收好,转身出门,又照原路出院子。走后天井,如来时一般闪出。就见一骗腿一腾身,胯下突跃出一匹白马,一阵风似地出了巷子。
申府里对阿暆的事浑然不觉,一半是真不知,另一半是佯装不知,知道又能如何?到后来索性就不提“阿嗨”这两个字。有人问起,便说在外游玩,倘有多嘴多舌的人来传话,则以诽谤白解。申柯海早在阿暆出事前,天启三年便谢世,享寿八十,这也是他的福分。免去多少世事干扰。小绸晚一岁,也是八十终年,又少去一个操心人。余下的,或是不管事,或是自顾自,外面看是一家,内里其实已经各过各的。院落与院落间,因疏于往来走动,回廊过道渐渐颓圮,残砖烂瓦堆垒,又成隔断。那大厨房以及厨房前的小码头也久不用而废,塌下水里。三重院有两重是不住人的。两处楠木楼还算完整,在一片颓败中尚留些生气,却又显得突兀,而且不可靠,早晚都会被瓦砾堆掩埋。阿暆的母亲落苏,是个宽心人,总说阿璇在外游学,自己竟也信了,并不多虑,自在门前开了一畦地,种些菜蔬瓜豆,其中真的就有落苏。得了收成,东邻送送,西邻送送,也够一大家的日常食用。这一畦菜地,生出一股怡然自得,不把落魄当回事的样子,颇合乎申家人的性情,就好比紫藤一类的花,开相好,败相也好。
惟有蕙兰知道阿暆的事,为他日不安,夜不眠。畏兀儿一去不回,无一点消息。倒是坊间时有传说,东林党如何受魏忠贤残害,有六君子为东林之首,在狱中受杖,死去活来。说得极多极详的是一名燕客,在京师四处活动,与衙门里的马夫、狱卒喝酒寻欢,混得透熟,得以潜入监房,抚慰囚人;又出银子行贿,卸镣解铐,或者送些酒菜;然而,终是不能解脱,六君子遂毙命……蕙兰听得心惊,深恐六君子中有一个阿暆,因那燕客形状颇似畏兀儿。传闻所说六君子又各不同,今日姓张,明日姓王,最齐全的有道是:“应山杨大洪,嘉善魏廓园,常熟顾尘客,武定袁熙宇,桐城左浮丘,南城周衡台”,听起来确凿得很,蕙兰的心略放下一些,可是叛党多是隐名,谁知道真身是谁呢?况且,魏忠贤一个不放,即便是在六君子之外,又能有多少活路?愁绪就又上心头。时间就在忧患中过去,灯奴娶妻生子,四世同堂。绣学扩张几许,戥子与乖女已成师傅,送女都拈针引线了。所以,忧患之外,还有欣喜纷至沓来。悲悲欢欢,又换了皇帝,改了年号。
崇祯二年春,申府前方浜上行来一艘船,缓缓靠岸,下来一个人,长身瘦面,着布衫,足上一双麻草鞋,随身一柄雨伞。到申府门前,不认识似地打量一下,门上的竹签子断的断,朽的朽,铁钉子也锈完了,门脚下生了青苔,显见得长久不开。于是沿烽火墙绕到侧面,那里有一扇小门,开着,径直走进去。看来是一位熟客,原来是阿暆。
阿暆回来,从此深居简出,或在屋里看书,或帮母亲种菜。偶尔过浜对面,去到天香园旧址。九亩地上的甘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歇种,断垣之上,却建起一排兵营,驻进崇明水师。穿了兵服的小小子,就地挖灶起炊,闹得遍地烟熏火燎。园中央开出一片方场,铺了细沙,供操练列队。阿暆立得远远地看,听那口令声清泠泠传过来,脚步声则齐刷刷,有一股清新矫健。歇息时,散了队,有小兵速速地跑来,从地上草丛中拾了什么,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