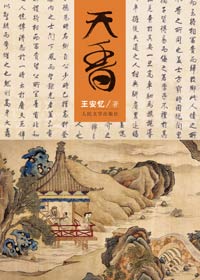天香-第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都是世间物,不难认得的。蕙兰问:婶婶怎会有罗汉图?并不见吃素念佛。希昭说:我当然是个俗人无疑,但在杭城家,巷口有一座庵子,名“无极宫”,小时候常去玩,认识些师姑;其中一名出身好人家,学过书画,很投缘,出阁前夕,送一本册子来,就是这本罗汉图;据蒙师吴先生说,像是从唐卢棱伽《罗汉图》摹来,却又有宋李公麟笔法,扫去粉黛,以白描见长,或可临作绣本。
至此,蕙兰已望而生畏,畏的不止是针线,还是此后所要担生计,就从这里开始了。希昭说:我也帮不了你,你没看见?这一家上下,凡姑娘媳妇,都在赶着绣活,衣食住行全凭借它。蕙兰抬起头,望着婶婶,脸上无一丝笑,认真道:放心,既开弓,便无回头箭,决不辜负婶婶。希昭倒笑了:怎么像发愿?蕙兰自幼心灵手巧,有样学样,如今又有长进,只能越来越好,哪里有辜负的道理!蕙兰还是正色:有一句话我要说在前头,任凭蕙兰如何用心用力,终也不能与婶婶同日而语,所以,务必请婶婶包涵!希昭说:这也忒没志气了!蕙兰说:不是没志气,菩萨造人,塑好的泥胎,吹一口气便活了;我是塑胎,婶婶是吹气,那一口气是天派给的!希昭不禁也有些动容:无论你说得怎样,也是灯前影下,一针续一针,一行接一行。两人静了片刻,再低头看册子。希昭说:我也没绣过,但觉得,虽然人间相,毕竟是罗汉,有异禀的,还需庄严;不用色,只用黑、灰、米黄、米白,针法也要简略,多用接针滚针勾线,工整大方,才是佛像的要义。
如此。蕙兰在娘家住了三天,将罗汉图绘成粉本,携回家去。家中大人孩子正翘首以盼,尤其是夫人,见到人,竟红了眼圈。蕙兰这时发现,夫人憔悴许多,鬓发都已飘白。这一段日子,子丧、夫病、长子一家一去不回,倘不是有过人的意志,万不能挺住。然而,也再经不得一点摧残了。接下去的时间还算平和,阿暆的银子支撑着,又有两家送来润笔,是老爷病前所做的贺表与谢表,忙乱中早忘了,可谓意外之喜,就又接续上。李大和范小全心打理内外事务,夫人日夜侍奉老爷,蕙兰开始绣活,灯奴在院里和兔子玩。范小在桂花树下盖了个兔舍,砖砌的墙,架了木梁椽子,铺瓦爿,开门窗,莫说兔子,都可住得人。小兔子已成大兔子,因养得好,毛色纯净,蓬蓬松松,在灯奴怀里满满一大抱。就是尿臊味重,家里院里全是,灯奴也是一身腥,如何洗也洗不掉。这院子里有了畜类的气味,倒显得有生机,不那么冷清了。只是蕙兰生怕染了绣品,就不让灯奴挨近,晚上由李大带了睡去,她趁此还能多做几针活计。
蕙兰闭着房门,燃起香,镇日埋头在绣绷上。李大难得推进看一眼,见素色缎面上是和尚,盘腿坐于松下溪畔,不由惊一跳,说:难道是在闭关?蕙兰回道:我要闭关,叫李大这一撞门,不也破了戒?李大就说:你再想做姑子也做不成,上有老下有小,别指望脱个清静!主仆二人说笑几句,蕙兰方才告诉说,是叔叔从寺里找来的针线活计。李大挨近了细看,咂嘴道:这是什么?真舍得让那些腌臜和尚坐啊,造不造孽!蕙兰赶紧止住:李大莫胡乱说,出家人怎么是腌臜,冒犯菩萨现世报!李大看她一眼:听说亲家爷爷半路出家做了和尚,难道是有慧根,还又传代?蕙兰笑起来:我都没见过我爷爷,看那一家人,哪里像有一点觉悟?我爷爷止不过是个异数罢了!现如今手里做寺里的活计,菩萨就算是衣食父母,自然要敬着了。李大伸手在蕙兰额上点一下:这就叫作临时抱佛脚!蕙兰来不及让开:李大手上有尿臊味,别沾了我的绣活!李大说:菩萨是普济众生的,无论赶脚的还是苦力,一视同仁,还忌惮尿臊味!说归说,手还是收回去。过后,与夫人说起蕙兰绣佛的事,不免担心:这么年纪轻轻,守一盏孤灯形影相吊的,到底叫人不忍!夫人低头想一时,说了句:人自有天命,由她们去吧!李大知道,夫人说的“她们”里,还有张陞媳妇。自她回娘家,张陞跟去后,直到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方才来家看过一回,替故人放了河灯当晚就走了,借口这边房子没收拾,墙脚都生霉,潮得很。临走前,张陞期期艾艾流露出点意思,亲家那边有心招张陞入赘,与大舅子一同经营豆米行。夫人硬压着性子,声音都哑了:你和我说没用,去和你父亲说。手一指里厢房:你父亲就在床上躺着呢!张陞再不敢出声,赶紧跨出门,门外的轿子里,等着他媳妇,晓得没办成事,揭起来的轿帘一摔,打在张陞脸上。
阿暆过来看灯奴,只见灯奴大半个身子扎在兔舍里,往外拖那白兔子,身后球着黑兔子,三下里乱成一团。阿暆上去将人和兔撕扯开来,白兔子一转身又往兔舍里钻进去。阿暆矮下身子一看,兔舍里不知什么时候,扯了兔毛做成一个窝。再看那白兔身子沉重,就知道要娩小兔子了。将灯奴驱开,灯奴已是一身兔毛,腥得呛人。阿暆一笑,往灯奴后脖颈摸一把,摸到那银锁圈,缠的红线绳,本就是浸透泥汗,如今又裹上一层新的,上了釉似的。扯起灯奴去蕙兰屋,刚推门,里头就传出声音:别让他进来,膻!趁阿暆一彷徨,灯奴脱了身,回到兔舍跟前,好在范小赶到,死把着门,阿璇这才放心进屋。
蕙兰已绣成两幅,阿暆不甚懂佛经,叫不出名,只见是一个和尚傍着溪流席地而坐,腿边趴着个小沙弥,倒有点像灯奴。再一幅,也是和尚,坐在石上,正展开一卷经,身旁站一个人,披盔甲,头顶一簇缨,手持法轮,应该是沙弥,可又像送信人,和尚手里持的就是家书。画面疏落清淡,细部却惟妙惟肖,既是佛道,又是人世间。蕙兰停下针,等叔叔批点,见沉默不语,便不安起来,问:是不是有俗气,不合寺里规矩?阿暆则说出与李大一样的话来:怕的是他们不配!蕙兰吁出一口气:这就不怕了!阿暆又说:出家人清心寡欲,粗衣淡饭的,大可不必如此精致求工,忒费神劳力了!蕙兰就说:我恨不能更好却也不能了,“天香园绣”誉满天下,要砸在蕙兰手下,从伯祖母到婶婶,一律饶不了,就也顾不上和尚不和尚的!阿暆赶忙说:砸不了,砸不了,这不,“天香园绣”又添一品,之前有谁绣过佛?蕙兰笑了,又收住,抿着嘴,低头拈起针来。这一幅绣的是麒麟,回头向上,所望之处,也是一罗汉,炭笔勾了形状,未着针,好像刚下凡来就要现身。麒麟通身白色,须尾与脚爪是黑,黑白对应,倒又有一种绚烂。阿暆说:寺里原本打算过年后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辰日用这批蒲团,看起来赶不及了。蕙兰“哦”一声,又停下针来,怔忡着道:拚了不吃不睡,到四月能绣成八幅,已经了不得,还要缝、填、滚、缲,最终做成蒲团。说着就急躁起来,怪自己鲁莽,冒失接下活,要误大事!阿暆劝她尽管宽下心绣活,由他到寺里与畏兀儿交道,四月初八交八个,另八个下一年除夕前交到。蕙兰问畏兀儿是什么?阿暆便将畏兀儿的来历说了一遍。蕙兰说:叫这样的名,怪好玩的!停了停,对叔叔说:就和畏兀儿定下,四月初八交一半,除夕交一半,再快也不能了。阿暆答应了要往外走,蕙兰又叫了一声 “叔叔”。
蕙兰说:能不能向家里支个人,帮着打些下手?阿暆不由为难了:家中闲人是不少,却是什么也不会,凡会点什么的,则忙得披星戴月,真还支不出帮得上忙的人!蕙兰说:我娘房里新添一个丫头。叫戥子,算我借娘的,用完就还!阿暆答应带话给蕙兰娘,蕙兰又补了一句:只借半天,下半天来。傍晚就回。阿暆禁不住一笑,晓得是为了省一顿饭,又觉凄楚,这一家果然是到了量米下锅的日子上,却不得不佩服蕙兰义气,为难时不离不弃。只隔一日,戥子就自己来了。上回在母亲房里,被差遣得来回往互,没看真切,此时在跟前站定,才见出这丫头还小得很。个头都没长齐全,脸黄黄的,五官还在混沌中,显不出美丑。身上穿的是蕙兰小时候的旧衣服,倒也干净。双手抱一个篾编的针线匣子,也是蕙兰在家时用旧的。但凭她能自己摸到这边来,却是够机灵和大胆的。蕙兰带她进屋,先让洗干净手脸,再穿针引线,将前一日裁下的绸缎片,缲上边。蕙兰缲一行给她做样子,再看她缲一行,见她拿针的手势挺秀气,就晓得是做过针线的。蕙兰不由多看几眼,又看出这丫头长了一双好手,虽还是孩子手,和她的脸一样黄和瘦,但已经显出匀长的手指头。干的是粗活,却没有一点趼子,指甲也整整齐齐。拇指和食指一提针,小指一翘,挑着线,扯直了,不松也不紧。蕙兰放心了,兀自回到绷上绣活计。一炷香燃尽,起身换香,才发现屋里多一个人,这才觉着戥子的静。再去看她的活,已缲了一片半,针脚长短深浅一律齐,毫不走样。窗户向东,日头此时去到西边,光就弱了,平下来。但因是晴朗的好天气,足够照亮,连线的毛头都清晰可见。窗外听得见灯奴的叫喊,原来大兔子已娩下四个小兔子,满院子滚绒球。桂花开了,沁甜的香里掺了兔子的尿臊,自家人惯了,不觉得。外边人猛一进来,以为是庄户人家。兔子进窝,门插上,灯奴又吵着要范小堵黄鼠狼的洞,喧嚷一阵子,天色暗了。蕙兰说一声:回吧!戥子就立起身,缲好的叠起放一边,没缲的放另一边,又将线头线毛撸起来,揉成球,案子上便干干净净,抱着针线匣,走了。
下一年的四月初,阿暆带着八个蒲团去到龙华寺。畏兀儿见了都不敢接,怕玷污了。那拖延的八个也不催了,只说慢慢绣,不着急。带阿暆到账上领了银两,一刻也不耽误的,阿暆立时送去张家,刚好接续上抓药和过立夏节,还有李大和范小的工钱。这一年。灯奴已满三岁,兔子生下好几茬,送的送,卖的卖,灯奴的热头也熄了火,换上一只大花猫。本来是让睡兔舍里的,却偏要灯奴抱着睡,兔舍腾出来,做了李大的鸡窝。院子里叽叽喳喳遍地开花,全是黄、黑、白的小绒球,脚都插不下去。
36 戥子
蕙兰的母亲是个笨人,所以戥子的针线就不能是她教的,那又是从哪里学的呢?姐姐们。戥子上面有三个姐姐,大的二的都嫁人了,三的自小在彭家做丫头,长大后,就配给彭府上一个杂役,也嫁了。本来,戥子也要走这条路,可是不等她长到嫁人的年龄,做父亲的患赤痢,一昼夜便拉死了。母亲带着底下两个弟弟改嫁,继父不肯收她,只得由三姐带去。先在彭家灶火间里打杂,后来就进房里,替奶奶姑娘做些贴身的活,然后又被蕙兰的母亲要走,到了申府。
姐姐多,就有一般好处,总是针啊线啊,花儿朵儿的。贫寒人家,纵使没有绫罗绸缎,缝补连缀的活却少不了。女儿家都是爱美的,能将补丁做成一朵花。父亲做过几日买卖,生四的那一年,在市面盘下个铺子,生意有兴隆的迹象,巴望生个儿子,不料又是个丫头,取名叫戥子,是称银子进财源的意思,又是 “等”的音,表示等着生儿子的决心。到了下一年,真等来个儿子,可买卖却不济了。货接不上,要就是货交付了,却收不回钱。不得已,便关了店,将铺子又盘出去,回到肩挑手提,串街走巷,第二个儿子却又来了。世人看来,就是福分浅,有家业没儿子,有儿子没家业。想不到还有更不济的事,索性一命呜呼归了西,连儿子都姓了别家的姓。
到申家时,戥子十二岁,虽然年纪小,经历遭际却抵得上一个大人还多。本来就是家中最不疼的那一个,然后到姐姐姐夫家,即便自己亲戚,也是寄人篱下。还要做使唤丫头,做了这家又做那家,真是够她应付的。她还没长熟心智,也没有爹娘教,只守着一条,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此,以不变应万变,都顶下来了。也是自小看人眼色惯了,还没开口,已经知道让做什么。看起来有些木讷,是变故给吓的,生性里还是有一股小聪敏劲。刚到彭府时,多少吃的用的,从来不曾见过,却也没有打碎过东西,或者伤了手脚。再从彭府到申府,又是多少不相同,也没有搅混过。走了这两家,都是沪上数得着的大户,到底长见识,遇事更加不惮畏,木讷里倒有几分从容了。小心眼里,会将这两家作比较。彭家有排场,规矩也大;申家不拘礼,却糜费些。做仆佣,照理是乐意不拘束的主子,可是在俭省人家出身的戥子,申家的随心所欲却让她不忍,以为造孽!今天的百宝千珍,明天就弃之如敝屣。彭家也豪奢,却还有长性,看起来也像是底子厚一些,就沉着,反不那么张扬,像是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