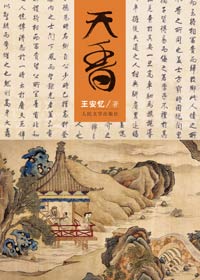天香-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绸心想,这不单是负气,也是一股心志吧,好似说:谁弃下谁啊! 众人们正赞叹不已,蕙兰忽看出一个疏漏,那就是绣画的落款为“武陵绣史”,而非“天香园绣”。人们其实早已看见,只是嘴上不说,蕙兰一点破,不禁都有些尴尬。停一会儿,还是小绸解了围:这仅是四开中的一开,待四开全绣完再题款也不迟。蕙兰“哦”一声明白了。
希昭来到绣阁,多少有些拘谨。素来心气傲,和妯娌婶娘无甚多话。绣艺上面的事,总是多看少问。与闵姨娘还和谐,但闵姨娘本就是个寡言的人,两下里也说不起来什么。这一回,阿潜没一句交代地走了,人人都说阿潜不好,没一句嘲笑她的,反而事事待她小心。可那是别人,自己呢?不说伤不伤心,单是颜面也伤得够呛,就更缄默了,也与众人更生分。惟有一个人,相处起来称得上自如,那就是蕙兰。蕙兰这年十一岁,半大不小,在别人家可算作大人,在这家,一家都是孩子似的,就是个极小的人,说话行事出自天然,没什么顾忌。就好比看“昭君出塞”绣画,问落款的事,也就她问得出来,因不知其中人事的曲折微妙。正是如此,希昭对她也无防备,双方都可直来直去,倒格外省心。这其实只是一重原因,另有一重,也是更要紧的,就是这一大一小两个人,挺投缘的。
蕙兰出生时候,正是天香园绣扬名天下,申家凡是女眷,都必学绣。蕙兰几乎一下地便摸针,是在绣阁中长大。申家儿女,总要读书,蕙兰也读过《三字经》,还听讲过《烈女传》,仅此而已。对读书始终不开窍,前续后断,这一项,随她妈,都有些混沌。可一旦到了花绷上,对着丝线绣针,顿时生出慧心,原本酱一般的脑筋,此刻一清二白,这一点就和她妈不像了。她妈是一路蒙到底,她却是蒙塞中忽开一隙,透进光来,分外明亮。采萍小时候用过的针指,早早就传到她手里,做了她的玩意儿。在绣阁中,往来都是女眷,穿花戴朵,蕙兰眼睛里就尽是姹紫嫣红。小孩子总是喜欢抢眼的颜色,难免俗艳,就好像品味浅的人口重。渐渐地,有了鉴识,清雅下来,可时不时地,还会冒出村气,她就是脱不了个乡下丫头。长相也是,丰圆的脸颊,眉眼浓浓的,鼻梁略平了些,鼻尖却略翘起,就是个俏皮的乡下丫头,其实也是像她母亲。大家子的人多少有些村气,是不更世事所至,别一种的娇贵。也是这点村气,她还和叔叔阿施很好。说到底,没有和她不好的人,只是有几个格外好一些的,比如阿施;再比如,如今的希昭。不过,和阿施玩在一处,还是个孩子;与希昭结好,就脱去稚气,有些初长成人的心思了。所以,虽然是两辈人,但更接近闺密。
背地里,蕙兰问过希昭,叔叔阿潜如何出走的,也只有她敢问。希昭说:小孩子别问大人的事。她不敢再问,兀自叹一口气,希昭好笑道:叹什么气啊?蕙兰道:我为婶婶不平!希昭更要笑:不平什么?蕙兰说:其实叔叔不如婶婶聪敏,本来就亏欠婶婶,不好好地过日子补还,这一走,再也补不回了!希昭不由收起笑,定定地看这丫头一眼,这回真看出她是长大了,虽然形容依旧是个孩子,可那眼睛里的神气,却相当正经懂事。心里暗暗惊讶,嘴里说:他走他的,谁稀罕!蕙兰说:婶婶心里还是有气。说话如此直断,倒不止是小孩子口无遮拦,还是出自心底纯良,一无芥蒂。希昭倒顾不得骂她,好奇道:我心里有没有气,蕙兰怎么知道?回答是:婶婶自己说出来的!希昭更奇怪了,她又何时何地说过?蕙兰眼睛直瞪瞪望着希昭,一点儿不躲闪:婶婶绣画上不肯落“天香园”款,就是有气!希昭心里一动,依然辩驳:并不是因你叔叔走才不落款,原先也没落的!蕙兰执意道:原先是原先,现在是现在!希昭不由恼起来:和你说你怎么不信?你可以去查!蕙兰还是说:查不查都一样!希昭气急道:小小年纪这么武断,一根筋的,我不与你说话了!蕙兰眼里含了一包泪,住了嘴。两人都不说话,各自走开去。僵持几日,当然是蕙兰先找希昭,一来是辈分高下的缘故;二来还是脾性所致。
小绸在旁冷眼瞅着,就要想起当年她和镇海媳妇,也是这么好好坏坏,吵是她们最凶,却又是她们通款曲。镇海媳妇一走了之,留给小绸的那块空,怎么也补不上。一空几十年,故人的相貌已经模糊,可那空还在。阿潜出走,不过是将那空再扩一扩,不是新鲜的创痛,所以小绸还过得去,倒是更为希昭难过。希昭和蕙兰好,也让小绸觉着安慰,这一大家子里总算有个人亲近,就不至太孤单了!就像当年众叛亲离的小绸,有个镇海媳妇。
不几日,蕙兰来找希昭说话,有言道,老天不打笑脸人,希昭就也不好太拒斥了。蕙兰要说的是希昭绣画的第三开:苏李泣别。蕙兰问:男人家家的,怎么也像是妇人一般,儿女情长?希昭就说了:男人们的朋友都是自己选下的,可说千里挑一,万里挑一,不像妇道人家,所遇所见都是家中人,最远也不过是亲戚,在一起是出于不得已;在家中又不过是些茶余饭后,针头线脑,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故,老话说,危难之际见人心!又说,剖腹明志!家里头那点儿破事,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人家苏武李陵在塞外异族人那里,单是听听彼此乡音就动心动魄,再莫要说天寒地冻,山高水远,既是客边,又是敌中,有多少困苦,结成同心,一过一十九个春秋!一朝分手再无来日,怎么不叫他们痛断肠?蕙兰听了,若有所思,道:婶婶说男人同心我也信了,可是女流中也有肝胆相照的,听家中人说,大伯母和我死去的祖母就是一对知己。希昭说:那就要有非凡的缘分,比夫妻还难得!禅家说,修百年同舟,修千年共枕;要我说,女子间结金兰谱怕是要修万年也未必成!蕙兰又问:我和婶婶可算一对?希昭嗤之:我与你不是一个辈分上的,如何结得兄弟,你也太过妄想了!蕙兰认真道:既是前缘,就与今世的人事无关,是另起一路。希昭倒驳不了她,只说她荒唐。蕙兰又说:那李陵既是与苏武情深,为何不跟了他一同归汉?希昭说:连这个都不知道,苏武是人质,李陵却是降将,回不去!蕙兰说:有什么回不去的,上一回是汉降匈奴,这一回是匈奴降汉,不就两清了!希昭笑她糊涂,国与国之间,哪有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蕙兰却不服气,说:那李陵一定另有回不去的隐情,比如已有妻室儿女,这才断不下的。希昭不觉叹口气:妻室儿女有什么断不下的?这是万事万物中最轻贱的一桩。蕙兰说:世上也不全是叔叔那样的——希昭气恼道:怎么又来了?蕙兰想掩口也来不及,直着性子接着说:婶婶为叔叔生气,不如在绣画上头大喇喇地落个天香园款,将来传到园子外头,说不定叔叔看见,臊死他!希昭一转身,又不理她了。再下一日,蕙兰却来邀希昭一同买豆腐。希昭不去,到底经不得蕙兰一步一趋地跟着,甩也甩不脱,只得去了。
两人挎着柳条儿编的篮子,不像买豆腐,倒像采花。袖笼里揣着小荷包,里面装了十来枚金灿灿的隆钱,叮珰作响。乘着一领敞轿,往大王庙去了。来到“亨菽”,见门前已经停了一顶轿,蓝布轿帘上绣着暗花,晓得是位夫人的轿。店堂里一团白雾,又暖又潮,伙计们忙着往里端新}}{的豆腐。氤氲中,果然见有一位夫人,身量高大,仪态端庄,着藕色衫,紫花裙,披云肩,戴遮眉勒,素雅沉着,看来不是寻常人家。身边随一妇人,虽是仆佣装束,也十分干净简洁,托着瓦钵,与阿唠交割豆腐和铜钱。那夫人不说话,只在一边看,听见蕙兰一声“买豆腐”——亨菽里多半卖的人不吆喝,买的人吆喝。夫人转过头来,眼睛一亮,嘴角掠过一丝笑,没有停留,在头里走了。走到店门口,又回头看一看,这才迈出去,上了那顶蓝布轿,直向西南三牌楼方向去了。
夫人住三牌楼新路巷内一座宅院。宅院不大,前后两进,院子里栽一株梅花,一棵银杏。人口也不多,主仆总共七八个。主家姓张,北方人,祖上做过正三品的官,鼎革之际迁来上海,家族已经零落。如今几十亩薄地,百来卷诗书,一线香火,勉强可称小康。近日里,渐有些兴起的声色,就是他家两个小子,张陞和张陛,年前二月里双双通过县试,四月,又通过县试,再过院试。这年,一个十六,一个十四,人称兄弟两秀才。那大的张陞,早已说定一门亲,寻常市井人家;这小的,却还没有。自取了生员,多少人家来托媒妁,无不说得天花乱坠,夫人只是听,不同答,心下的主意是,定要亲选亲定。一来是对小儿子格外溺爱些,二来多少也是懊恼大儿子的亲事操之过急了,要在小的身上补回来。早听说大王集上开了一爿豆腐店,取名“亨菽”,就觉着有趣。再听说是申家大少爷的店家,更生好奇。申家是上海出了名的大户,不止殷富,还因为家风独特——男人们都喜欢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往往一事无成;女人们的绣倒成天下一绝,闻名四方,人们多称“阴盛阳衰”。夫人却以为这家人有性情,就比如“亨菽”豆腐店。张家离开仕途多少代,染了些清士的脾气,赏识散淡悠闲的人性。张夫人自己又是巾帼中的英雄,都没裹脚,家中大小事由她做主,更不以“阴盛阳衰”为怪。一旦听说“亨菽”的店主有个年将及笄的姑娘,不由就动了心思。私底下将申家的亲缘关系理了理,就知道女孩儿的外婆家是彭府,又是上海一门赫赫大户,比申家还有渊源,老爷正在任上。张夫人并不打怵,反倒激起雄心来,想,各往上数三代,申家彭家,还有张家,大约平起平坐;再数三六九代,说不准就是张家坐着,申彭两家站着。上海人家多是经不得数典,风气新,其实是没根基。所以,论家世,张夫人是不怕的。弱就弱在当下,境况确实寒素了,然而世事难料,张隍和张陛照这般精进,前途当无可限量。想到这里,张夫人就有了底气。她独自乘轿往亨菽去过两回,看招牌上的字写得如何,店主的仪态规矩如何,第三回,带了佣妇来打豆腐,凑巧就碰上了姑娘。
。
这姑娘比传说中显得年幼,行动举止还像个孩童。张夫人倒格外多看了同来那个媳妇几眼,暗叹是个人才,气度很不凡,不动声色,却令人不由瑟缩起来。倘是她,张夫人断不敢娶回家的,于是反觉得那姑娘形容天真,与张陛恰是一对。回来之后,不几日便遣媒聘,这回却是让张老爷出面,因请的是杨知县。张家与杨家祖上通好过,称得上世交,但因一方时运上升,一方则平平,为避免攀附的嫌疑,就淡淡的。几年前,杨知县退官回钱塘,张家才放开些拘束。捎了书信去钱塘,不料,杨知县亲自来了。杨知县的大媒,自然没有不成的道理,申明世做主,将蕙兰定给了小童生张陛。一对金童玉女,众人都觉着十分有趣。蕙兰再要与希昭拌嘴争执,希昭就问:“七月亨葵及菽”,下几句是什么?惠兰自然背不出来,希昭背给她听:“八月剥枣,十月穫稻,为此春酒”——什么酒知道吗?惠兰傻傻地摇头。希昭告诉她,是喜酒!停一会儿,忽地悟过来,脸刷一下红了,狠狠丢下一个白眼。
28 沉香阁
万历二十七,乙亥年,七月,先是城外,无风的天,却有风声回响,一夜不息。紧接着,城内也起呼应。不二日,城内外连成一片,啸声遍地,此起彼伏,绵延不绝。便有流言,说是鬼哭。淞嘉这块地方,原是水域,积沙而后成陆地,其下有多少溺毙的性命,可说是白骨堆成的。到七月十五盂兰盆会这一日,地方绅士集钱放焰口,办超度;从灵隐、宁海等名寺请来高僧,焚香颂经;又有伶优扮成饿鬼,脸用圭粉涂得惨白,血盆大口吐出一蓬一蓬的火;还有扮成目连的,以武生装束,披盔戴甲,佩剑持枪,也画了脸,是红白二色,在集市上巡游。到了夜晚,凡河边桥头都是卖灯的,用蜡纸做荷花底座,芯里点一支小烛,放在水上,任其顺流而下。一时间,成千上万盏河灯下了水。上海本是水网纵横,如今全成了灯河,就像天上银河落下人间。岸上无数人追着河灯跑,那灯闪闪烁烁,挤挤挨挨,到了河岔交汇的地方,就要拥堵一时,然后又一并突破,几成汹涌之势。最终分成两路,一是方浜。一是肇嘉浜,分头浩浩荡荡向东。河道宽起来,流速加剧,人群渐渐追不上,落在后面,只见那两路河灯,一从玉带门益庆桥下,一从宗朝门蔓笠桥下,奔流过去。从此,鬼啸息止,城内城外再无异响,终于安宁下来。
然而,人们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