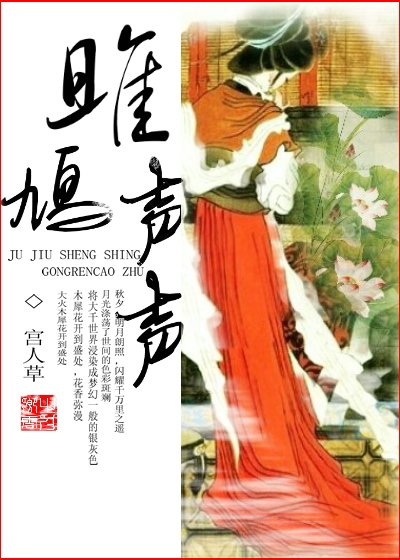杜鹃声声-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过是借了你的权来谋点儿小名,要说成就感,怕在你那里贻笑大方!”我回头看他,突然想起一事,便问道,“我都忘了问你,那个小镇长,你怎么发落的?我只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们?认识你倒也有可能,我是经久呆在宫里的,怎么也认得我?”
他低头一笑,很无奈的,“店家说的不错,他是攀了阿哥的亲戚,不过不是贝勒,是太子!他原是做皮货生意的,后来攀上那么点儿关系,生意做到宫里去,十三大婚时他献过殷勤,故识得我们,如今倒捐了官来做。”
我冷笑,把脸扭到窗外去,心里头有那么一瞬的嫌恶,甚至骂了句烂泥糊不上墙。随后便是满满的悲哀,“你定是做了好人,两边都没得罪吧?”
他想伸手来拉我,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你果然是要生气。”
“我生气又有什么妨碍,沾不到边儿的人,爱怎样怎样,横竖和我再没关系。”撩了车帘子往外看,车已渐走出镇外,路边少有几户人家,偶尔听得几声犬吠,远处山林被白雪覆盖,因少有人来,雪地完整洁净,背风口处,几桩枯木……等等,还有一个人影,我下意识地叫停车,人就要往外冲,刚跨出车门,人影就匆匆沿土坡而下,消失在坡的另一面。
胤禛也随着我探出了头,想必也认出了那个人影,回头一把拉我进去,把我狠狠甩到座位上,“你念他,他也不一定敢来。”
“未必那么巧就是他,敢不敢也不由你说了算!”我瞪视他,“你以后最好不要对我动粗,我们谁也不归谁管着。”
“哼!”他也端身坐好,冷冷道,“管不管也由不得你说了算!”
我冷笑一声,“我是相信的,四爷一向好手段,明珠聪明了一世,也没逃出你的手心。我若黎,又岂敢跟你叫板儿?”
他突然伸出手来,抓住我手腕,使劲儿一带,我便趴进他的怀里,被他抬了下巴,“你是一直为这个恨着我?”眼睛里是火,手也重了几分,疼的我直抽冷气,却倔强着不肯表现出来,闭着眼不理他。他晃了我一下,“是也不是?你为福格,一直怨我心狠,和我好,也只是为报复?因为我爱你?”
是针在心上划了道口子,不见血,细细长长的疼!
他用恨的语气说爱我,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知道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可以在一起,却为彼此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沟渠!
我眼光落到他的手指上,无名指上,还套着当日夺我的戒指,此刻车内光线暗淡,钻石也难现其彩,似蒙了一层灰,水也洗不去。他突然疯狂的吻下来,似乎要把我揉到他的身体里去,舌像受了伤的迷路的孩子,四处寻着最安全可靠的去处。我在迷迷糊糊中想开口叫胤禛,他却突然放开我,一掀车帘出去,听到外边一阵混乱声,然后又渐渐安静下来。
我保持着他放开我时的姿势,半趴在他坐过的地方,车外马蹄踏雪的声音有序地传来,车身晃动,无端地想起那首《外婆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凡事皆有因果,种的什么因,结的什么果!
太原府地处山西中南部,在康熙年间,煤矿开采已初具规模,此时煤矿归朝廷所有,每年除上供朝廷及归官用外,同盐一样,不由私人私自买卖。因其利润极大,许多富商便买通了当地官员,私开煤窑。私人的煤矿主不比官家,他们更注重利润,在经营管理及雇工报酬方面均比官家高出许多,银钱自然滚滚而来,渐渐便形成一批靠煤窑起家的富贾,他们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些更是捐了官做,官商勾结,官借商权势,商贿官钱财,最后坑苦的还是百姓。一个月前,太原府发生特大煤矿坍塌事件,下窑的六十三名雇工无一生还,当地官员不但不报,又敷衍善后工作,几百名矿工家属结众声讨,太原知府不仅不加抚慰,反而无赖矿工家属聚众闹事,指使手下人鞭打闹事者,当场打死两名幼童及一名老人。不服的人们联名上告,却遭遇官官相卫,将呈递状纸的人活活打死。山西府衙的一名刀笔师爷难受良心谴责,暗中将此血泪种种挥笔成书,冒死送入京城,恰好拦了四贝勒爷的轿子喊冤……
晋商是个传奇,如果说浙江人聪明,那么晋商应该用智慧来形容。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山西的土地无疑是贫瘠的,可是她养育了山西人肥沃的大脑。山西人勤劳勇敢,敢拼敢闯,讲信誉,抱团儿,顾全大局,这些都是为商的根本。
行走在高墙窄巷之间,鞋底重重扣在结了冰的石板路上,有拉水的牛车,脖子里一路叮当响着进了谁家的朱门,吱呀的门响声和听不懂的招呼声合成一幅安稳的民生图。朱门复又闭上,我仰头看着门上讲究的铜鼻环,是怒目相向的狮子,不知门内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忍不住想扣一下,扣到半截又止住,这一敲,不知是否会敲出另一个故事?
低头一笑,继续走路。
这是我们到太原府的第二天,没有惊动当地官府,只扮作商人的样子在一处客栈住下。昨天胤禛他们就随着那名刀笔师爷去了事故发生地点,可能还会见一些当事人。胤禛虽不和我说话,我也知他是不愿意我去,在房里闲着无聊,便换了男装出来,来看看传说中的晋商大院。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个死党是这里的,经常蹿掇着我跟她一起来,可因为种种原因,一次都没成行。如果真的能回去,亲口告诉她我到过三百年前的山西,摸到三百年前晋商的蓝墙灰瓦,她会不会信?何不留下个纪念,让她来看?想到此,有些兴奋!看前边有个家庙一般的建筑,墙根是用超级大的石头垫的,佛主保佑这建筑不要被摧毁,也好给那妮子留个证据。我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蹲身在石身上刻了“牛牛,我真的来过。”本来想刻自己名字的,无奈太费周章,索性捡最简单的字,能说明问题就成!
刻完字左右看了看,又觉的有点丢人,好歹在古代镀了这么久的金,该说些更文雅有内涵的话,偏想都没想就弄了这么几个小孩子都写的来的字!一时心情有些不爽!
第 38 章
痴立了一会儿,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回头看是留下跟我的七喜,我因想一个人逛,就留他在客栈里,结果还是跟着了。
无奈的朝他笑了,胤禛调教出来的人都几乎一个德行,寡言、谨慎、利落。如苏培盛是我接触最多的,我从没见过他失态,总是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不能说他们是神,更像是兽类!
七喜打了个标准的千儿,“格格,天色不早,请回吧。”言语里是恭敬,却不卑不亢。
我没有拒绝的理。
回答客栈,掌柜的热情的迎上来,“小爷逛回来啦?”
我点头,无奈做这一行的天生话多,接着又问,“大爷昨天出去怎今日还不回来?”
我停住脚步,无奈的笑,“怎么你比我都急?是怕我们少了你的银子?”
=奇=“说哪儿的话?看您这身打扮,还是缺银子的不成?俺们山西人好客,就算您短了银子,俺们也不能委屈了爷们。”掌柜的腆着脸笑。
=书=“这话说的还中听。好好的做你的生意,别的就不要多问。”我倏地收回笑,径直朝楼上走。
=网=七喜在身后冷冷扔了一锭银子到掌柜怀里,“给爷备饭。”
掌柜的一边接银子一边道谢,待我走到楼上时忽然想起什么叫了声,“小爷!”
我住了脚看他,他左右看了看,紧走几步上了楼,离我三步远站了,低声说道,“下午有人来问过小的,最近有无可疑人等来住店,看着倒像衙门里的人,小人瞅着不善,只说没有。小爷你们一看打扮就知非富即贵,怕是有人要打你们的主意。爷们出门要提防着点儿!”
“哦?”我笑了一声道,“多谢掌柜的提醒了!不过我们只是普通经商人家,一向公平买卖,并无结下仇家,他们自寻他们的。”
“是是是,是小的多虑了。”掌柜的哈腰退下。“小的这就给爷们传晚饭。”
走至房中,小二送了水进来,七喜沏了茶端上,便站到一边。
我指着旁边椅子道,“跟了一天,辛苦你了,坐下歇着吧。”
“奴才不敢。”七喜吃惊道。
“坐吧,我不是你家爷,没那么多讲究。”我喝了口茶,不歇不知道,一坐下来,才发觉一天路走下来,腿也酸了,腰也硬了,好一会儿适应不过来。
七喜斜签着坐到靠门边的椅子上,腿也下意识的屈伸了几下,再是跑惯腿的人,这样一整天不分神跟个人也够呛。
“四爷对你们好么?”过了一会儿,我好奇问道。
他条件反射地想站起身来,被我示意坐下。才又低了头回道,“四爷一贯赏罚分明!”
“喔!”我点头,“脾气不好时拿你们出气不?”
“奴才们也分许多等级,奴才是第一次跟主子出门,但也都听苏公公差遣,不直接听命于主子。即使主子发脾气也轮不到我们这些品级较低的人,不过听闻那些跟主子久的人说,主子很少骂人!”
是了,他不骂人的时候都够威慑人,还何须动太多怒!
还想再问,门外一阵声响,是掌柜的亲自送饭菜来,七喜忙起身接过,并不让他们进屋来。掌柜的好奇怔了怔,便识趣地退下。还想再问些什么,又觉的没意思,纵然是他们不会乱自猜测,于自己却再无必要。
出了太原府,我们直向西走,经陕西榆林,宁夏,到达青海武威,然后南去西宁,一个月后抵达青海湖东畔,地藏汗已在那里等了半个月。
太原府的事怎样我一句都未多问,因时间耽搁太久,索性舍弃马车,我也与他们一起骑行,我的手因多年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猛一下受苦,生了许多冻疮,晚上睡觉时奇痒无比,七喜用土方子煮了辣椒水给我洗,才略微好上一点儿。
到达西宁城时,雪下的正大,早有地藏汗派的使者在西宁城里迎接,他们不曾驻扎城内,依康熙皇帝令驻扎在青海湖畔。
然而我们却不能立刻去见地藏汗,因为来藏的大多数人都因为适应不了高原气候,先后躺倒。
包括胤禛,他是病的最重的一个,别人都是服药后一天便舒缓过来,可是他却又发起了高烧。地藏汗派来了巫师来为胤禛瞧病,我知道藏族的巫师除司祭祀外,还兼有医生的职责,只要他不跳大神,我认为他们的医学知识还是比我多,所以尽管苏培盛不放心,我还是准那藏族巫师给胤禛来切脉配药,看药方时发现其中确实有当初玛吉来人给我治病时的几例药材,我亦放心的命人给煎来喂送。
病中的胤禛异常听话,高烧使他失去素日的骄傲,甚至是意识。喂一口药下去,眉头都不皱一下,乖乖喝了。藏族翻译传达巫师的话说,天子的使者是因为连日劳累加上风寒及高原反应,才会多病一起发难,致使身体虚弱,难以承受病魔侵袭。
我望着他苍白的脸,因发烧脸颊处微有些病态的红,呼吸紊乱,眉头紧锁。病了,都还不知放松!
我叹了口气,擦掉他嘴角的药渍,掖好被子。
外边雪下的正大,走廊上立了一会儿,才回自己房间,拥被独坐,脑子似被冻僵,什么都想不通。
迷迷糊糊中似听到有人叫若黎,慌忙起身,推开隔壁房门,见苏培盛一脸的愕然,继而镇定下来轻声道,“爷似乎在叫您名字,奴才正准备叫您去呢!”
“喔!”我点了下头,继续往里走,身后有苏培盛退出关门的声音。
也顾不得什么,胤禛疲惫的叫了声“若黎”,我快步赶过去,却见他闭着眼睛,并无清醒的样子。摸摸头,已没有初时的烫,到底是底子好,一幅药就能见效。他已不吭声,不知是睡沉了,还是意识到我已在身边,眉头慢慢苏缓开来。见他嘴唇干裂,便去桌上拿水,竟是凉的,本想招呼苏培盛去准备热水,到底止住。他又叫了声若黎,我返身回他的床前,凝神盯住他看,眼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看着眼前他的面容就虚掉模糊了。
“若黎在这里。”我轻轻的答道,不是回他的话,是在跟自己说,若黎在胤禛面前,却手足无措。摸着他棱角分明的脸,眉梢眼角鼻翼,佛主问女子尤洛斯爱伽南哪里,尤洛斯说,我爱伽南的眼,爱伽南的鼻,爱伽南的口,爱伽南的心……,佛主点头!
尤洛斯爱的简单,伽南背后是佛主,佛主是通灵万物的,佛主愿意原谅。我爱的懦弱,我不敢面对有朝一日胤禛身后背负兄弟骨肉怨忿的江山,我怕得不到原谅,胤禩的胤礻我的十四的,甚至是十三,都可能不原谅我!
冷了手,收回来,低身去吻他,用自己的舌尖去润湿他干涸的唇,然后起身。
他突然说,“若黎,你不许走。”我一怔,他手一拖,便把我拉到他怀中,“我没有糊涂,若黎,你不要走。要是我病着你才肯亲近我,不如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