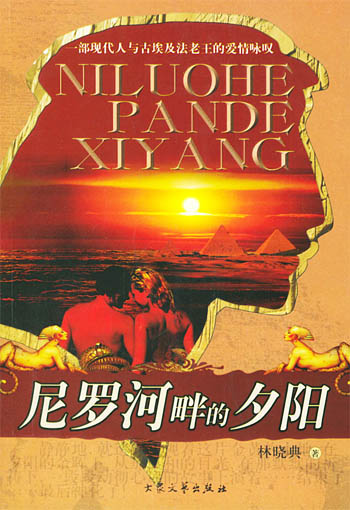玉带河畔-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来,除夕晚上吃完饺子,青云跟雷达给林民夫妇拜年,林民顺手抽出二十块钱装在红包里给俩小的做压岁钱。因为雷达还小,玉秀就把雷达的红包给了青云,又嘱咐她好好存着,等开学交学费。这样,青云就把她妈的话给记脑袋里了,想着自己一定要多攒压岁钱好开学交学费。
青云知道她奶奶抠门,又好面子,每次就爱包大红包,偏偏里只面塞五毛、一块的毛票,还弄得鼓鼓囊囊的,不晓得的还以为里面塞了多少钱哪!于是这次去老李头家拜年时,小机灵鬼就挑了个早上本家通姓拜年人多的时候来。
老太太虽心下不待见这个性子随了大儿媳的孙女,可晚辈来拜年,说喜庆话,当着这么多人,总不能甩脸子撵出去,于是就不甘不愿地从炕席下掏出一个大红喜包塞给了青云。
青云当着众人面打开红包,见里面是两张一块的,就撅着嘴儿把红包又塞给老太太,道:“俺昨晚上问俺爸俺妈过年好,他们一人给了俺二十!”说完,就瞪着两个大眼珠子,往老李头老太太身上使劲儿瞄。
前面说过,丁槐村有大年初一早上在村里拜长辈的说法。老李头在村里也算是辈份挺高的几个老人之一,初一早上,来拜年的村人络绎不绝,这会儿更是有四五个年轻后生正坐在炕边上说话。青云这话刚落,屋子里便出现了一小会子寂静。
老太太本想着拿出红包来早早打发人走,没想到大孙女竟来了这么一出,不禁有些尴尬,也有些生气,正准备发火儿呢,那边老李头从兜里掏出两张大团结塞到孙女手里道:“来,来,云云,不要你奶奶的红包,过来爷爷给你‘割(ga)耳朵’的。”
在农村,过年时长辈为图喜庆,一般都会去储蓄所兑些崭新的钞票装在红包钱做‘割耳朵’钱,说是能割掉小孩子耳朵根儿上的晦气,来年一整年顺顺当当。
青云这会儿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便心满意足地跟老头老太太回了句:“爷爷奶奶,你们先忙,俺去俺叔家拜年了啊!”说完,还甩了甩崭新的大团结,打出个响来,才转身往外跑了出去。
本就心疼老头子一下子拿出了二十块钱的老太太听了这话,刚憋回去的那股气儿“噌”地又上来了!这小兔崽子,嚯嚯了她二十块钱不中,还要去嚯嚯她家林宝!这小兔崽子!简直跟她那猴精儿娘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满肚子花花肠子坏心水子!
青云到她叔叔家拜年倒没一个人来,而是回家背上了弟弟雷达。林宝家的青华这会儿已经五个多月了,眉目刚刚张开,身子有些娇弱,整日里除了吃就是睡,安静地跟只小猫似的。云芝刚做母亲,正是母爱泛滥的时候,因为生了个男娃,如今更是喜欢活泼淘气的男孩子多来带带她儿子。这会儿见了刚会满地儿爬着叫人的小雷达心里也颇为高兴,一边招呼侄女,一边抓着块糖笑呵呵地逗雷达喊她娘娘。
青云在路上已经教过弟弟怎么喊人了,雷达也是个不拘的,抓着云芝给的糖便奶声奶气地喊:“娘娘……过……奶好!啊……啊……好……”虽然喊得断断续续,但配着这张肥嘟嘟的小脸儿和粉软的小嘴巴,便显得格外讨喜。
云芝心下欢喜,掏出两张十块钱,一人塞了一张。青云把钱放在弟弟的小口袋里,又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展到云芝跟前,抿嘴儿道:“娘娘,爷爷给了俺二十呢!”
云芝面上一滞,又让林宝从抽屉里拿出二十块钱,塞给了青云。
青云收好压岁钱,心想着要是能天天过年就好了,这样她不光能捞着啃鸡腿,还有红包拿,更不用见天儿地起早上学写作业,这日子得多滋润啊!
林民两口子不知道自家闺女在外边干的“好事儿”,对于老李头今年竟舍得给孩子这么多压岁钱也只是小小诧异了一下,并没太过放在心上。因为,这两天村里又出了大新闻——年三十那天晚上,村里来了辆派出所的小四轮!
说起这辆车出现在此的缘由,笔者不得不先说说此时丁槐村的大环境:丁槐村隶属的镇子叫马庄镇,是原来的马庄镇跟唐庄镇合并而成的。也是当年乡镇规划没归并好,两个镇说是合并了,可镇上的领导班子和公共服务系统却并没立刻整合,这就导致了现在马庄镇有两个派出所,两个计生办,两个镇医院,两个中心中学……这样有利有弊,往好的来讲,这也算是有竞争了,两边的医院会时不时地会下乡送个药、做个免费检查活动,学校也会在每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到各个村子做学生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各种优惠条件。
可这不好的地方也很明显。就拿这派出所来讲,镇派出所每年到了年根儿严打时期,下乡抓赌抓嫖可以说是所里年末完任务的主要来源,特别是聚众赌钱,人头多,油水足,既便于完成指标,又能多捞点儿外快。可现在两个所一起干这活儿,这不是想啥时干就啥时干的了,而是能者多劳,哪个所先逮着人就归哪个所管,这样一来,就出事儿了。
以前的时候,因为派出所也要放假,一般严打到年根儿放了年假也就过去了。可现在不同了,两个所为了争指标、争优先,大过年都不歇班,挨个儿村窝着逮人。于是昨晚趁着大年三十,几个聚在一块赌钱的村民就不幸撞在了枪口上,这里面就有前面提到的胡建国。
聚众赌钱在农村其实很常见,虽然派出所抓得挺严,可把人给逮回去了,也不过是把赌资收了,再罚几个钱拘几天做个行政处罚就了事了。
活水养鱼,“可持续发展”。
这样,初一这天早上,被逮着的几个人就回来了,虽说算是一景,倒也没那么大波折。让大伙儿看热闹的是,隔壁的胡建国回来后,他媳妇却被派出所里的给逮走了!
这可是大事儿了!
大伙儿谁不知道啊,胡建国那媳妇,虽然嘴碎了点儿,可平日里在村子里也算是个勤快老实的,怎地会被派出所带走呢?
再一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胡建国惹的祸!胡建国是个好赌的,村里人都知道,前段时间这厮手痒了,竟跑到邻村杜家村去赌,结果一晚上下来,身上输得精光不算,还欠了人家三千多块钱。这胡建国上了赌桌入了迷,时间一久脑袋也木讷了,欠了赌资后又打了张借条,上面写着因为某某事儿借人家多少多少钱,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还有胡建国红灿灿的大巴掌印在上面。
这下好了,大过年的,人家理直气壮地要钱要到派出所了。为了过年不被拘看守所里,胡建国又想了个让媳妇给自己顶缸的法子,三下五除二将事全推到自家媳妇身上了,这就出了他媳妇初一早上被派出所的给传了去谈话的场景。
胡建国家这事儿在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毕竟一个大老爷们干这样的事,也着实太没担当太没种了。可不过几日功夫,林民家却没怎么有功夫关心这个了,因为刚刚过完年没几天,林民的雇主便打来了电话催人,很快地,林民便收拾了一下东西又出去打工了。
作者有话要说: 作者有话要说:很多读者很疑惑,为什么前面解春旺杀了人却没被送进派出所,而这边胡建国只是小小的赌博便被逮进局子里去了。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农村很常见,笔者记得很小的时候,曾经目睹过一个做婆婆的将儿媳妇从河岸上推下去,那个媳妇不会游泳,被救上来时早就泡囊了,大家只是说那个做婆婆的苛刻,却没一个说该报警将那个做婆婆的抓起来。而还有一件事印象也蛮深刻的,村里有个姓刘的小子好赌,最后在赌桌上连自己媳妇也押上去了,后来对方真将他媳妇给睡了,这事儿让人给举报了,那个睡人家媳妇的人没啥事儿,那个刘姓小子却被拘在所里待了小半年……有些事儿,笔者真实目睹过,也疑惑过,真要说点什么时才发现,自己只能叹一句,泱泱大国,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扭曲的不像一个国家了……
☆、赤松
作者有话要说: 长长的玉带河畔,黄沙漫漫,连接远山与河沙,凝固明黄与松散,干枯斑驳的枝干,密麻尖细如针的叶子,深厚耐旱如网的根系,还有耐旱喜酸不急不慢的性子……便是一波又一波的洪水冲过,那又怎样?便是干涸的沙土浇进热浪滚滚,那又如何?它坚强着、坚持着、坚定着,不是话语的描白,而是一生的写照——赤松
林民在外打工的地方也算鲁省颇为出名的地方,那就是有“蔬菜之乡”之称的寿光。林民去时,正逢寿光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这时候全省各地,甚至是全国各地大棚种植还颇为稀少,而寿光市辖制下的乡户人家已然有一家三四个大棚的规模了。这样一来,人手肯定不够,雇人来打理大棚的现象就变得稀松平常了。
林民以前在钟家村时一个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兄弟,早年倒插门到这边做了上门女婿,这活儿就是这个兄弟给介绍的。
这个时候寿光的蔬菜棚还是那种北边有挡风泥墙、南边为竹竿立柱撑塑料布的温室棚,但即使是这样,初来乍到之时林民也被这规模庞大的大棚给惊住了。想想吧,入冬后的平原大地本是一片皑皑白雪,偏偏这雪白里如今还缀着密密麻麻的一层又一层蓝色波痕,如潮水般铺天而来,而这波痕就是一家又一家的大棚;不光如此,外面明明寒风凛冽,棚里却偏偏一幅春暖花开、绿茵葱葱的景象。这样的视觉差,也不怪乎初来者会惊诧赞叹吧?!
林民受雇的这家男人姓刘,叫刘文业,是林民那拜把子兄弟媳妇的一个本家叔叔,家里有三个大棚,是一年四季棚,种的全是无刺小黄瓜。年前,林民跟林宝来时正逢夏初,每天做的活儿就是中午头太阳毒的时候将三个棚的草毡子放下来,近傍晚太阳不毒时,再将毡子给卷起来,其他的时候便是跟着这家女主人陈娟在棚里给新花授粉、打农药,将长成的黄瓜摘下来,包装好、上秤上车。这就是两人回家后看着显得白了不少的缘由,见天儿地在暖呼呼的大棚里捂着,换谁都要白净不少。刘家除了村里的这三个大棚外,在镇上还有一家果蔬包装袋批发门市,男人刘文业大多数时间都在铺子里进货发货,偶尔回趟家,基本上也是为了往村里送包装袋。
刘家在村里有栋两层高的小楼,刘文业夫妇俩住在一楼的东间卧房,儿子闺女住在二楼;林民林宝则住在一楼的西间卧房,屋里是四张上下铺的架子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桌子下是几个马扎,一看就是给来打工的住的。当初兄弟俩刚来时,这屋里已经住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儿了,小伙子也姓刘,叫刘飞,平日里在刘文业镇上的批发铺子里干活儿,晚上的时候刘文业留在铺子里看货,刘飞就回村里住,第二天骑着车子,再带着刘文业的早饭赶去镇上。
这次回来,林宝没跟着来,这个屋里就剩下了刘飞跟林民俩人。刘飞过年时压根儿没回家过,据他说他爹早年得病死了,他妈不久也改嫁了,家里现在就他一个人,他既不愿回家一个人对着冷灶台发呆,也不愿去继父家跟一群不熟悉的人过年,干脆就留在刘家替刘文业守了几天铺子,正好挣几包烟把子钱。
林民从家里带着玉秀做的灌肠,给主家送了几根,剩下的就扔在桌子上,让刘飞想吃了就自个儿拿着吃,然后就换了身旧衣服,跟着陈娟去棚里放草毡子去了。
虽然只有十来天没进棚,可现在大棚里的景象明显变化了不少,原来还只有小指头大小的黄瓜扭子,现在一根根长得有林民中指那么粗了,水嫩嫩的,绿中还带着些嫩黄,头儿上坐着黄嘟嘟的小花,显得格外招惹稀罕。
陈娟挨个棚转悠了一圈,面上明显带着喜色:“今年这茬黄瓜长势不错,再过个四五天,基本上就可以有进账了。”说着,从边上的蔓上摘下了几根来,给林民递了一根尝鲜。
林民掰掉瓜花,在裤子上随便擦了擦,便狠狠咬了一口。也不知是黄瓜品种的原因,还是长时间没吃过新鲜果蔬的缘故,不得不说,这无刺黄瓜口感竟比那露天菜园子里的黄瓜格外脆生。“这黄瓜现在下来,价挺高吧?”
“三块多钱一斤吧!”说到这个陈娟倒有些惋惜,“咱家这茬黄瓜是年后下来的,卖不出高价来,村里有几家上的是双膜棚,温度提得高,黄瓜下来的也早,人家年前卖的六块多钱一斤呢!那才叫价高。”
这时候猪肉的价格也是六块多钱,也就是说,这黄瓜竟货真价实地卖出了肉价!林民觉得自己这回出来果真是个正确的决定。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把这门技术学到手,种大棚可不是打理葡萄,你就是想分,没有技术也是白搭,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