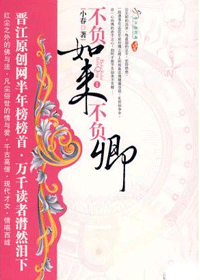��������������-������(�����) ����:��-��6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ڸ��Ϻ���������
�����������ʴȻ�������֮�����ͺ����õ�ū�ͺͳ����������͵ı��̺���������ٻ������Ҳ��ɼ���
��������ʮ���¡��ٻ�����
�����������ʴȻ�������֮�����ͺ����õ�ū�ͺͳ�������ʢ���ı��̺���������ٻ������Ҳ��ɼ���
�����������ȸ��ԡ�
���������Ҿܾ����ڷ��������˺ü��ա��������˼����ȷ���������⣺ǿŤ�Ĺϲ����Ҳ������ϣ�����Ժ�ĪҪ�����Ϊ���������ˣ���˼�����Σ�Ҳֻ�ܽ��ܡ�
�����������ɵزμӰ�˼����ʮ���������硣��˼�Ͳ��ܳ�̫��������ȵĶ��������ֲ�Ը�����������Լ��籸�ü���ֻ��һ����Χ�������˼��ף�أ���˼�;��ã�������̫��ʱ�䣬������������������Ϣ��ͻȻһ�����ӳ�����������������������������������ֹ��������������
������˼�����Ҷ���һ�ۣ�������ɫ��䣬����ɣ�����ǽ�ֹ�����������ѵ����������ˣ���˼�ͳ��������Ե��ӷԸ��������̽����Ǵ���������
���������ڵ��ӵIJ����һȳһ�յ��߽��鷿����������ܴ��ѣ������������ϸ�·�����ݿ��£�����ή�ң����Ѳ�����ǰ��ֺ������̬֮����˼��������һ�µĻ���û�У�ֻ������ؿ�������
��������Ҳ���ϻ���ֱ�����⣺����ʦ��������û�б��Ŀ�ģ�ֻ������ҷ�һ��������֪����������ѡ���
������˼��üëһ̧�������£���
����������ɭɭ��Ц�ţ���������֮�������Ǻ�����Ϊ����
���������̧�ۣ���æ�ʵ������������㾩�����������𣿡�
������������ʹ��û����������һ�룬�ҷ�����ʱ��������������ȷ��������ͻȻ�����Ц������ͷ�������˰̣���Ц�����˰̸��Կֲ�������ô��������������һֱ��֪������������һֻ��Ы�ӣ����������ͷεض���ֻ��Ы�Ӻá���������������֮������֪��ʵ�飬���ǻ��鶼���ð�������
������˼�ͼ�æ�߽���������һ�������������죺����˵���ǹ���ɣ������
����������¶���⣬��ݺݵ�����һ�ڣ�ҧ���г������������������ֻ��Ы�Ӷ����˰��������ִ��㽫��ֹ���������ţ����Ǻúݵ��ֶΣ���
���������˵������ɣ����ʲô����Ҫ��ǡ�ǣ�����ʮ���������ǡ�ǣ���ǡ����������������������Ȣ�����ȴ�С�㣬�Ӵ�����ū�����ݡ�����˼��ͻȻͣ��ס������ؿ��������������ˡ�����ɣ������ֹ�����㻳�����ģ����Է�ҧ��һ�ڣ�����ҵ��ֳ��������Dz��ǣ���
�������Ҿ�֪����ʦ�������ţ������Ҵ��������������������ɮ�ۣ��������и������ڴ�������С�ĵ��ó�һ��С��ֽ����һ����¶��һ�ű�Ե���ƵĻ�ֽ��������Ƕ�Ы�ӱ������度�����ӵ�֤�ݣ�Ҳ����Ϊ��Ҫ��ֹ���������ŵ�ԭ��
������˼�ͽӹ�������Ͱ͵Ļƽ㣬�Dzصس������������������Ѿ����ڵ�ָӡ�ͼ�����֤�˵����ֺͻ�Ѻ����˼���ɻ����ǣ���
�����������ϵ������������ʲ���������ֻ����һ��֪�������ڽ�ʲô����������ĥ��Ц�����������������ӵ����������Ǽٵģ����ԣ������ʲ���������ֹ����һ���������˼�Ͳ����������ʣ��������ʲ����ǹ���ɣ������
����������������ص����~��ԭί��ԭ�����ڰ��Ǵ�ʱ�ڣ�ֹ�������Ƚ����˳�Թ����ʱ�ոյ���ֹ�������ľ�������������������ѡ��������ĸ����ຢ�Ӳ������������ȣ��ѳ��Ǻ��ӵľ˾ˣ�����Ƿծ�������������������������ȡ�����ֻ���������Ȱ������ߣ�����ʱ����û�ϵ������������µ����Ӿ��ڶ�ʮ��������˾���������ֵ����ã�����Ϊ����ɣ���������ʲ�����ʮ������һֱ����ǡ������ԭշת����ֹ������ʧȥ���硣��˼���ֵ����زصؾ���ī��ʱ��Ӧ����֮������ֹ��ͣ�����գ�ð�乱��ɣ���˾˵�����ֹ�����ӣ��ӹ���ɣ�����ϵ�̥���ϳ��˵���ĺ��ӡ�
����ֹ������ϵ���˹���ɣ��������������������Ҫ��ɣ��Ϊֹ�����~�����ֻ��Ҫ�����ṩ���ȵ��鱨��������ֹ�������ȵ�Ħ��Խ��Խ���������ȫ�����͵ĵز�����ʱ�����������ܷ��زصص���ϣ����������ֹ�����뾩�����ļ��ϣ�����ֻ��Ҫ��˼�͵���������ϣ����ȴҪ����ǡ�ǣ���˵����˼����ǡ�ǵ���̶ȷ���ͨ�ֵܿɱȣ���ʹ����һ�����ҽ��ѣ���һ������Ҳ���Դ��������һ�겻��
��������������ȶ�����˶�����һ��������ļƻ�������ƻ���Ҫһ���ӽ����������˲�����ɡ�
������ʱ�Ĺ���ɣ���������ȹ�ү��������������������������ϴ�Ӧ�����Ǿ�����в�ع��������ʲ������ݣ����������ղ��ɣ��������ֹ�����������ɣ���������ӣ��������������������ʲ���������������թ���ʲ���������ֹ���������˵�֤����Ѻ����Щ��ȫ��������ֻҪ��Щ��֤��������һ���״̥�ǵľ��������ʲ�����û���κΰ취������
�������Ƶ����ǵĹ���ɣ��ֻ��ҧ��ͬ�⡣����ѩɽһ֧����ֲ��������¥���ֹ�����߳���ǡ��ϲ���Զ��ǣ����վ�������ϣ���˵ļƻ���ǡ��������·���������������Ѳ���Ϊǡ����ʳ����ȴ�Ա���Ϊ�������Գԡ����գ�����������������ǣ����Լ�Ҳ�ж������������˻ỳ�ɵ�����
�����������������ף�Ϊ����Ҫ������ֹ���ɣ����������ض��㣬����Ѫ˿�ܲ������㽫��̧��̫�ߣ����������ȱ��գ�����Ů����δ������֮�ޡ���˾����������ǰ�����ڲص���һ��֮������֮�ϡ���������Ը�����İѱ����������ϣ���ֹ�����ţ���ɽ�֪�������ܵ���ȫ��ɱ��������������˵��Ϊ�˰��������𡣹��������˵ĺ���˼�����ֶΰ�����
������˼��վ����ס�����ӵ���ײײ�������£��Ҽ�æ��ǰ��ס��������������ޣ�һ���������鰸���������ڻڲ�������������ֹ���϶����ȷ�����������ʧЩ��������������������֮�֣������ֹ������ǧ����ˣ����DZ�ɱ���DZ��������ڶ����ƴ�����������ӳ����������������������Ϊ�������㡣��
������ͻȻ����������һ��ذ�ף�������һ������æ���ڰ�˼����ǰ�����ϣ����������ذ�����Լ��ľ���������µ��Ǵ�Ѫ������ⶼ����Ϊ���Լ����˶������ȣ�����������ҵ�����Բ���ֹ���������ڡ���������Ӧ�ã�����ֹ����ô���˶������ģ��������㣬���Ǵ������Լ��������ָ�������������������Ķ������ǹ���ɣ����ֻ�����ܰγ���ֻ��Ы�ӣ�Ϊ��ֹ������ȥ���˱��𣡡�
����������ذ����ǰһ�ͣ���ͷ���ۣ�̹Ȼ��������һ˲�䣬����ĺ�������ذ�ס����ٴ����ォ����ǧ����У����̻���������ڵ��Ӿ�������ǰ����ȴ����������ȥ�á���˼������ս�����Ұ�������Ĭ���ã����ų������������㺦���ҵܵܣ�������ô�����캦��֮�£���Щ����******�������壩���Ӳд�������Ϊ�˵ȡ����������һ�졣�������Ҳ�ܵ��˶�ҵ����������������������ת�������ž��������������Զ֮��Ʈ�������������Ҳ�ɱ�㡣�����ˡ��˰��ˣ����Ų��Ƕ������ijͷ��������µ�ÿһ�춼�����ޣ�ÿһλ��ȥ��ֹ��ͽ�ڶ����Ϊ���ج�Σ�����������ɸ���㷢��������¶������Ŀ־塣��˼��ÿ˵һ�䣬���Ŀ־������һ�֣����ͷ��˻���ߵزҺ������ĵ����Ǽ�æ���������·���˹��㣬�������ѿ��������������غ��ţ����������������Ҳ��ǹ���ģ���
����������Զ������������ֹ���ɷ������������Ŀ־���ں��о���ʧ�����������������Ӵ��ص��ص�û��ã���һ������Ķ���ҹ���������������Ĵ����ߣ����������¡�ֹ����Ȼ�ܵ�����ش���������֮�����������������ĵ����������ټ���������ؽ���ֹ���¡���Ȼ����Ҳ������չ������Ҳ�����ʶ��صص�һ���ɵĵ�λ�ˡ�
�������ž�����ҹĻ����ʧ����˼�����ֳ����������������Լ�վ�ȣ������ض�����˵�������ȣ���������һ����������ȣ���
�������ס��������������������˳�;���氡����
������ҡͷ��������������ʹ��͵��ǣ����ұ����ȥ������˵��û�������ҽ���Ы�ӷ�������ô�ߵ�λ�ӣ����Ҳֻ���Ҳ��ܰγ�����Ϊ����ɨ������
�����Ҽ���Ҫ���ˣ�������������ȵ��ƣ��в��������ɽ�ͽӵ�������������ѷᣬ���ȥ��Ҳ��һ�����������⡣�ο�����������ܳԵ�������
������˼�Ͱ��������и���ʹ�������ؿ����ң������ȣ���Ը���������ȣ�������ǡ�ǡ���
�����Ҳ�������������������ɬ���̣��������������ӡ���ͻȻ���ƿ���һ���ߴ����Ӱ�������룺����ʦ����������������������Ȱɡ���
���������˼�;���һ㶡�����˵�Ļ�̫�������Ҿ�û��ע��������������ط�����ʲô�£���������Ѿ��������ˡ�
�����ҷ��Ű�˼�����£�����ϢƬ�̣������ҡͷ��������ô���ԣ��������ڹ����ϱߵ��ι�����Ҫ�ﱸԶ������������������ܰ�����æ���ݿ������ף������Ĵ���������ĵܱ�ƽ����ľ��������֣����ر���������·;ңԶ��һȥ���ꡣ��ոձ���Ϊ̫�ӣ������������Ҫ����������������ʱ��������ȥ���ȣ�������ڳ�͢�ϼ�Ϊ��������
����������Ƴ��һ�ۣ���ͷ��������һ˿���ɵĺ��Σ�����ʦ�����֪���ҵ���˼����
�����Ҷ�ʱ���ˣ���������Щ���ա�����ô�������ģ���˼�Ϳ�����һ�ۣ�ƫ��ͷ���Լ�����
�����������һ�£�ҧ��ҧ���̧�ۿ����˼�ͣ������������������𣬿��Ը���Ů����ߵ���ҫ��Ȩ�ƣ���С��������������Щ����Ը��Ϊ�����������κ�Ů�ӣ�����Ҳ�����š�ֻ���ͳ������������������п��ܽ����ҡ�������ʦ�����ȣ������������Ը����Ϊ������֤���ҵ����ġ���
�����Ұ��յس����£��������ͱ��١�����
����������ң�������ȣ������������С�����Ҿ������¡���ʦ�������֮�ˣ�����ʦԲ��֮ǰ���Ҿ�����������κ����֮�١������ʦ�Բ���֮�������������Ż��������ҵ�����ն���������ο�����̫��֮������Ϊ�������ȷ�����ӵ�λ�����Ųصؽ������ٸ�������֮�ģ���Դ����δ��Ҳ�кô��������𣿡�
�������һ�仰���Ƕ�����˵�ģ�Ŀ�����Ʊ��ˣ��Ƶ�����Ҳ������Ե����ɡ��Ҽ���ֱ��ţ����㣬�����ô������
������˼��ͻȻ���ԣ��������������DZ��������飬�ұ�ͬ�⡣��
��������˷ܵ�������������⣬���еص�ͷ������ʦ���ģ����������ʦ����һ����˵�����ʡ���
�������˵��û�����˴λ����ȣ��������ԶԸ����������ĸ�ɣ����ֻ��������������������ȷ�����ݡ��Ұ���̾������Ȼ�������ǰ�Ҵ��Բ��ѵ�˵�����������Լ������ٵ����ּ����¼����һ�����Ҫ������������˼�ͺͶ��ӡ�
������Ԫ1274��3�£���˼�Ͳ������岡�����������ͬ�����һ��̤�Ϲ���֮·�����Dzʹ�ٻش�������ҵ����飬�ɰ�˼�ͼ�����·���Ȳ���ʹ�ߴ��غ�����ּ�⣬�����������˼����·����ʹ�ߵõ�������ּ�����·�ϡ�
�������������������������Խ��ԽС����䬳ǣ������������ᡣ��Ȼֻס�����꣬������������������Ϊ�����������˽��������ĸо����������������������ܴ��������ǣ���ˡ���˼���뿪ʱ������֪���Լ����������ܷ�����ԭ���㽫���ׯ������в����������������չ����ĵ��Ӻ����ۡ�
����һֻ�ַ����ҵļ磬��ת������Ҳ�����⿴�������������ƺ��ڳ�˼�������������������𣿡�
���������һ�£��������ˣ�ҡ��ҡͷ��§ס�ҵļ������ٶ���һ��������������ô���ˡ���
������Ͷ�������У���ԥһ�£�С��Ȧ�������ݵ���������ͷ�������ϲ����������ҵ��ᡣ�����ᱧ���ң��·����Ǹ�ֽ�ˣ�����һ������ȥ�����Ǿ�����С��������ӵ���ţ���ˮ�������䣬�����ֺ�ɮ����Ⱦ��һ���������С����
������˼�;��ܲ���ÿ�쳬���ĸ�ʱ���ĵ�������������ֻ�ܾ��������������н����ٶ�ֻ��Ѱ��ʱ�������֮һ����˼���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