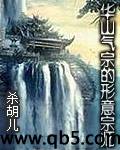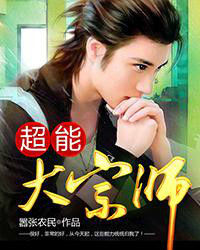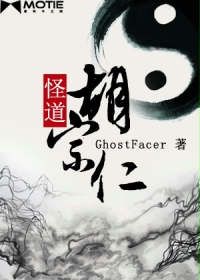煮酒话太宗-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匈奴不是和秦汉一样的国家,它其实只是草原上诸多部落之一。后来通过战争,使其他部落臣服,也没有像炎黄那样合并成一个部落,而是形成了一个共同攻守进退的部落联盟。各领主继续领有自己的私有部落,但领主本人有义务听命于匈奴部的首领——大单于。后世经常为了渲染这种部落联盟的强大,将其称为匈奴帝国、突厥帝国,法国史学家格鲁塞还将他们的故事编著成一本《草原帝国》。其实这仅用于形容其强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帝国。
虽然蒙古草原的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谈不上先进,但掌握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马。
马是冷兵器时代骑兵必备装备之一。作为一种生物,马适合生长在高寒地带,喜食干草,绝大多数汉区都不适合养马。蒙古草原是马匹主产地,蒙古马种的质量显然比不上中亚或更西方一点的阿哈尔捷金马(汉语称汗血宝马)和阿拉伯纯血马。但蒙古马吃苦耐劳,极易大量繁殖,草原游牧部族不需要掌握太高的畜牧技术就可以放养出大量马匹,用以组建至少在数量上很庞大的骑兵军团。所以,这些草原部族一旦联合起来,将是非常可怕的军事力量。从汉代的匈奴起,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北方草原的边患成为每个中原王朝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中原王朝形成统一之前,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汉人自己打得不亦乐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秦汉以后,汉民族形成统一汉式帝国,游牧部族反而成了严患。其实这正是因为汉人的文明在进步,游牧部族也在跨越式发展。
首先是技术方面,周代游牧部族逐渐掌握了大规模放牧的技术,才能组建较大的马队,而汉代匈奴从西域学习了初步的锻冶技术,开始使用金属武器。不过汉初匈奴主要以兽皮甲和兽骨箭镞为武器,相当落后。最重要的技术跨越则是马镫,马镫是骑兵史上划时代的发明,使骑士和战马融为一体。马镫发明前,骑士无法在马上坐稳,要想发挥马力的威力就必须配备工业化产品——战车,这显然超出了游牧民族的能力范围。而马镫发明后,一人一骑就取代了战车,骑兵从此驰骋战争舞台上千年。不过马镫发明的确切时间还有争议,大概是在汉代,也可能更晚。
除了科技,更重要的是组织管理。秦代以前汉人没有形成统一帝国,草原上更是一盘散沙,游牧部族成千上万,无数马匪比战国七雄打得还欢。正是匈奴部的头曼单于、冒顿单于等强势领主树起赫赫声威,才将这些部族整合到一起。虽然还只是部族联盟而非帝国,但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三十万马匪一旦组织起来还是很恐怖的。
那么汉初面临的匈奴到底有多强?
这样比方吧,汉初汉军大概相当于北京市公安局,匈奴帝国则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有人就奇怪了,北京市公安局连个地级市城管局都搞不定?别忘了匈奴最大的优势,就是想打就打,打了随时跑。草原那么大,他随时出一支马队到一个边城来收摊——也不占领,收完摊立马就走,等你北京市局的步兵赶到,早就没影了。反过来组织大规模兵团深入草原讨伐匈奴却不太现实,一则草原太大,找不到敌人;二则过于深入容易被马匪切断补给线;三则中原王朝出动大军攻入草原,他反正没有城市,你要践踏草场请便,我自领军趁机攻入中原——放心,也只是抢一把,不会占领国土,但你也不可能不回救,你要是回救我又没影了。所以针对这三点,从战国的燕赵等国起,历代中原王朝大都要修建长城,以对抗游牧部族。
虽说组织大军讨伐草原性价比很低,但严打总是有用的。狠打他一次,很长时间内他都不敢再来。就算不能狠打人家一次,也不能让人家狠打自己一次,所以就需要嫁几个公主给人家……但就算嫁公主,前提也还是要打得赢,不然人家可以直接来抢,无需你嫁。
汉文帝还算幸运,秦始皇赔上基业,修好了长城留给他用现成的。汉高帝亲征匈奴,遭遇白登之围,靠给冒顿单于的老婆行贿才捡回一条命。后来冒顿单于又写情书挑逗寡妇吕后,大政治家吕后忍一时之气,低声求和,但将此列为国耻,遗命子孙定要雪耻。汉文帝登基时,汉朝已经册封了好几个宫女冒充公主嫁到匈奴去了,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和平。汉文帝手持吕后雪耻的遗训,但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方面是要执行与民生息的政策,不愿轻开战端;另一方面是时机确实还不成熟,要实力积累够了才能打。
为了积累实力,汉文帝、汉景帝一方面对匈奴委曲求全,送钱送女人,开放贸易。匈奴有了钱和女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打劫的冲动就克制了很多。而且通过贸易,匈奴可以买到盐、铁、布等物资,一旦开战就买不到了。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贸易能够交换比较优势,使每个人的情况都更好(剥削式的不对等贸易除外),匈奴通过与汉人和平贸易,比打劫更能促进本民族的文明进程。
另一方面,汉文帝也绝非老好人,和平发展的同时,也在整军经武。汉朝采取全民兵役制,寓兵于民,每位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不过汉文帝把秦朝十七岁开始服役,每年一番的政策,改为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三年一番,已经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文帝朝兵役制度执行得很好,汉军的指挥、训练、后勤、装备体系建设卓有成效,为后来汉武大帝麾下那支所向披靡的铁血汉军奠定了良好基础。汉文帝还在西北边境开设了许多马场,并鼓励民间养马。据粗略统计,最多时官马便达四十万匹。汉武帝征讨匈奴的思路就是以骑制骑,不仅是冲锋在前的那一小部分战马,负责后勤保障和轮休所用的马匹更是多如牛毛,如果没有汉文帝的积累,这样的战争简直无法想象。
所以汉文帝包括后面的汉景帝朝,汉帝国始终没有和匈奴,也没有和其他任何人大动干戈,直到汉景帝朝后期的七国之乱,汉军才真正面临大战考验。如果非要挑汉文帝开疆拓土的功绩,勉强只能算上对南越的和平收服。
上一篇讲到天下反秦,项羽、刘邦直逼咸阳,但秦朝正规军都在外地不回救,这其中最大一支有五十万人,正在征讨南越。南越包括现在的岭南和越南北部,当时的广东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但秦朝君臣志在开疆,派出大军,建立桂林、南海、象三郡。项羽、刘邦逼近咸阳时,南越部队的主帅任嚣病卒,赵佗继为主帅,但是身为秦宗室的赵佗没有回救,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直到子婴出降,楚汉争霸,赵佗凭借手中的兵力在天南自立为帝,定都番禺(今广州),建立南越国,即为南越武帝。
南越国号称“东西万余里”,其实并不大,但易守难攻。为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汉高帝、吕后都曾对赵佗威逼利诱。赵佗高瞻远瞩,看清形势:所谓威逼,无非就是派兵来打,但南越以前秦锐兵守岭南地利,无惧汉军;所谓利诱,请问又有什么利能比当皇帝更诱人?汉高帝曾派大夫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一度接受册封,对汉称南越王,但对内仍称皇帝,保持着独立王国。吕后摄政时双方关系紧张,汉朝派大军征讨,可惜还没过岭南就病死一大半,就更不可能取胜了。有了胜仗做后盾,赵佗底气更足,不但重新称帝,而且周边很多归附汉朝的南蛮部族纷纷转投南越。文帝继位后积极改善关系,派人修葺赵佗在河北的祖坟,又派陆贾再度出使,反复交涉。最后穷鬼皇帝赵佗终于被诚意所感,再次撤去帝号,接受册封。从此双方相安无事,保障了汉帝国南方边境的安宁。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朝大举讨伐四边,才将南越国彻底攻灭,改制成郡县。
身后是——汉并天下
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六月,汉文帝驾崩,享年四十七岁,在位二十五年。无疑,汉文帝是历史上最值得景仰的好皇帝之一,他的个人品行、治国方针几乎无懈可击,受到后世一致推崇。更重要的是,他身后这个帝国,是中华民族走进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的王朝。秦朝虽然完成了第一次形式上的统一,但由于理论过于超前,脱离了时代,以致二世而亡。尤其可怕的是,由于秦朝的失败,天下人对皇帝制度(郡县制的汉式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产生了严重怀疑,回归商周诸侯封建制的呼声很高。而汉王朝在秦朝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了一个既符合民族性格,又适应历史阶段的汉式帝国,有力地维护了历史车轮继续向前。
而正是凭借汉文帝、汉景帝时建立的强大国家组织以及积累的雄厚实力,汉武大帝才能厚积薄发,痛击匈奴。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汉式帝国和第一个游牧帝国的首次交锋,以汉军的大胜告终!匈奴人部分逃到欧洲,部分滞留在东亚,数百年都未能恢复元气,为中原王朝的继续发展留出了重要的时间和空间。不仅是北方草原,大汉天威广布寰球,全世界都诚服于东方的伟大文明。成功的汉帝国,其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无疑是后世最适用的范本,中国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总结改进,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高速向前。所以说,后世之有强盛的中华帝国,既蒙秦朝的理论设计,更承汉朝的实际运用。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汉朝成功的重大意义。可以这样说,汉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用人身依附关系,而将上亿人直接置于一个统一帝国的治理下。不是上亿的附庸,而是上亿的国家公民!这上亿人除了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皇帝外,所有人理论上都是互不隶属、互相平行的国家公民。如何直接管理这么大人口规模的公民,如何通过行政体制和组织结构的设计让人身平等的公民相互管理?西方人可是在学习了中国现成的经验后,也才在二百年前在千万人口数量级的国家真正做到啊!我真的很难描述,两千多年前在上亿人口数量级的国家第一次做到的人到底有多么伟大。
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显然不是人称“粗人夫妇”的汉高帝和吕太后组合。太祖是打天下的,如果继续玩粗,汉朝不会比秦朝长几年。能让一个王朝国祚连绵,必须靠太宗塑造正确的国家形态。
当然,我们也无意把汉文帝吹成天上有地下无的神人,任何人都有历史局限性,甚至整个汉王朝在历史进步方面也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汉文帝为筹集资金,向民间出售爵位。而汉文帝的经济政策也非十全十美,超低的田赋让土地兼并变得更加容易,下放铸币权也造就了邓通、刘濞这样的金融寡头,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当然,如果提高田赋,也会造成大量中小农田主破产,同样会促进土地兼并。后世颂扬文景之治的伟大成就,称粮食堆在仓库里面吃不完,不得不加盖新仓;库府里的钱币堆积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多得无法统计。这在大多史学家看来是积贮丰厚的表现,但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是过于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利于拉动内需。当然,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至今未能解决的分歧,我们又岂能用以苛责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不过最严重的还在于汉文帝包括整个汉王朝都没有彻底解决先秦贵族社会的残余影响——尽管我们并不认为某一两个人甚至某一两个朝代就可以解决。汉朝虽然终结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先秦贵族,但又分封了一些新贵族,即便铲除这些异姓王侯,刘氏宗族仍实施分封。汉朝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分封的范围,但分封仍然存在,我们可以略览汉文帝身后的历史来评判这种影响。
文景之治积累了深厚的国力,汉武帝要做的是把积攒提取出来,他的两大方针对后世影响极大。首先是改“无为”的道家思想为“大有为”的儒家思想,以至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此后一以贯之的主流治国理念。其次是任用有严重凯恩斯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桑弘羊主政财经,收回铸币权,实施盐铁专卖、衡平均输。我们说是提用也好,搜刮也好,总之就是改用一套有利于敛财的经济政策。虽然儒家认为这是国家在与民争利,但现代国家无不使用,亦不足为奇。不过汉武帝倾尽国力,大战匈奴,毕竟对国内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破坏。晚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轮台宫颁罪己诏,他没有炫耀赫赫武功,而是为自己给百姓带来战争的苦难向天下谢罪。司马光认为汉武帝做了很多坏事,不亚于秦始皇,但是能够主动罪己,仍然体现了一位伟大君主的宽广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