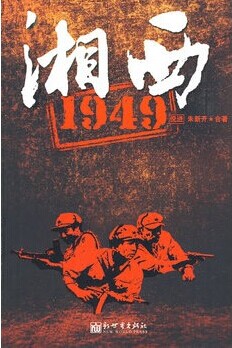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铺设,将荒原拉到了大都市的隔壁,而印第安人也被迫再次面临白人们令人不安的接近。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铁路则意味着一种更加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中国的版图更加广阔,但与印第安人统治的国度不同,这里很少有人迹罕至的地区,除了不适合生存、因而也不适合修建铁路的高原和沙漠地区之外,其他地方都有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严密的统治机构。白人们的介入不再会没有阻力,但这种阻力意味着其后的商机也是非同寻常的。在内陆深处的人们尽管坐拥巨大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却还局限于自给自足、自我依赖、缺少商品交换的生活。从他们身上不仅能获取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他们的购买力一旦被开发出来,也将是一个容量无法估计的潜在市场。
另一方面,面对幅员辽阔的国家,连遭洋人和太平军重创的清政府统治力已经大大下降,而良好运行了几千年的官僚层级制度在千古未有之变局面前也力不从心了。电报的虚拟性无法弥补路途的间隔,而铁路却能够保证政府控制力的提升,被铁路拉近的距离使得官僚们和老百姓都脱离了“山高皇帝远”的自由生活,运送粮草、军械乃至士兵的能力也使铁路的军事意义变得越来越显著。
尽管修建铁路有如此多的好处,但让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在中国,具有实力修建铁路的不只有漂洋过海而来淘金的白人。中国人即使缺乏技术和资金,但是却有着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集权结构,虽然没有私营企业能够承担修建铁路这样巨大的工程,全国性征收税赋的政府确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金主。而且,西方人带来的合股方式的优越性也渐渐为中国的商人们所认同,合股募集的资金也能够与财大气粗的欧美人的钱箱相抗衡。一旦几方人马都认识到铁路这条动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明白控制铁路就是控制了内陆的道理,那其中的争斗就可想而知了。
简单来说,在中国修建铁路的商机是任何人都垂涎的。有财力修建铁路的外国人、朝廷以及联起手来的商人们都觊觎着这块肥肉。正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使修建铁路这一桩造福国家的大好事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颠覆政权的惊天惨剧。
革命与改革
宣统三年,也就是公历1911年的第5个月,注定是多事之秋。
8日,清政府颁布了《新订内阁官制》,即所谓的“责任内阁制”。根据这种新制度,原来处于机要位置的内阁和军机处被裁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所谓新内阁。
这次改革是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强烈要求之下,清政府做出的让步。去年9月,各省的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包括: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具有鲜明民主意义的关键性措施。而来自奉天的激进代表更是申明,第二年必须召开国会,他们还认为军机大臣的责任不明确,要求设立责任内阁。
这些颠覆性的制度居然能够被“腐朽愚昧”的清廷所接受,受革命逻辑支配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根据他们对清政府思维的揣测,清廷的这些妥协都是他们为了拖延时间所玩弄的把戏,这个内阁完全是一个骗局,因为内阁大臣13人中,满洲贵族占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这是个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革命的逻辑认为,这个内阁的成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表明了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从而抵制革命。
但不管它的实质如何,新内阁的成立的确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有时候,名义上进步的意义并不比实际进步的意义小多少。清政府做的“名义上”的事情有很多,从“预备立宪”到“资政院”的设立,再到现在取代君主独裁的军机处和旧内阁的新内阁。如果要说所有这些思路清晰、一以贯之的“名义上”的妥协都是清政府的欺骗,那革命者们的逻辑可能是太过偏执了。如果放下革命意识形态的偏见,我们从更加心平气和的态度去看,虽然清政府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并因此而使这些变革具有“名义上”的性质,但要说这种渐进的、被迫的变革永远只会停留在名义的地步,那只是一种建立在不太靠谱的阶级论与暴力革命论之上的纯理论而非历史性的推测。
简单举个例子,如果不是1910年9月份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上发出的呐喊具有实际作用,那新内阁也未必会成立。单单这一事件,就足以说明,清政府被迫设立的“名义上”的资政院起到了实际的作用。世界历史已经给予了我们无数的例证说明,在从君主到立宪的进程中,很多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许多制度看似是“名义上”的,看似是欺骗,但却无法回避其作为一种进步的本质。英国在19世纪的民主改革,都是资产阶级受到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而被迫推行的,但这些渐进的改革最终成就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如果眼光长远一些,清末的立宪派也会欢迎这种哪怕是“名义上”的变革,至少他们从此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和机构去抨击独裁。而且,他们有理由期待这些“名义上”的制度像以往一样逐渐变成为实际。
事实上,这个新内阁也并没有像革命派想象得那么糟糕。参加内阁的皇族大都是些有名的政治改革派,像总理大臣奕劻虽然是个贪官,中饱私囊的勾当干了不少,但却是个公认的改革者,他甚至公开主张三权分立;而载泽、溥伦、善耆、绍昌同样也是热心的宪政实践者。同时,这些内阁里的皇族大臣也是满族权贵当中最有学识的成员,政治倾向相当开明,甚至暗中与梁启超等“逆党”私通款曲。当然,要让掌握朝政的满族亲贵们乖乖地把权力交给立宪的或革命的汉人,那不太现实。但这些同情立宪的贵族们至少可以分出皇帝的权力归于内阁,变君主独裁为内阁独裁。如果资政院日后再闹得厉害一些,甚至连国会都设立了,那开明的贵族们会不会将权力放到更多人的手中呢?
退一万步来讲,不论满族亲贵们是否有意推进立宪,这次新内阁在机构的设置上,尤其是阁员分部等方面,对推进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还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职责不清的军机大臣的权力被分配到了若干有着明确权力使用渠道的大臣手中。盛宣怀就分到了其中看似平凡却决定了清政府命运的一杯羹。
这个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就替自己以及清廷找到了掘墓人。
1911年5月9日,清廷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
按照革命逻辑的演绎,这条政策的出台,导致了投资铁路的商人们的不满,然后清政府进行弹压,这就引起了保路运动,最后就是该年的重头戏——武昌首义的上演。
但是如果不解释一下这条政策为何出台,其谋划者是基于何种考虑,那对于清廷的当事人来说,是有些不公的。
“铁路国有”中的这个“国有”指的是铁路干线国有,因为支线很多是洋人出钱建造的,你说国有就国有,人家哪里能答应。所以,要收归国有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办的铁路干线。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铁路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收归国有未必是一件坏事,而就其主事者摄政王载沣的本意来说,“铁路国有”应该是一项造福老百姓的“民心工程”,因为在当时,很多搞商办的铁路公司,比如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名义上是商办,实际上是靠对农民搞强行摊派来筹集资金。这种摊派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们当然不乐意了。而且,这些征集来的钱又没有真正用到修铁路上,这些年修成的铁路中,绝大多数都是官办公司或者洋人建成的,商办公司几乎毫无建树。拿川汉铁路公司来说吧,成立了六年,集了一千多万两银子,可是路只修了十来公里,倒是把三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扔进了股市去搞投机,结果亏得连爹娘都不认识了。
按照载沣的想法,实行“铁路国有”,停止向农民摊派租股,减轻农民的负担,应该得到农民的拥护才对啊!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向外国借款的方式继续修路,由国家职能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规划,见效自然就比较快,那对国家经济发展,对各地绅商兴办实业,都是大有好处啊!
可是,涉及精明的商人们利益的事永远不会简单。
热情的外国人
商人们大规模介入铁路修建是在1903年。在这之前,洋人在中国铁路修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自己直接修建了很多铁路,占了中国铁路总里程的很大份额,而且他们还通过参股、借款、抵押等方式加入到了热火朝天的铁路建设之中。鉴于他们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讲述辛亥年中国商人与铁路之间尴尬的故事前,我们还得回头先来看看洋人们在中国的铁路事业中所起到的作用。
基本上,从19世纪60年代寻求在中国架电报线的同时,列强们就已经开始打中国铁路的主意了。1862年,被李鸿章称为“外托柔和,内怀阴狡”的英国翻译梅辉立,就在广东提出“由粤开铁路入江西之议”。但经过勘察,这项“工程过大,事遂中寝”。
1863年,正当清廷和洋人携手攻打太平军占据的苏州时,以英国怡和洋行为首联络了英、法、美三国的27家洋行,向李鸿章索要修筑上海至苏州间的铁路权。外交嗅觉向来敏锐的李鸿章意识到“三国同声造请,必有为之谋者,未必尽出于商人”,他们肯定有后台老板,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864年,英国人斯蒂文生为英国怡和洋行拟了一个所谓“综合铁路计划”,很有心地规划了一套中国铁路网。他打算修建上海—汉口、汉口—广州、汉口一四川—缅甸和上海一天津一北京四条干线以及三条支线,这样就能把广州、上海、汉口、天津4个重要商埠与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印度连成一片,从而“打开进入中国的后门”。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当局的疑虑,总理衙门就把这个计划束之高阁。斯蒂文生本人也只得泱泱离开了中国。
但洋人们并没有死心。1865年,一个叫杜兰德的人竟然擅自在北京宣武门修建了一条小铁路。总理衙门觉得这种行为太过凶险,就命令沿江沿海的各将军督抚对洋人修铁路的请求,都要严加防范,而且统统都要坚决拒绝。总理衙门的看法是这样的:“山川险阻,皆中国扼要之区,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以任便往来。”这还是从国防考虑的,是为了避免洋人们太过轻易地在中国行走。当时在江苏担任巡抚的李鸿章也回应说:“铁路费烦事巨,变易山川”,中国“断不能允”。而其他封疆大吏,比如江西巡抚沈葆桢、两广总督毛鸿宾则从有伤民间庐墓、夺民生计和怕引起伏莽滋事、影响社会治安等方面对这种企图加以反对。
洋商见了这种声讨的阵势顿时傻了眼。他们本来不过是纯粹为了建立商业关系而铺设的基础设施,不仅便利洋人,华人也能沾到利益,但这种要求竟然被这帮不识好歹、不懂商务的官僚们拒绝地一干二净。眼看着谋财之路要断送在中国的官僚手上,洋商们不得不找来了他们的政府人士参与到这场争论之中。
1865年11月6日(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局外旁观论》,第二年3月5日,英国公使馆参赞也在公使阿礼国的授意下向总理衙门呈递了《新议略论》。这两篇文章都涉及了新政改革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特别论及了铁路修筑的问题。两篇文章都认为铁路事业是清政府“应学应办”的重要事情之一。一则“做轮车以利人行”,对中外都有利益,二则“各省开设铁道飞线……各国闻之无不欣悦”。因为在中国“添设铁路和电报……对于在华自由发展外国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清政府当然不高兴外国人对自己的政策随意指摘,就把《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作为反面典型,于1866年4月让有关督抚和通商大臣“专折密奏”进行批判。最后洋人们在清廷上下的一致反对声中,还是没有能讨到铁路上的便宜。
但英国人还是不甘心,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向上海道沈秉成含含糊糊地提出修筑通至吴淞道路的请求,在这里,“铁路”被“道路”掩盖了起来。沈秉成果然中计,觉得这既然只是一般修路,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于是当场就予以批准。
吴淞铁路通车典礼
修路的请求一得到允准,英国人马上着手开始修铁路。在风气未开的沪郊地区,土地要价不低,风水庐墓的问题也很麻烦,工程进展缓慢,最后还是停顿了下来。后来几经周折,到了1875年,总算招足股金,在英国购买了铁轨与机车,一起运到上海。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