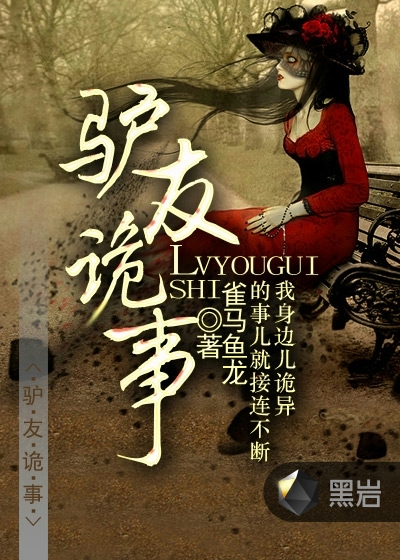她的事-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个英俊的男孩子,他们以友情的名义在一起两年,彼此折磨伤害互相讽刺,继而奔向各自的命运。
那时的她敢穿很短的白色牛仔裙,眉目里张扬着骄傲,还有横溢的才华,以及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自卑感。
她用手拢了拢长头发,放下那张习题纸,骑车去那时的学校,走到高二三班的教室外。里面的高中生好奇的看着窗外的她,并因此被讲台上的老师呵斥。她不知为什么就笑了,那个老师也教过自己的,她一点都没有变。而靳勒从前在窗户玻璃上写的我心永恒早就不见。也许被擦掉也许那块玻璃被换掉,反正就是没有了。
她想起复读那一年冬天他托人带给她东西还有他宿舍的电话,那一晚上,她开心极了,恨不得立刻给他打。可是那时候她没有手机,她要打电话就只能去排队等公用电话。她那时从来没有想过电话通了要说什么,她只是觉得她一定要打过去,因为自己没有被忘记的喜悦在心里一点点膨胀着,让她感觉自己快要飞起来。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和他说上话,每次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比如说电话卡的使用范围触及不到他所在的城市,比如他刚好不在。也许这是老天刻意的安排,她在这种安排下越来越淡漠,开始的快乐像泄了气的热气球,一点点坠落。而他永远不知道她曾那么疯狂的冒雨去买电话卡。然后在电话亭外排长长的队,直到深夜。得知电话卡无法使用后,翻墙去校外打。冬天的寒气让她的膝盖又酸又疼。可心里却是暖暖的迫切
他不知道她曾经那么努力的想要靠近他。
却终究触不到。
高三毕业后,他不见了。她曾问过他,你会复读吗?他说,以我的成绩,也只能复读了。她心里说,我陪你。
那一年高考,她放弃了语文的作文,她对所有人说,她不舒服,考语文时睡着了。成绩下来后,她刚够二本线。她把自己锁屋子里,父母哄朋友劝,都不出来。她不是难受自己的成绩,不开心,是因为他不见了。
他又没给你什么承诺;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一厢情愿的奉献还以为是牺牲,可笑的小心思。
想在一起,是不是?你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天。
你放弃了最有把握的作文,你放弃了自己的前程,可依然什么也得不到。
那时的她,那么勇敢,那么甘心的认为前程没有爱情重要。
他去上了大专,因为家里人认为他就是再复读一年也不会考上多好的学校,就不浪费时间了。
她去复读,第二年去海南读大学。
住也如何住,去也终须去
2004年
大三前半期,七夕一改往年懒散,开始为以后做打算。
她还记得那天接到家里人打得电话时,她还在悠悠然的看着《资本论》。电话那头的叔叔只是说,你回来一下,家里有点事。之后再不肯多说。她心里不安大于讶异。打父母电话,均是无法接通。她心里隐约察觉到了什么。打电话给祖父祖母,心里的猜测被电话那头的混乱证实。她有一丝茫然,像是刚睡醒时的混沌,很长时间她都没有动,看着眼前厚厚的书,怎么也反应不过来。
“我们有规定,没办法批你长假。”系办公室里那个中年男人一本正经的说。“李主任,我真的有急事要回家办。”李姓男子好整以暇的看着她,问,“什么急事,要一个月假?”七夕低着头,沉默好久说:“我们家人去世了,我回去办丧事。”中年男子不相信的说:“办丧事,轮的到你吗?你们家大人呢?”七夕低低的说,“锅炉爆炸,我们家人都死了。”对方愣了一下,说:“既然都死了,你急着回去又有什么用”
七夕看他一眼,抓起桌子上东西就摔,“你他妈还是不是人?”办公室外的尹之洲紧忙进来,拉住情绪失控的她。说,“你回去,我帮你。”
她站在街上,单看到被炸得坍塌的店也想得到里面的人会怎么样。她回来时,亲戚们正在装殓尸体,她看了一眼,爸妈弟弟三个人已经分不出来谁是谁了。战场上的血肉横飞竟然也会出现在现实中。
她趴在路边干呕,呕的胆汁都出来了,就是哭不出来眼泪。
她的父母,虽然算不上什么善良的人,但也从未做过什么缺德的事,为什么会落个这样的下场?
办丧事的时候,她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想哭,可脸上的表情已经由不得自己了。大家都以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傻掉了。披麻戴孝的她抱着父母和弟弟的照片,那曾是张全家福,照相馆把她摘了下去,从此阴阳相隔,天人永别。
“那孩子以后算是吃穿不愁了。保险公司赔的钱和锅炉厂赔的钱足够她好好生活了。”
“她爷奶总也得分点吧?”
“纪老三真命苦,店刚有点起色,这么死了。真没福气啊。”
“这么个死法纯粹给闺女挣嫁妆了。”
“这姑娘也可怜啊,才二十出头,就没个家。”
她木然的听着人们在她旁边说着,议论的是同情还是扭曲的羡慕?
她的奶奶,已经哭昏过好几次了。
她想起自己曾对母亲说的狠话,“我一点也不怀疑,灾难来时,你会带着弟弟先走。”那时候,他们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做生意,每个晚上回去时,母亲总是骑车带走弟弟。让她走夜路。
现在好了,他们真的走了,只剩下她一个。
她和父母感情向来淡薄,母亲想要儿子,却先有了她,对她鲜有好脸色。父亲终日在外奔波,一回家,就和母亲口角,他们彼此恶语相向,有一方骂累了妥协,另一方却不肯放弃,持续的咒骂,像是接力棒。等到其中一个有觉悟想为和解做努力时,另一方却不依不饶,回以刻薄的话。他们彼此熟悉,知道对方的软肋,每一句话都像神枪手击中靶心一样刺向对方最柔软的地方。七夕夹在中间被骂傻骂笨骂了十几年,瞎子聋子一类的称呼从未断过,却从未被称为哑巴过。她说的话,狠且准,不像个孩子。在父母的战争中,她开始是害怕,后来是调停,再后来是不耐烦,再后来是听之任之。
她三四岁的时候,一次父母打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爸爸一巴掌打在她脸上。她鼻子开始流血,她妈妈慌了,顺手拿张纸给她擦。那时候家里条件很差,她妈用的是账本上撕下的纸,她一直记得那账簿纸在自己鼻子上摩擦的痛。
那时候她以为他们吵是因为她是女孩,可后来有了弟弟,他们依然吵。她抱着弟弟,看他们吵,打。她妈妈歇斯底里的叫,她爸爸吼,咒骂,摔椅子摔暖瓶。邻居们都在劝,她冷冷的看着,抿紧了唇,一言不发。
“我不过了!我喝敌敌畏死了算了!”她妈妈哭着喊,脸上的妆花的很难看。身边的人都去劝。
“你要喝就喝,敌敌畏在小屋的窗台上。”混乱的人群因为小姑娘一句没有感情的话安静了。
“我知道,你不想死。”她抱着弟弟进了屋。再不管外面的事。
现在的她,一个人呆在空旷的家里,她关好每扇窗每道门,家里的老狗一直跟着她,它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家里一直很混乱,它只知道对自己最好的小主人回来了,她不开心,它要陪着她。
“只剩你了啊,狐狸?”她看着它,轻声说。
“那我们就相依为命吧。”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
2009年7月23日
“怎么不用度蜜月?姐夫。”七夕看着眼前的男人,一阵恍惚,他是靳勒吗?
“叫哥好了,叫姐夫太生分了。”天成说。七夕低着头,没出声。
“再有三十九天,我们就认识满十年了。”
“哦?”七夕挑了挑眉。
“其实,我不是开学那一天才认识你的。”天成笑。
我也不是那一天认识你的。七夕想。
静寂的空气让两个人都闷的有点透不过气,他会来宾馆,是个意外。
“这些年,你有想起过我吗?”他问。她还是没有出声。
“一定没有吧?我找人给过你电话号码,给过你地址,只要你想,你就能联络上我。可一次都没有。”他苦笑。“而我,没有任何方式找到你,骆明铎他从来不肯告诉我你在哪你的电话。直到昨天,我才看到你,说起来我还要谢谢我妻子。至少,结个婚,让我见到你了。你不想见我,是不是?”
她定了定神,说,“你很奇怪,靳天成,你从前喜欢的是颜色,她去当兵,你跟着去当兵。你现在娶的是我表姐,昨天你还说在你心里她最美。你还来招惹我干什么?”
“我喜欢颜色?谁告诉你我喜欢颜色?”他激动的说。
“所有人都知道!”
“那我怎么不知道?”
“你……”她瞪着他,不说话。
“而且,我也没有因为她去当兵,我和她根本就没联系。我去当兵是因为我觉得上大专没前途,正好有征兵的,我就去了。”他解释。
“那又怎么样?你都结婚了?你这样是做什么?”七夕问,心里满是苦。
他不说话了,好一会儿,终于问,“我只想知道,你究竟有没有喜欢过我?”
“我要知道,这些年,我是不是在唱独角戏?”
“好吧,我也告诉你,你不是,我在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可是现在,你想让我怎么办?”
他走过来,拥她入怀。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温暖的地方,自己无数次伤心时梦到的地方。真的如此温暖,可却不属于自己。蓦地她想起表姐的笑脸,猛地推开他,冷冷的说,“勾引有妇之夫的事,我不擅长。”他迷惑的看着她,随即问:“那你擅长什么?”
“遗忘。”她看着他说。他盯着她,不知过了多久,说:“好吧,那就让我们来做一件你擅长的事。”他转身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大木盒子,塞她手里,说:“给你,我答应过的。”
她低着头,没有任何反应,他看着她,终于还是叹口气,转身上车,发动车子,走掉。这个世界,如果用心去找一个人,是一定可以找到的。天成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为什么自己后来放弃了去找她。自己并没有尽全力,不是吗当年没和她在一起,是觉得自己不配。现在终于配的上她了,却还是不能和她在一起。过去的十年里,自己想着她念着她,揣测着她会爱上什么人。以后呢?以后要怎样?忘是忘不掉的,可是又能怎么样?爱情这东西,并不是谁都要有的必需品。就这么算了吧。原来,总有些事是要不了了之的。
她抱着那个盒子,回到宾馆的房间,靠着门,就那么蹲着,紧紧地抱着那个盒子,她甚至都没有勇气打开看,隔了那么久,无论经历多少,她还是在乎他的,不是吗?
十七岁,陈小春的卡带,后面附着靳天成自弹自唱的《献世》,她听的时候,明明很开怀,却流下泪来。
十八岁,《乱世佳人》,她那时候喜欢《飘》喜欢的要死,一本书翻得边角都开了,还是看。他买了VCD,请她去家里看,她怎么都不肯。于是,那碟子从未被打开过。她试了试,居然能播,看到最后。郝思嘉对自己说,Tomorrow is another day。她看着漆黑的夜,睡一觉吧,醒来又是新的一天。
可竟是睡不着的,又好像是睡着了的。她还能看见那双红色的高跟鞋在面前晃,他写,你说过你希望二十岁时有人送你高跟鞋。那一年我大二,我在酒吧打了半年工,终于可以买给你,却不知道怎么送给你。我记得你的脚可不小,是九号的,对不对?哈哈。可惜,现在样式已经过时了。睡着的她嘴角微微的有笑意,那是双简单到没有任何装饰的鞋子。爱情永远不会过时。睡梦中的她想着。
2008年,那一年她26岁,他准备的是枚戒指,他写,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去救援,碰到了塌方。最绝望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从来没告诉过你我爱你。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永远也不知道这么帅气的我爱着你。那个时候,你爱不爱我已经不重要了。被救出后在医院呆着的时候,我想我要去买枚戒指,送给我想在一起一辈子的人,哪怕我并不能和她在一起。出院后我去挑戒指,七夕,我是真的想给你幸福。我去找你,我在海南呆了三个月,那个地方真热,很适合你这种怕冷的家伙。可是他们说你在上海;说你有男友。于是我乖乖回来,相亲,结婚。我以为我们再也不会相见,可是居然见到了你。我们重逢在一个瑰丽的时刻,那场日全食,天地都黑了,只有你,站在那里,眼睛里流光溢彩。我以为是做梦,可是天还是亮了。一切还要继续,是不是?就好像暑假总会结束,开学那一天总会到来。我不喜欢上学,但1999年的9月1号除外,因为那一天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看你和你说话,虽然那个开场白不是让人很愉快,可总算开始了。这些是为你准备的,从十七岁到现在二十七岁,十年的生日礼物。我说过,你以后的每一个生日,只要我知道你在哪里,我都会把礼物送到。可是,刚开始,不敢送,后来,却送不到。你真傻,有哪个男孩子会亲自己不喜欢的女生呢?我以为你明白,你还是不明白,你说你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