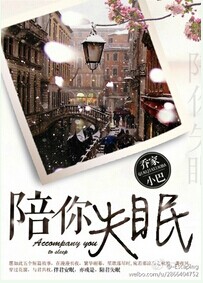陪你失眠-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想了想,阿秋和兰州姑娘的感情里,阿秋大抵是那个被橡皮筋弹到泪腺干涸的人。
“房子和车子的钱我都挣来了,结婚的事情也全全是我一个人在打理,不让她为了这个事情操一份心。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快要订婚的时候,又出了件大事。本来我留在兰州当会计,我父母就不是很乐意,特别是我妈,总觉得我们家吃了亏,受了委屈,但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她们家提出要我们家出六十万的彩礼,家宴上,我妈一气之下就把一杯酒泼到了她妈的脸上,说自家儿子几乎都是入赘了,彩礼钱居然还收六十万,呵斥她们家是市侩小民,霸道无礼,骂骂咧咧的。最后,两家人的脸皮干脆被撕得残破不堪。”
阿秋说完,就叹了口气,道:“其实我家也不是出不出这六十万,只是我父母憋了一肚子的火,终于在那天爆发了。说实在的,我那天看到我妈那副憋屈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那场家宴最后搞得不欢而散,自那以后,她父母就一直劝着她还是找个本地的嫁了,找了我这杭州人居然惹出了这么多事。”
“于是呢,你那兰州姑娘后悔了?”
我转过头,认真的端详着阿秋的轮廓。怎么说呢,往常他都是欢脱的逗比,笑的愉悦清爽,甚至没心没肺。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他那样皱着眉头,抽着香烟屁股头,一副颓废萧瑟的样子。我想,阿秋此时的表情,再给他加上一个络腮胡,一头长头发,一把吉他,他就是那种带着忧郁气质的街头艺术家了。
“嗯,后悔了。那天夜里她枕着我的臂弯,说了很多心里话,说着说着就泪眼滂沱。她说她的压力很大,低沉沉的阴霾压的她就像快要窒息一般。她不能对不起生她养她的父母,她不能离开兰州,跟着我走。那一夜我没有回话,没有挽回没有责怪,只是抱着她,一夜未睡。第二天,我看着她收拾行李,把衣橱里属于她的衣服全部装箱,而把我们一起买的情侣杯,情侣衫都留给了我一个人。她走了,屋子里顿时空荡荡的,我都能听到楼上那孩子的一颗弹珠落在地板上的声音,清脆却又冷酷无情。”
阿秋说到这里,啃着手里那早就发凉的的鸡大腿,恶狠狠的咬下了一块肉,快速咀嚼,然后吞咽,语句模糊的说道:
“她走之前,不知道其实我背着她把婚房都布置好了,她走之后,不知道其实她看中的那件白色婚纱已经送到我家了。其实,后来,每每当我看着挂在我衣橱里的那件婚纱,我想,其实她是自私的。自私到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她不知道,每每她用泪眼看着我,求我宠爱她心疼她可怜她时,我的心里都在滴血。我也承受着我父母和她父母给我的压力,我也希望能讨她父母的欢心,早日让四位老人家的关系变好,迎娶她进门。可是,她说一句不要,就全部都不要了。”
顿时,我不知道怎么安慰阿秋,我突然想起了曾经的我,对一个人那么的爱,奉上一颗真诚的心任其践踏,到最后却是一片触碰不到的虚无。那种大梦初醒的感觉,那种独角戏演完了的感觉,可悲却又可笑。那会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大手勾住了阿秋的脖子,什么都没说,借了个肩膀给阿秋靠,而且我还能感受到空气中多了三分咸味的水汽。
“万里长征走到头,到会宁会师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友军在那里等我。我一个人在终点木木呆呆的守望,才发现到头来都是我自己的一场美梦。”
阿秋说完,把手里的竹签往一旁的垃圾桶里投掷,吟了一句李白的诗句,道: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02
“阿秋,没关系,你我都还年轻。”
说完,我拍了拍阿秋的肩膀,而阿秋只是举起了手里的啤酒,向我敬了一杯。
“我和她分手后,我们全家人都很开心,特别是我父母。我把兰州的房子和车子都转手了,收拾了包袱行礼,离开了兰州。临走前,我没有去见她,我想,与其相见,不如不念。我回到杭州后就开始精算的工作。至于她的那件婚纱,我一路从兰州带到了杭州,直到我发现,我真的释怀的时候,我把它送给了我一天天想嫁人的学妹。”
“释怀?怎么说?”我问着阿秋,想了想他当时一路向西,从杭州追到西北兰州,着实让人遗憾。
“倒也不是不爱她了。有时候,爱不爱,能不能和在不在一起不是一码子事儿。说实话,我很爱她,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让我这样费尽心思,可是,若是从一起过活这个角度考虑,她绝非我的佳人,我也绝非她的良人。”
阿秋说完,便对着我大笑三声,捏着我那张他形容是苦瓜一样的脸,道:
“蔻蔻,你是成年人,这点事情你该懂才对。”
“懂是懂,听完你这经历,我只是觉得两个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长相守,实在不容易。就像你说的,爱不爱和结婚不结婚是两码事儿,这世间有那么多人秉持着差不多,凑合这样的态度是结婚。今后,我要不我也找个差不多的算了,那种死生挈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太难了。”
言毕,阿秋便用指关节打了我的脑门,赏了我一颗“毛栗子”,教训道:
“不要随波逐流。我想,总会有的,不要心急。”
“真的会有吗?”我喃喃道,问着阿秋。
彼时,我和阿秋就像两个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人正在互相吐露着心里的声音。阿秋被我这么一问,先是迟疑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我想,他这大概是在安慰我,也在安慰他自己。
“蔻蔻,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我记得阿秋是这么问我的。
“走出失眠。”我回答了他这么四个字。诚然,失眠症困扰了我太久,就像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让我倍受煎熬。
“你呢?”我反问阿秋。
“我只求无牵无挂。”
我看着阿秋的侧眼,风吹拂着他的碎刘海,遮蔽着他那双有些暗淡的眼。
我深深的叹了口气,用一米六的个子搂着阿秋那一米八的个子,说着:“祝你我梦想成真。”
后来,我和阿秋一边走一边聊了很多的事情,聊我的过去,评我的过去,聊他的过去,评他的过去,也算是知心好友敞开心扉,大谈彻谈。对于我的事,阿秋也有他的见解。说实在的,他真的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异性朋友。
离开兰州后,我们又去银川呆了几天,可是,母亲的病恶化了,得动一个大手术。在晚春的时候,父亲打了个电话给我,跟我说了母亲的情况,为我订好了机票,让我立刻回家。在外旅行了三个月,本来我还想跟着阿秋去西藏,去找他的信仰,可是,事与愿违,我还是得回家去照顾生病的母亲。
那天阿秋送了我去机场,帮我拎着包,陪着我在候机室等了四个小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和他是准备分开去异地的情侣。等了一会儿,我便起身,背着我那只登山包,准备登机。阿秋愣愣的跟在我的身后,还挠着头发,说什么我这一走,他孤身一人什么的还挺不习惯。
走到登机口前,我对着身后的阿秋,说:“阿秋,我要走了。”
“还能再见面吗?”阿秋就简简单单的问了我一句。
说难听些,我和阿秋不过是萍水相逢,在旅途上相识的过客罢了。
听到阿秋那么说,我便扑哧一笑,道:“当然能了,阿秋,你在想什么?”
顿时,阿秋继续挠头,然后笑着低了低头,说着:“没什么,行了,你快登机吧。”
“嗯,再见了,阿秋。”我和阿秋认真告别,顿时,心里突然觉得酸酸涩涩的,脑袋里想着的是李白那首《赠汪伦》里的那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我想了想,没有回头,径直往登机口里走,我原以为阿秋也会背过我离去,谁知他唤了我的名字,喊道:
“蔻蔻,我在西藏等你。”
我转身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的阿秋是最帅的,纤长的身材在旅客中显得有些夺目,双手插着裤子口袋,背着他的灰布包,碎刘海被撇到了一边,单纯的笑着,露出一口皓齿,绝对不是那个我印象里的烤串青年。
我朝他点了点头,挥了挥手,应道:“好。”
然后转过身,给工作人员检票,随着人潮一起登上飞往家乡的飞机。自那一次后,阿秋依旧一个人在各地转悠,没有回杭州,而我也常常跟他互发邮件,和他分享他在旅行中的趣事。但是,自从我和他分别后,他没有去西藏,他跟我约定,如果十年以后,我依旧失眠,他依旧无牵无挂,那两个人就干脆一起去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西藏一遭。
03
早晨,我精心装扮,穿上了一身简单的休闲装,卫衣加黑色休闲裤,穿了双纽巴伦的运动鞋,背了个杰斯伯的背包,看上去应该还不够二十六岁。
我和阿秋约定在滨离宫庭院景区的门口碰面,我早到了十分钟,便立在那边抽烟,玩手机。近来宫本先生忙的不可开交,先前只是熬到凌晨下班,如今干脆住在公司里了,天天开会,还要熬夜。于是,我干脆不去打扰他了,一有休息的机会,我就让他好好休息,把睡眠补足,不要累坏了。我爱上宫本先生了吗?我也不知道,或许是爱上了吧,但我又不愿意主动去揭开这一切。
等了十分钟,载着阿秋的那班车迟迟赶来,阿秋蹦蹦跳跳的从车上下来,还是几年前的那副逗比样子,一点都没变。我先看到了他,朝他招手,他便愉快的向我奔来,欢腾的像一匹脱缰的小马。还没等我回过神,他便大手一勾,手臂勾上了我的脖子,一副哥俩好的样子。其实,换做是别人对我做这样的动作,我可能觉得有些不自在,可是阿秋不一样,他是我交心的朋友。
滨离宫全称滨离宫恩赐庭院,面临东京湾,江户时代是个猎鹰场,到了明治的时候成了皇室的离宫,二战后变成了公园。付完三百日元的票价,我和阿秋便一起在滨离宫里游玩。湛蓝色的天空,小桥流水,异形的古树,湖中的倒影,冬日滨离宫的景色让我醉于其中。潺潺流水划过惊鹿,沉重敲打着石壁,发出一声深远的响声。与以前不同的是,如今的阿秋的胸口多了一只单反,看到绝佳的美景,他便按下快门,咔擦咔擦的拍下一张张漂亮的照片。我问起阿秋为什么突然会这样时,他说大抵是受了我的影响。我们步过花间,行过流水,在精致清幽的庭院里礼貌性的低语。
后来,我带阿秋走到了茶屋,请他品尝日式抹茶和糕点。阿秋极不自然的跪在了榻榻米上,没一会儿,他就捂着自己的膝盖,跟我说那感觉简直和膝盖上中了两箭一样。当然,我也没有为难他,干脆和他一起盘腿坐在了榻榻米上。纸门外有一株樱树,枝桠上光秃秃的,没有开花。我指着那棵樱树,笑着对阿秋说:
“其实你应该春天来,春天的时候,东京满街都开满了粉红色的樱花。”
“我觉得冬天的日本也不赖。”
阿秋说完,便豪饮了一口抹茶,然后眉头一皱,一个劲的跟我嫌弃抹茶太苦,而我只能说他的喝法不对。
盘着腿的阿秋用手撑着下巴,玩弄着手里的茶碗,问着我:
“蔻蔻,这些年,你在日本混得如何?”问到这个问题,我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说实话,在日本的这些年,有苦也有甜,从一开始懵懵懂懂,瓶颈期到现在的习惯,其实是难以言说的。
“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写些稿子,做些访谈什么的。总的来说,还算不错。”
“蔻蔻,你还失眠吗?”阿秋继续问着我。
我毫无犹豫的点了点头,承认我每晚还是受着失眠症的苦。
阿秋看完我的反应,便乐呵乐呵的笑了,然后伸了个懒腰,对我说:
“你啊,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那你呢,还是无牵无挂吗?”我这么一问,阿秋看了我一眼,沉默着摇了摇头。
良久,阿秋轻轻的啜饮了一口抹茶,苦笑道:“蔻蔻,我可能已经办不到无牵无挂了。”
或许是阿秋刚饮完那一口苦茶,我的错觉告诉我,空气里弥漫着一点点苦涩的味道。正当我想问阿秋是不是找到心仪的妹子时,他打断了我,笑着道:
“结束日本以后,我准备回杭州工作了。”
我之前说过,阿秋是个名副其实的浪子,这些年一个人行走在外,把自己赚来的老婆本全部都挥霍完了。可如今,这个浪子要回头,要回家了。我想,或许他的心里放下了什么,或许又抓住了什么。
“你是该回去看看了。”我笑道。
“你呢,和你那丧尽天良的劈腿前男友如何了?还在想他吗?”阿秋问着我。
我迟疑了一下,啜饮了一口抹茶。我突然觉得这口抹茶实在苦,比我曾经吃到的任何苦味的东西都苦。
“这个月,我准备和他见一面,甚至过一夜。”
说完,我才发觉这么一句话原来是如此的难以启齿。
阿秋的表情很难看,脸色和他身后的白墙一样白,眼睛瞪得很大,好似那两颗黑珍珠般的眼珠儿都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