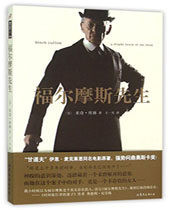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周这些妩媚的入侵者在她们夺走的胜利品名单中,又添上了一位重要人物。圣西蒙勋爵二十多年来从未堕入情网,现在却明确地宣布即将与加利福尼亚百万富翁的令人一见倾心的女儿哈蒂·多兰小姐结婚。多兰小姐是一位独生女。她优雅的体态和惊人的美貌在韦斯特伯里宫的庆典欢宴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最近传说,她的嫁妆将大大超过六位数字,预期将来还会有其它增益。由于巴尔莫拉尔公爵近年来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藏画,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圣西蒙勋爵除伯奇穆尔荒地那菲薄的产业之外,一无所有,所以这位加利福尼亚的女继承人通过这一联烟使她由一位女共和党人轻而易举地一跃而成为不列颠的贵妇,显然这不只是她这一方面占了便宜。';”
“还有什么别的吗?〃福尔摩斯打着呵欠问道。
“噢,有,多着呢。《晨邮报》上还有另一条短讯说:婚礼将绝对从简;并预定在汉诺佛广场的圣乔治大教堂举行;届时将仅仅邀请几位至亲好友参加;婚礼后,新婚夫妇及亲友等将返回阿洛伊修斯·多兰先生在兰开斯特盖特租赁的备有家具的寓所。两天后,也就是上星期三,有一个简单的通告,宣告婚礼已经举行。新婚夫妇将在彼得斯菲尔德附近的巴克沃特勋爵别墅欢度蜜月。这是新娘失踪以前的全部报道。”
“在什么以前?〃福尔摩斯吃惊地问道。
“在这位小姐失踪以前。”
“那么她是在什么时候失踪的呢?”
“在婚礼后吃早餐的时候。”
“确实,比原来想象的要有趣得多。事实上,是十分戏剧性的。”
“是的,正是由于不同寻常,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们常常在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失踪,偶尔也有在蜜月期间失踪的。但是我还想不起来有哪一件象这次那么干脆的,请你把细节全说给我听听。”
“我可有言在先,这些材料是很不完整的。”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们凑起来。”
“就是这样,昨天晨报上的一篇文章谈得还比较详细,让我读给你听听。标题是:《上流社会婚礼中的奇怪事件》。';罗伯特·圣西蒙勋爵在举行婚礼时发生的奇怪的不幸事件,使他们全家惊恐万状。正如昨天报纸上简要地报道的,婚礼仪式是在前天上午举行的;可是直至日前,始有可能对不断到处流传的奇怪传闻予以证实。尽管朋友们设法遮掩,此事却已引起公众的极大注意。因此对已经成为公众谈话资料之事,故作不予理睬的姿态,是毫无裨益的。
婚礼是在汉诺佛广场的圣乔治大教堂举行,仪式简单,极力不予张扬。除了新娘的父亲,阿洛伊修斯·多兰先生、巴尔莫拉尔公爵夫人、巴克沃特勋爵、尤斯塔斯勋爵和克拉拉·圣西蒙小姐(新郎的弟弟和妹妹)以及艾丽西亚·惠延顿夫人外,别无他人参加。婚礼后,一行人即前往在兰开斯特盖特的阿洛伊修斯·多兰先生寓所。寓所里早餐已经准备就绪。此时似乎有一个女人引起了某些小麻烦。目前她的姓名未详。她跟随在新娘及其亲友之后,试图强行闯入寓所,声称她有权向圣西蒙勋爵提出要求。只是经过长时间煞费其力的纠缠,管家和气役才把她撵走。幸亏新娘在发生这件不愉快的纠纷之前已经进入室内,同亲友一起就座共进早餐,可是她说突然感到不适,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她离席久久不归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她父亲即去找她。但据她的女仆告知,她只到她的卧室逗留片刻,很快拿了一件长外套和一顶无边软帽,就急急忙忙下楼到走廊去了。一个男仆声称他看到一个这样装束的太太离开寓所,但是不敢相信那就是他的女主人,以为她还和大家在一起。阿洛伊修斯·多兰先生在肯定女儿确实是失踪了以后,就立刻和新郎一起同警方联系。目前正在大力调查。这件离奇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然而,直到昨天深夜,这位失踪的小姐依然下落不明。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件事的谣言,认为新娘可能遇害。据说警方拘留了那个最初引起纠纷的女人,认为她出于炉忌或其它动机,可能与新娘奇怪的失踪有牵连。';”
“就这些吗?”
“在另一份晨报上只有一小条消息,但是却很有启发性。”
“内容是……”
“弗洛拉·米勒小姐,也就是肇事的那个女人,实际上已被逮捕。她以前似乎在阿利格罗当过芭蕾舞女演员。她和新郎相识已有多年。再没有更多的细节了。现在就报纸已发表的消息而论,整个案情你已经都知道了。”
“看来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放过。华生,你听,门铃响了,四点钟刚过一点儿,我肯定这一定是我们高贵的委托人来了。别老想走,华生,因为我非常希望有一个见证人,即使只是为了检验一下我的记忆力也好。”
“罗伯特·圣西蒙勋爵到!〃我们的小僮仆推开房门报告说。一位绅士走了进来。他的相貌喜人,显得颇有教养。高高的鼻子,面色苍白,嘴角微露愠意,有着生来就发号施令那类人所具有的一双神色镇静、睁得大大的眼睛。他举止敏捷,然而他整个外表却给人一种与年龄很不相称的印象。当他走路时,略有点弯腰驼背,还有点屈膝。头发也是如此,当他脱去他那顶帽檐高高卷着的帽子时,只见头部周围一圈灰白的头发,头顶上头发稀稀拉拉。至于他的穿着,那是考究得近于浮华:高高的硬领,黑色的大礼服,白背心,黄色的手套,漆皮鞋和浅色的绑腿。他慢慢地走进房内,眼睛从左边看到右边,右手里晃动着系金丝眼镜的链子。
“你好,圣西蒙勋爵。〃福尔摩斯说着站起身来,鞠了个躬。〃请坐在这把柳条椅上。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医生。往火炉前靠近一点,让我们来谈谈这件事吧。”
“你很容易就能想象到这是一件对我来说十分痛苦的事,福尔摩斯先生。真叫我痛心疾首。我知道,先生,你曾经处理过几件这类微妙的案子,尽管我估计这些案子的委托人的社会地位和这件案子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委托人的社会地位是在下降了。”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我上次这类案子的委托人是一位国王。”
“噢,真的吗?我没想到,哪位国王?”
“斯堪的纳维亚国王。”
“什么!他的妻子也失踪了吗?”
“你明白,〃福尔摩斯和蔼地说,“我对其他委托人的事情保守秘密,就象我答应对你的事情保守秘密一样。”
“当然是这样,很对!很对!一定要请你原谅。至于我这个案子,我准备告诉你一切有助于你作出判断的情况。”
“谢谢,我已经看到了报纸上的全部报道,也就是这么些而已。我想,我可以把这些报道看作是属实的——例如这篇有关新娘失踪的报道。”
圣西蒙勋爵看了看,“是的,这篇报道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
“但是,无论是谁在提出他的看法以前,都需要大量的补充材料。我想我可以通过向你提问而直接得到我所要知道的事实。”
“请提问吧。”
“你第一次见到哈蒂·多兰小姐是在什么时候?”
“一年以前,在旧金山。”
“当时你正在美国旅行?”
“是的。”
“你们那时候订婚了吗?”
“没有。”
“但是有着友好的往来?”
“我能和她交往感到很高兴,她能够看出我很高兴。”
“她的父亲很有钱?”
“据说他是太平洋彼岸最有钱的人。”
“他是怎样发财的呢?”
“开矿。几年以前,他还一无所有。有一天,他挖到了金矿,于是投资开发,从此飞黄腾达成了暴发户。”
“现在谈谈你对这位年轻的小姐——你的妻子的性格的印象怎么样?”
这位贵族目不转睛地看着壁炉,系在他眼镜上的链子晃动得更快了。〃你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的妻子在她的父亲发财以前,已经是二十岁了。在这时期,她在矿镇上无拘无束,整天在山上或树林里游荡,所以她所受的教育,与其说是教师传授的,还不如说是大自然赋予的。她是一个我们英国人所说的顽皮姑娘。她性格泼辣、粗野,而又任性,放荡不羁,不受任何习俗的约束。她很性急,我几乎想说是暴躁。她轻易地作出决定,干起来天不怕、地不怕。另一方面,要不是我考虑她到底是一位高贵的女人,〃他庄重地咳嗽了一声,“我是决不会让她享受我所享有的高贵称号的。我相信,她是能够做出英勇的自我牺牲,任何不名誉的事情都是她所深恶痛绝的。”
“你有她的照片吗?”
“我随身带着。〃他打开表链上的小金盒,让我们看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的整个面容。那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象牙袖珍像。艺术家充分发挥了那光亮的黑发、又大又黑的眼睛和优美的小嘴的感染力。福尔摩斯长时间认真地端详那画像,然后阖上小盒,把它递还圣西蒙勋爵。
“那么,是这位年轻的小姐来到伦敦后,你们重叙旧情?”
“是的,她父亲偕同她来参加这一次伦敦岁末的社交活动。我和她数度聚晤,并且缔结了婚约,现在又和她结了婚。”
“我听说她带来了一份相当可观的嫁妆?”
“嫁妆是相当丰富的,和我们家族通常的情况差不多。”
“既然婚礼事实上已经举行过了,这份嫁妆当然归你了?”
“我确实没有去过问这件事。”
“没有去过问是自然的。婚礼的前一天你见过多兰小姐吗?”
“见过。”
“她心情愉快吧?”
“她心情再愉快也没有了,她一直谈着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应当做些什么。”
“真的!非常有趣。那么在结婚那天早上呢?”
“她喜气洋洋,高兴极了,至少直到婚礼结束始终是这样。”
“那么这以后你注意到她有什么变化吗?”
“啊,老实说,这时候我看到了我从前没有看见过的第一个迹象。她的脾气有些急躁。不过那是件小事,不值一提,并且不可能与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
“尽管这样,还是请你讲讲。”
“唉,简直是孩子气。那是当我们去向教堂的法衣室的时候,她手里的花束掉落了。当时她正走过前排座位,花束就掉在座位前面。稍微过了一会儿,座位上的先生把花束拾起来递给她。看来这束花依然完好如初。可是当我和她谈起这件事时,她回答我的话很生硬。回家途中在马车里,她似乎为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心烦意乱,实在令人可笑。”
“真的!你是说在前排座位里坐着一位先生,那么当时在座的也有一般群众了?”
“哦,是的,教堂开门的时候,是不可能不让他们进去的。”
“这位先生不会是你妻子的一位朋友吗?”
“不会,不会,我称呼他作先生是出于礼貌,他只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很平常的人。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容貌。但是,我想,真的,我们谈得离题太远了。”
“圣西蒙夫人婚礼结束回来时远没有她去时那么心情愉快。那么,当她重新回到她爸爸寓所的时候,她做了什么事?”
“我看到她和她的女佣人在说话。”
“她的女佣人是什么人?”
“她名叫艾丽丝,是个美国人,从加利福尼亚和她一起来的。”
“一名心腹佣人?”
“这么说也许有点过份。在我看来似乎她的女主人对她非常随便,不拘礼仪。可是,当然在美国他们对这一类事情有不同看法。”
“她和这位艾丽丝谈了多久?”
“哦,几分钟。当时我正在考虑一些别的事。”
“你没有听到她们说些什么?”
“圣西蒙夫人谈到些';强占别人土地';的话,她总是惯于说这一类的俚语。我不理解她指的是什么。”
“美国的俚语有时是很形象化的。你的妻子和女佣人谈过话后做了些什么事?”
“她走进吃早餐的房间。”
“你挽着她走进去的吗?”
“不,她一个人。象这一类小节,她是一向不讲究的。接着,在我们就座大约十分钟以后,她急急忙忙地站起身来,咕哝了几句道歉的话,就离开了房间。她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据我了解,那位女佣人艾丽丝作证说,女主人走进自己的房间,用一件长外套罩在新娘的礼服上,戴上一顶软帽,就出去了。”
“正是这样。过后,有人看到她和弗洛拉·米勒一道走进海德公园。弗洛拉·米勒就是现在被拘留的那个女人。那天早上,她曾经在多兰的寓所里惹起一场风波。”
“啊,是的。关于这位年轻的妇女,我想知道她的一点具体情况,还有你和她的关系。”
圣西蒙勋爵耸了耸肩,眉毛一扬,“我们已有多年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