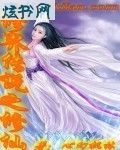沈从文正传-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器是否又换了什么式样,照例为沈岳焕所关心。他还常常停下来,看铺子里的人在冥器上贴金、敷粉,一站许久。
沈岳焕再往前走。
过了衙门是一个面馆。面馆这地方,我以为就比学塾妙多了!早上面馆多半是正在擀面,一个头包青帕满脸满身全是面粉的大师傅正骑在一条木杠上压碾着面皮,回头又用又大又宽的刀子齐手风快地切剥,回头便成了我们过午的面条,怪!面馆过去是宝华银楼,遇到正在烧嵌时,铺台上,一盏用一百根灯草并着的灯顶有趣的很威风的燃着,同时还可以见到一个矮肥银匠,用一个小小管子含在嘴上像吹哨那样,用气逼那火焰,又总吹不熄,火的焰便转弯射在一块柴上,这是顶奇怪的融银子的方法。还有刻字的,在木头上刻,刻反字全不要写。大手指上套一个小皮圈子,就用那皮圈子按着刀背乱划。谁明白他是从哪学来这怪玩艺儿呢。①沈岳焕就这样一路看过去,他总是看不厌倦。他喜欢这些人和物,它们的颜色、声音、形状、气味能让他眼热心跳。
百物制作的全过程,比学塾里背书识字,更来得上心。然而,这并不能使他满足。有时,他又绕道向西城窜去。
西城设有关押囚犯的监狱。大清早便可见一群犯人戴着脚镣,成一线从牢中走出,由士兵押着去做衙门派定的苦役。牢狱附近是杀场。如前一天刚刚杀人,一时无人收尸,尸体便常常被野狗撕碎。沈岳焕赶过去,或用一块石头,敲击那颗污秽的人头;或拿一根木棍去戳尸体,看会不会蠕动。他太好奇,却还想不到去追究背后隐伏的悲剧。有时,还不等他靠拢,便有一群野狗因分赃不匀,正在尸体边互相龇牙咧嘴地争斗,喉管里不时发出沉闷而凶狠的吼声。这时,沈岳焕便远远站定,用书篮里预先准备的石头,扬手向野狗掷去。见野狗受惊后猛然分开,因不甘就此罢休又复聚拢的情形,沈岳焕便得到了一种极大乐趣。
杀场临近一条小溪。小溪傍西城墙根朝东南方向流去,过南门、东门,汇入沱江。既然已经到了溪边,沈岳焕总免不了挽起裤管,从溪流中一路口止尚去。流动的溪水轻轻咬着一双小小脚杆,沈岳焕感到十分舒服受用。口止尚水到了南门,便上岸。机会好,河滩上正巧杀牛,他便急忙赶过去,看人如何将牛放倒,如何下刀,下刀时那满腹委屈无从申诉的可怜畜生如何流着两行清泪;牛被开腔后,心、肝、肠、肺的位置又是如何分布。
河滩过去一点,傍南门有一条边衔。街上有织簟子的铺子,又有铁匠铺。看完杀牛,沈岳焕走进边街,便又看篾匠用厚背薄刃的钢刀破篾,两个小孩蹲在地上双手飞快地编织竹簟;看小铁匠拉风箱、扬锤、淬火。积以时日,他便将编织竹簟、打制各种刀具农具的工艺程序,弄得清清楚楚。
学塾位于北门,沈岳焕却出西门,入南门,在完成这门必修课的各道程序以后,才再绕城里大街朝学塾走去。
还有两件使沈岳焕醉心的事,一是出东门站在大桥上看大水。每逢春夏之交,一场暴雨过后,沱江涨了大水。这时,城里城外只听见满河水响,于是,城街里人急匆匆去河边看河里涨水。一时间,桥面上和沿河岸边便站了许多人。平时温柔清澈的河水一反常态,变得暴怒异常。浑黄的激流不时从上游卷起木头、家具、牲畜、屋梁之类,奔涌而下。这时,桥头上必有人用长绳系住腰身,眼睛直直地瞪住河面,一见有值钱可用的物件漂来时,便踊身跃入水中,游到物件旁,用绳子将其缚住,然后借水势飞快地朝下游岸边游去。上岸后再将绳子另一头捆在大树或巨石上,这猎获之物便归其所有了,那情景十分壮观。而在不远的河湾洄水处,又有人在那扳罾,巴掌大的鲤鱼在罾网里蹦跳。扳罾的人从容安静,与捞东西人的紧张激烈,形成鲜明对照,一面是动如脱兔,一面是静若处子。这一静一动,其美丽动人处,非笔墨所能形容。
另一件是捉蟋蟀。五月麦收时节,树木迸发新枝,竹笋破土而出,田垄里新麦香气弥漫。感应着大自然的变化,人身上被激发起的生命力量已呈饱和状态,仿佛要从全身毛孔里绽出。一场微雨过后,满山遍野都响起蟋蟀鸣奏的曲子。那声音在沈岳焕听来,简直是天籁!他在学塾里更是坐不安宁,总是想方设法逃学,到山野田间去捉蟋蟀。春天,蟋蟀多藏身于草丛、泥缝、割剩的麦兜里,捕捉便极容易。不一会,沈岳焕两手便各有了一只。但他并不离去,又将第三只赶出,一见新赶出的较手中的更为雄壮,羽翅色彩更油亮,旋即将手中的放掉,扑过去将这新的逮住。如此捉了又放,放了又捉,大半天过去后,手里剩下的仍是两只。下午3时许,他便急急赶到城里一个刻花板的老木匠家里,借他专供蟋蟀斗架的瓦盆,比试两只蟋蟀的优劣。老木匠同意借盆,却以斗败的一只归他作代价。随后,他又提议用自己另一只蟋蟀与沈岳焕剩下的一只比试。条件是如果沈岳焕的斗赢,借瓦盆一天;若老木匠的斗赢,蟋蟀全归老木匠。沈岳焕正等着这个建议,便立即答应下来,老木匠进屋拿出一只蟋蟀与沈岳焕的相斗,结果不消说是沈岳焕又输了。沈岳焕有点丧气,他看出老木匠的一只照例是自己前一天输给他的。老木匠见他悻悻的,赶紧收拾起瓦盆,带着鼓励的神气,笑着说:“老弟,明天再来!这不算什么,外面有的是好的,走远一点去捉!明天来,明天来!”于是,沈岳焕仿佛取得了胜利的预期,微笑着走出老木匠家的大门,转回家里去了。
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在这地方要成天向各处跑去,照例必须养成一种强悍的脾性。一只狗会冷不防向你扑来,另一个顽劣孩子,与你当面交臂而过,会突然用手肘向后朝你背上一击,撞你一个“狗抢屎”!这暗施袭击自然算不得角色,即便得手也会输了名头,更多的是公开挑战。如果见你单身一人,对方便用眼睛睃定你,一面大声大气地说:”“肏他妈,谁爱打架就来呀!”
“哪个大角色,我卵也不信,今天试试!”
“小旦脚,小旦脚,听不真么,我是说你呀!”
假若你生性软弱,就只能自认晦气,假装没听见,脚步快快地走去;如果忍不得这口气,便会有一场恶斗!沈岳焕当然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一来,他从一心想当将军的父亲那里,早就继承了一份胆量与勇气;二者,凤凰地接川黔,民气强悍,游侠之风颇盛。军营里有哥老会的老幺,市井里有好打不平的闲汉。因此,即使在大白天,凤凰街上也可见两条汉子,一对一用单刀或扁担互砍。事情发生时,本地小孩不但不躲,反要拢身去看热闹。这时,孩子的父母照例不加理会,只间或说一句:“小杂种,站远点,莫太近!”沈岳焕就亲眼见过后来名震湘西的龙云飞与人决斗,用刀将对方砍翻以后,极从容地走下河去洗手。在这种环境里,除非有先天弱疾,后天残废,莫不从小就把心子磨得硬硬的。沈岳焕当然不会例外。好在这一对一的争斗方式,也影响到孩子身上。打架时,即使对方有一群,也不会以多欺少,可以任你选定一个作对手,其余人不许帮忙。如果被对手摔倒,只怪你运气不好,让他打一顿了事;如果将对手摔倒,对方只说一句:“有种的,下次再来!”便让你扬长而去。每逢这种时节,沈岳焕照例能选出一个与自己差不多的对手,凭着他那份敏捷与机智取胜。或是将对手摔倒,或是先被对手摔倒,而后凭技巧翻过身来压到别人身上去。对沈岳焕来说,这种斗殴也只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打架的次数越多,认识的朋友也越多。到后大家都因逃学打架成了熟人朋友,反倒不再打架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沈岳焕逃学的次数随年龄增加而增长,受处罚的次数也就与逃学次数成正比。既然逃学已成积习,要瞒过家里耳目,便越来越困难。或因熟人告状,或因学塾与家中两方面对证。而且,一天野下来,身上总要带一点形迹,或是上山摘野果时被刺蓬扯破了衣裤,或是捉蟋蟀时浑身沾满泥浆,或是打架时手上脸上挂一点彩,都能成为家里施加处罚的凭证。这处罚,除了挨打,照例是罚跪。下跪时点上一根香,不等香燃尽不准起身。然而,同一种药服用多了就难免失效一样,罚跪一多,沈岳焕身上有了抗药性: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按照天气冷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拨喇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
沈岳焕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想象里。在这种情形下,他已将罚跪的痛苦忘却。20年后,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①
尽管如此,在当时,沈岳焕幼小的心里并不服气。他有他的理由:
我从不用心念书,但我从不在应当背诵时节无法对付。许多书总是临时来读十遍八遍,背诵时却居然琅琅上口,一字不遗。也似乎就由于这份小小聪明,学校把我同一般同学一样待遇,更使我轻视学校。家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进,不好好的利用自己聪明用功,我不了解家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不让我玩。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一点,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稀奇。
最稀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在他那份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汁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这些古怪事情实在太多了。②童年的沈岳焕生活在他自己所能感觉到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充满了他无法解释的自然之谜。要获得谜底,学塾和家里两方面都不会给他什么帮助,他也不敢拿这些去问先生和父母。他常常为此发愁。生命有了扩张自己的冲动。这种扩张既然不愿循着社会和长辈安排的道路,要一味发展自然的天真,便不能不依靠自己踩出一条路来。
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①这简直是一种方法论的胚芽。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的所作所为,他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模式,都可以溯源到他的童年。倘若这一说法并非全无根据,那么,当我们去把握沈岳焕生命成熟后的思想、行为模式时,便不难发现其中晃动着的童年沈岳焕的影子。
沈从文传……革命:晃动着历史的影子
革命:晃动着历史的影子
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仿佛是两个天地。沈岳焕愈是与自然贴近,便愈是和成人世界离远。虽然,每当人们在冬夜里围着火炕取暖,夏季黄昏摇着蒲扇坐在院子虽乘凉的时候,他总要傍着家里或亲戚中的长辈,听他们谈论、讲述亲族或本地有名人物的种种掌故和轶事。其中,浸润着人生创业艰难的感慨和属于本地人的那份荣光。
——咸同之季,“长毛”作乱,本地几个卖马草的年轻人投效湘军,如何九死一生,与“长毛”干仗,随曾国荃攻入南京城的,凤凰人中就出了四个提督军门。……那个被当地人翘着大拇指,因书读得好甲午年考中进士授“庶吉士”的熊希龄,先一年本已考中,因一笔字写得不好,房师要他先将字练好再参加殿试,他硬是呆在家里苦练了一年;戊戌那年,他如何与陈立三、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办时务学堂,鼓吹变法维新。变法失败,他因“庇护奸党”而被革职,后来,皇帝老子怀疑他与唐才常共谋自立军起义,密令将他逮捕,又如何赖人搭救幸免;后来又如何做了东北三省清理财政的监理官。……庚子年间,北方又出了义和拳,专杀洋毛子;他们如何练神兵,有神符护身,刀枪不入;那时候,父亲随军驻守大沽口,亲见洋毛子来攻,枪炮如何厉害,罗提督又如何率领人马抵抗,又如何败走,如何自杀……。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这一切对沈岳焕说来,就像平时从旧戏里看到的一样,或是红花脸杀进,黑花脸杀出,或是奸臣当权,忠臣遇害,义士死节,照例觉得十分遥远。虽然也感到一些兴奋,一些神秘,对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人们谈论时其所以感叹嘘唏,却不曾去理会。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