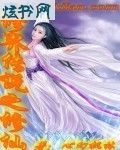沈从文正传-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品“比任何东西还重要”,文章便慢慢转入“游戏”。沈从文问道:“20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个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其次,沈从文还批评了一些刊物为谋求销路,不惜“针对一个目的”,向“异己者”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的现象。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想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相互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①这篇文章贯串了沈从文两个一贯的主张:其一,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一味提倡“性灵”,只能转入“游戏”,与时代要求不符;为幽默而幽默的结果,难免坠入“恶趣”。这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现象而发的;其二,作家应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充斥刊物的相互嘲讽与“私骂”,不仅培养读者的不良习气,而且势必影响文学创作的实际成绩。沈从文的批评对象包括了左翼文学刊物,由于未点明具体所指——这“争斗”是为着何事,在谁与谁之间发生,便难免过于模糊,模糊则易引起误解;或者其实也不会误解,因为对文坛上的论争,沈从文从来都感到不满。因为他希望作家能将精力主要用于作品的创作。他以此律人,也以此自律。
正因为此,沈从文的文章再次引起鲁迅的注意。9月12日,鲁迅写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对沈从文的文章提出批评:
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竟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慢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①
上述三次涉及沈从文和鲁迅的论争,争论的焦点都不在沈从文批评的对象本身该不该批评上。一些“海派”文人借文学以“登龙”,陷友人以邀功,造谣言以攻讦的恶行;国民党推行的禁书政策;文坛论争中往往出现的意气用事、相互间的辱骂与恐吓;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提倡等等,鲁迅同样提出过激烈批评。他的《登龙术拾遗》、《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小品文的危机》、《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等著名杂文就是明证。鲁迅和沈从文之间的分歧,显明地反映出左翼作家与民主主义作家在上述问题上,既有相互一致的方面,又有出发点与对问题的具体理解不同的一面。这种分歧与他们同国民党右翼文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30年代极其复杂的文坛局面。随后发生的关于“差不多”的论争,是这种京沪之争更为典型的事件。1936年10月,沈从文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指陈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近几年来,如果什么人还有勇气和耐心,肯把大多数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流行杂志翻翻看,就必然会得到一个特别印象,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这种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们都太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①文章很快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1937年初,《书人月刊》、《月报》转载了沈从文的文章,《大公报·文艺》也于2月21日组织“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沈从文在上面发表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观点,并进而阐明自己所持的文艺自由主义立场。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①
1937年春夏,“差不多”问题的讨论在北方达到高潮。参加讨论的作家几乎普遍承认文学创作中“差不多”现象的存在,认为沈从文说的是“老实话”,切中当前文学创作不能深入的时弊,形成差不多一致的看法。在南方,却引起不尽相同的反响。1937年7月,茅盾连续发表《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关于“差不多”》,对沈从文的观点提出批评。文章认为从新文学20年发展历史的“全体而观”,“矛盾中有发展,时至今日,不曾走过回头路”。而沈从文“单就现有的作品发议论”,“是把范围缩小了”。虽然,“所谓‘差不多’未尝不是现文坛现象之一”,但沈从文“无视了‘视野扩大’这一进步重点而只抓住了‘差不多’来作敌意的挑战”,②“且抹煞了新文艺发展之过程,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艺发展一步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幼稚病,作为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的弥天大罪,这种立言的态度根本要不得”!③大概在炯之先生看来,作家们之所以群起而写农村工厂等等,是由于趋时,由于投机,或者竟由于什么政党的文艺政策的发动;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想,则他的短视犹可恕,而他的厚诬了作家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则不可恕。①为了进一步澄清在文学与思想、与时代关系问题上产生的误解,1937年8月,沈从文又发表了《再谈差不多》一文。
近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品,似乎由于风气的控制,常在一个公式中进行,容易差不多。文章差不多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要从一堆内容外形都差不多的作品达到成功,恐怕达不到。
他以对鲁迅的评价为例说:最好的回答倒是鲁迅先生的死,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伟大何在?都说他性格、思想、文章比一切作家都深刻。——倘若话是可靠的,那鲁迅先生是个从各方面表现度越流俗最切实的一位。倘若话是不可靠的,那一切纪念文章都说错了,把鲁迅先生的伟大估错了。②
显然,沈从文并非反对文学表现“思想”、“时代”,而是要求作家有真思想,对人生有深入独到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满足于从某种现成观念出发进行创作。否则,就难免公式化倾向的出现。
这次讨论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差不多’这三个字在文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流行的名词”。①到1938年,余波犹存。其后,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便被新的文学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所代替。
沈从文传……“生命”的第一乐章
“生命”的第一乐章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②从故乡返回北平后,每天一早,沈从文就在达子营28号寓所院子里的老榆树下,摆一张八腿红木小方桌,放下一叠白纸,继续写返乡前即已起首的《边城》。残冬的阳光透过榆树的枝叶,细碎地撒在桌面上,空气疏朗而澄澈。沈从文的心也如一泓秋水,少渣滓,无凝滞。虚静中,隐隐约约起了哀伤而悠远的乐音。
检视离京前笔下所得,已完成故事背景和主要人物的构置。那是20世纪的初叶,这苗蛮杂处的边城,尚未卷入近代中国社会的变乱,到处是一片宁静与和平。它是湘西的昨天,也是整个中国更为遥远的过去的象征。在这乡村凡夫俗子的人生里,还厚积着属于那片土地的古老风俗——一个根源古老民族原始而纯朴的人性凝结。同这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因陈新代谢,老一辈正临近人生的终点——碧溪嘴白塔下摆渡的老船夫已年过70,而生命的新枝正在萌发。如新竹豁裂了外箨,老船夫抚养的女儿的遗孤翠翠,转眼间有了15岁。城里管码头的顺顺,儿子天保和傩送也已长成。这地方的阳光与空气,决定了新的一代与他们祖辈根连枝接。属于这地方男子的勇敢、豪爽、诚实、热情,在天保和傩送身上皆不缺少,他们是“自然”的儿子。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这里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当年翠翠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同一个清绿营屯防士兵“唱歌相熟”,肚子里有了孩子,却“结婚不成”。——黄罗寨那片林子里,立着那可怜的嫡亲祖母,一个苗族妇女的假坟,一'g黄土埋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剧故事。——屯防士兵顾及军人名誉,首先服了毒,老船夫女儿待孩子生下后,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也死去了。老船夫无从理解这悲剧的前因后果。
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
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不尤人,心中不能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到底还像年轻人,说是放下了,也还是不能放下的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件事情。摊派到本身的一份说来实在太不公平!
翠翠已经长大了。这一代人面临的,又将是怎样一种命运?——沪溪城绒线铺里的“小翠”、杨家嘴那个爱好、怀着某种期待的夭夭、沅水流域吊脚楼上的牛保和妓女……,正各自接受着摊派到他们头上的一份命运。
正因为翠翠长大了,证明自己已真正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把他的,翠翠长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他的事才算完结!
然而,人的良好愿望却不免与事实冲突。边城已不是“改土归流”前的边城,那时,这里的婚嫁,还保留着充分的自由形式。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而是从心里流出的热情的歌。而眼下,固有的风俗虽没有完全消失,一种新的变异已经楔入(这种变异在都市现代“文明”的畸形发展里,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人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常”与“变”在这片土地上,交织成一种复杂的人生形态。老船夫不曾料到,早在两年前的端午节,翠翠与傩送二老在河边第一次相遇,傩送已爱上翠翠,翠翠下意识里已朦胧生出对傩送的爱恋。不巧的是傩送的哥哥天保大老也爱上了翠翠。更严重的,是一座新碾坊又加入了这场竞争——团总将它作女儿的陪嫁,正托人向顺顺放口风,要傩送作女婿!…………
另有一个女人便插嘴说:“事弄成了,好得很呢。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些。”
有人问:“二老怎么样,可乐意?”
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