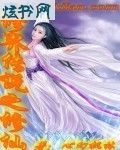沈从文正传-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从文,却与他们想象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眉目清秀如女子,面容苍白而少血色;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稍许冲淡了几分身心的憔悴。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感到仿佛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
起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五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到这时,满教室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张兆和,时年十八,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中公认为中国公学的校花,因肤色微黑,沈从文后来称之为“黑凤”。这时,她见沈从文行状狼狈,一颗心也憋得极紧,怦怦直跳,血潮直朝脸上涌去,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这些心地善良而富同情心的年轻女性啊!
这十分钟的经历,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但他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越。他慢慢平静下来,原先飞散的话语又开始在脑子里聚扰组合。……他好容易开了口。这第一句出去,就像冲破了强敌的重围,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然而,他又一次事与愿违。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不知具体起于何时,选修沈从文所授课程的那只“黑凤”的身影,飞进了沈从文大脑的屏幕,而且愈来愈鲜明,愈来愈深入,再也无从抹去。张兆和的美貌和沉静,强烈地摇动着他的心旋,使他目眩神迷。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的心窝,生发起爱情的潮汐。这时,沈从文已经26岁,早已过了一般人婚娶的年龄。可是,自从离开湘西,混入都市人群以来,他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莫过于吃饭问题,性爱的欲求不能不被求生存的挣扎压抑着。加上在他的人生路上,也未能碰上恰当的机遇,天下女子虽多,似乎全都与他绝缘。尽管同大多数青年一样,沈从文免不了被青春期的苦闷折磨,一切却无从谈起,对性爱的欲望,只能在虚幻的想象中生成,旋又在想象中破灭。
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眼下,如何活下去已经不再构成最紧迫的威胁,爱的对象又是那么现实,她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具体。爱的潮汐来得又是那样猛烈,他常常被弄得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饭后课余,他在校园里散步,常常情不自禁地朝张兆和住的学生宿舍跑去。他渴望着再见到她,并当面向她倾诉点什么。可是,他在人前却是个不尚健谈、口齿朴讷的人,每当他来到张兆和面前,总是愣愣地站在房间中间,不知说什么好。他本想向张兆和倾吐自己的爱恋之情,即便是一点模糊的暗示也好。可是及至说出来时,却成了问她的功课,读什么书,以及家里的情况。到后见她喜欢什么话题,就谈什么。看他站着说话,张兆和请他坐下,他却不坐也不走。见他这副呆相,张兆和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又从他的神色中,隐隐约约感到几分蹊跷,反倒有点不安起来。
笔谈远胜于言谈的沈从文,终于用他那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来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据说那第一封情书,“仅只一页,寥寥数语而分量极重”。①虽然,它连同随后而来的一大堆情书,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后,早已荡然无存,可是在《新废邮存底》中仅有的一封,从中依稀可见这些情书的大致轮廓。
我还要说,你那个奴隶,为了他自己,为了别人起见,也努力想脱离羁绊过。当然这事作不到,因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你感到窘迫,使你觉得负疚,我以为很不好。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作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却愿意自己作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你不觉得这也是生存里一件有趣的事吗?
……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们头上的,还是那个月亮。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至于你,“人事”的云翳,却阻拦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见,我不能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我现在,并且也没有什么痛苦了,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故只想怎么样好好的来生活。假如当真时间一晃就是十年,你那时或者还是眼前一样,或者已做了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或者自己不再是小孩子,倒已成了许多小孩子的母亲,我们见到时,那真是有意思的事。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许多诗是专为这点热情的指使而写出的,许多动人的诗,所写的就是这些事,我们能欣赏到那东西,为那些东西而感动,却照例轻视到自己,以及别人因受自己所影响而发生的传奇的行为,这个事好像不大公平。因为这理由,天将不允许你长是小孩子。“自然”使苹果由青而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上,转变成一个“大人”。××,到你觉得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愿作大人时,我倒极希望知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感想。“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①这封信写于1931年,距第一封情收已经两年有余了。而在最初,张兆和收到沈从文的情书时,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还稍稍起了一点反感;一个老师,给学生写这种东西,真稀罕!可是,一个少女的羞怯心理,却使她害怕这事张扬出去,弄得满校园飞短流长。她只得听任沈从文一封接一封给她写那没完没了的情书,却一概置之不理。
张兆和的不予理睬,真差点要了沈从文的命。他当然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结果非但不能得到她的只言片语,连再去看她也不能够。他爱她到了快要发狂的程度,一想起她,全身的血就奔窜得快了许多,浑身发热作寒,十分痛苦,仿佛人生的一切都与他作对,爱情、幸福都与他无缘。他真想从自己所住的楼上一跃而下,在死亡里求得人生烦恼的解脱。
沈从文的烦躁不安,不知怎样一来,很快在校园里沸沸扬扬传播开去,说是沈从文爱上了张兆和,张兆和却不予理睬,沈从文急得要自杀。张兆和的一位女友,听到这消息后,赶紧找到张兆和,对她说:“你赶紧给校长讲清楚。不然,沈从文自杀了,要你负责。”张兆和也紧张起来,她带着沈从文给她的一摞情书,急忙找到校长胡适,怯怯地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
她希望得到胡适的支持,出面阻止这事的进一步发展。
可是,结果与她预期的相反。在听过她的陈述后,胡适却微笑着,带着这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神气,对她说:“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
听了胡适的话,张兆和脸上不免有些尴尬。与胡适谈了一会儿其它事情后,就告辞走了。
自此以后,她既无从拒绝沈从文的来信,心里又没有作出回应的欲望。只好抱定你写你的,与我无干的态度,听任这事的自然发展。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冷淡反应,并不涉及她对沈从文值不值得她爱的估价——这个问题还压根儿没有被她放在心里掂量过。这既与她当时的年龄还小有关,也与她所受的家庭教养相联系。
张兆和出身名门贵族,原籍安徽合肥。张家为本地声势赫奕的大族,拥有良田万亩,在肥西筑成围子,人称“张家老围”。曾祖父张树声,为同治年间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中著名将领,曾领兵转辗江苏浙江一带,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1879年至1884年间,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于淮军中称儒将。祖父也曾作过管司法的四川臬台。父亲张武龄,字绳进,是过继给祖父的,祖父死后,承继了一份厚实的家产。由于受近现代新思潮的影响,嫌自己名字太封建,自改名为冀牖,又叫吉友。最初,想投资办实业,因不知如何经营,遂迁居苏州,独资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太多,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凡贫寒人家和工人女儿,一律不收学费。聘用教师也不拘一格,教师中很有几个著名共产党人,张闻天、侯绍裘、匡亚明等,都先后在乐益女中任过教。张兆和有兄妹十人,在她十岁那年死了母亲。张武龄不准自己女儿穿戴耳环,在张氏家族中,张兆和与二姐允和、妹妹充和也是最先进新式学校读书的女孩子。在乐益女中读书时,张兆和兄妹就喜欢新文学,家里订有《小说月报》、《新月》等刊物,还自办了一个刊物,取名为《水》。可是,由于母亲去世较早,张兆和从小又是保姆带大的,一份旧的家庭教育反由家里的保姆实行,逐渐培养起张兆和一份大家闺秀气质,雅静、平和、沉稳。长大后也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向新思潮认同,却终不能成为大胆、泼辣、热烈、敢于向一切传统挑战的“新女性”。
因此,写情书一事,反倒在她与沈从文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使她时时像山羊躲虎似的避开沈从文。当时,新月书店的会计肖克木,身材长像酷肖沈从文。一次。张兆和去买书,一走进新月书店大门,猛然间见到肖克木,以为沈从文在店里,吓得她掉头就跑。
然而,在她眼里,沈从文的情书写得实在是好!一方面,她害怕这骤然而来的求爱,另一方面,一份秘密的好奇,又使她无法推开这些充满情感的文字的诱惑。她从头到尾读完每一封情书,随后轻轻吁一口气,将这些信藏进一口小箱子里去了。可是,信中那些充满爱慕、混合着忧郁的言语,层积在她的心里。时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