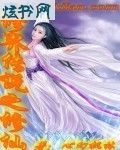沈从文正传-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荡漾,既悠扬,又绵长。听到这声音,沈岳焕小小心里仿佛浸入了一丝凄凉。
望着那些碾槽内正被碾碎的桐籽,沈岳焕常常想起幼时去黄罗寨乡下时见过的堆积如山的桐子。冬日的晴天,白霜渐渐化去,静寂的山野显得极为空疏、清朗。早饭过后,一群村妇围坐在桐子堆边,用小小钩刀剥取桐籽。剥出的桐籽摊晒在坪坝上。各家的孩子一会儿在桐籽上翻跟斗、摔跤,一会儿围在大人身边听他们摆“龙门阵”:张家老大上山砍柴,早饭少吃了点,到时又碰上落雨,又冷又饿,待他走进一个没人去过的岩洞里躲雨,猝然看见洞里有一张石桌,桌上摆着一笼白蒙蒙的泡粑,还冒着热气。旁边地上有一路脚印,每个有一尺多长;乾州有个跛子,姓李,过八面山时,碰到一个人熊。脚不方便,逃不脱,两只手被人熊死死抓住。人熊对着他迷迷地笑,笑了好久。笑够了,张嘴就咬。亏得跛子脚不方便人聪明,先就有了算计,手拐子上套了两个竹筒,人熊抓着的是竹筒不是人手。等人熊笑迷了的时候,跛子将两手轻轻抽出,白捡了一条命;城里副爷家一个女子,人生得好秀气!没想到讲婆家高低不就,年纪都二十好几了。那天到乡下走亲戚,从天坑①边过,没成想被洞神看起了。那个洞神是白蟒成精,白衣白帽,长得好标致!副爷女子也被他迷住了,转回屋里就不吃不喝,气色反越来越好,天天喊着洞神就要来接亲了。接亲那天,副爷女子满脸红光,笑成一朵花,嘴里尽讲新姑爷骑高头白马,八抬大矫,好不威风!只可惜凡人看不到……。
讲完这些,妇人们照例要拿那些三五岁的男孩子取乐:“老三,老三,快过来,伯娘问你,要不要讨个新姑娘?”“要。”
“要那个?”
这孩子准会指定一个平时给他印象最深的姑娘:“要四姐。”
“你要四姐作什么?”
“引我睡觉。”
看到那个被称作四姐的大姑娘羞得脸红红的,品味着那孩子答话的底蕴。姑嫂姐妹便前俯后仰笑得直不起腰来。这些挂在山里人嘴边的故事,原是他们泛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它们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来,却每次都说得有眉有眼,有名有姓,不由小孩子不信。那里面透着的神秘与新鲜,对沈岳焕具有无穷的魅力。就在这种既荒诞又现实的传闻里,孕育着沈岳焕所属南中国人的浪漫幻想情绪。
当沈岳焕终于从眼前各种光色和想象的迷醉里走出来时,几个人都感到肚子有点饿了。——乡下人赶场,最惬意的莫过于在摊子上吃狗肉。花点钱,买一碗“包谷烧”,要一碗狗肉,一面喝酒,一面用筷子挟狗肉蘸辣椒盐水往嘴里送。若遇上熟人,便两人对饮,吃得“哦荷”朝天,那滋味真够以后半个月的咀嚼。——这时节,若身上带有零钱,几个人虽不喝酒,照例要买一碗狗肉吃。假如凑巧谁也没带钱,几个人便在墟场各处转悠,看是不是碰得上亲戚熟人。运气好,碰上一位亲长,那亲长必要问:“过午了没有?”大家正巴不得有这一问,却又不好意思开口求援,便相互望着羞怯地一笑。那亲长心里有数,也就笑笑地说:“这不成,不喝一杯还算赶场吗?”于是,几个人便被这亲长拖到狗肉摊上,切一斤两斤狗肉饱肚。
吃过狗肉,各人身上立时长了许多精神,就又走到河边上,看河中来往的船只和竹筏、木筏。长宁哨位于苗区与苗汉杂居区的交界处,从这里沿河上行,到名叫鸟巢河的地方,便是纯苗区了。因此,长宁哨成了苗民与外部进行物资交易的集散地。河面上的小船和竹筏,有一部分是属于苗民的。苗民的船只造型特别雅致,篙桨十分精美,一眼就能分辨清楚。这河面。给沈岳焕开启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从中,可以窥见到一个根源古老的民族身影。
请你想,一个用山上长藤扎缚成就的浮在水面上走动的筏,上面坐的又全是一种苗人,这类人的女的头上帕子多比斗还大,戴三副有饭碗口大的耳环,穿的衣服是一种野蚕茧织成的峒锦,裙子上面多安钉银泡(如普通战士盔甲),大的脚,踢拖着花鞋,或竟穿用稻草制成的草履。男的苗兵苗勇用青色长竹篙撑动这筏时,这些公主郡主就锐声唱歌。君,这是一幅怎样动人的画啊!人的年龄不同,观念亦随之而异,是的确,但这种又妩媚,又野蛮,别有风光的情形,我相信,直到我老了,遇着也能仍然具着童年的兴奋!望到这筏的走动,那简直是一种梦中的神迹!
我们还可以到那筏上去坐,一个苗酋长,对待少年体面一点的汉人,他有五十倍私塾先生的和气。他的威风同他的尊严,不像一般人来用到小孩子头上。只要活泼点,他会请你用他的自用烟管(不消说我们却用不着这个),还请你吃他田地里公主自种的大生红薯,和甘蔗,和梨,完全把你当客一般看待,顺你心所欲!若有小酋长,就可以同到这小酋长认同年老庚。我疑心,必是所有教书先生的和气殷勤全为这类人取去,所以塾中先生就如此特别可怕了。①那时,沈家每年还有300石左右的田租收入。三个叔父两个姑母占有其中的两份,沈岳焕家占取一份。因此,沈岳焕便有机会跟长辈们到20里外的乡下去,督促佃户和临时雇佣的短工收谷。乡下有城里所没有的新鲜物事,沈岳焕也有了不同于城里的玩法。——去田里辨别各种禾苗、害虫;用鸡笼到水田里罩取鲫鱼、鲤鱼;向佃户讨斗鸡;剥桐树皮卷制哨子……。最有趣的是打猎。春天,到山中野雉交配繁殖季节,将驯养的雉媒带到山林间放出,勾引林间野雉。待野雉飞近,举起鸟枪便打。等候时那份期待,野雉飞近时那份急切,枪中鹄的时那份喜悦,永远不会使沈岳焕感到倦怠。秋末冬初,人们上山围猎黄麂、野猪、狐狸时,沈岳焕也跟着满山乱跑。有一次,佃户们将沈岳焕用绳子捆在一棵大树的高枝上,让他看被追赶的黄麂如何惊恐万状地从树下跑过。他还看见过一对狐狸被追得在一株大树根下乱转,后来这对狐狸的皮毛便成了叔父身上的马褂。这次猎狐所见种种,后来在他的小说里有过极精彩的描述:在这雪晴清绝山中,忽然腾起一片清新的号角声,一阵犬吠声。我明白,静寂的景物虽可从彩绘中见出生命,至于生命本身的动,那份象征生命律动与欢欣在寒气中发抖的角声,那派表示生命兴奋而狂热的犬吠声,以及在这个声音交错重叠综合中,带着醉心的惊恐,绝望的低嗥,紧迫的喘息,从微融残雪潮湿丛莽间奔突的狐狸和獾兔,对于忧患来临挣扎求生所抱的生命意识,可绝不是画家所能从事的工作!…………身后一株山桂树旁咝的一响,一团黄毛像一支箭射入树根窟窿里去了。大家猛不防吓了一惊,掉过头来齐声叫,“狐狸,狐狸!堵住,堵住!”
不到一会儿,几只细腰尖耳狗都赶来了。有三只鼻贴地面向树根直扑,摇着尾巴向窟窿狂吠。……于是那支箭就在这刹那间,忽然又从树根射出,穿过我的脚前,直向积雪山涧窜去。几只狗随后追逐,共同将溪涧中积雪蹴起成一阵白雾。去不多久,一只狗逮住了那黄毛团时,其余几只狗跟踪扑上前去,狐狸和狗和雪便滚成一团。在激情中充满欢欣的愿望,正如同吕马童等当年在垓下争夺项羽死尸一样情形。三个猎人和我那四个同伴,看见这种情形,也欢呼着一齐跳下山涧,向狐狗一方连跌带滚跑去。……………………………………………这中间,已经加入了后来才有的、沈岳焕自己的生命意识和审美观照,然而,谁能说其中没有沉积着人之初对生命的感悟?他读这一本大书所见到的一切,尽管在当时只能是对事物的直观感印,却也聚集着他后来思索人生、表现人生的实感经验。
这种不安于课堂,倾心于自然与人事的光色,几乎每个生长在这边陬之乡的学童,都能摊上一份。不肯好好念书,成天在外面野,虽使家长伤透脑筋,却也是意料中事。最使家里难堪的,是沈岳焕竟学会了掷骰子赌钱和说各种下流野话。掷骰子赌钱似乎与小时赌劈甘蔗培养的兴趣有关。沈家附近道台衙门前的大坪坝上,白天是菜市,晚上总摆有各种各样小吃摊子。一到天黑,每个摊子上便一齐亮起萤火似的灯光。那时,一吃过夜饭,沈岳焕便与同街的伙伴,在晕黄光波的漾动中,围着摊子赌劈甘蔗。——将一根甘蔗的一头削尖,竖立在地上,参加的人抽签排定顺序,轮流用小镰刀去劈。由于人小,第一个总要站在一张小凳上,方能与甘蔗等高。谁手法好,刀身能穿过蔗身,就可不花钱吃最好的一节甘蔗,由输家出钱。现在,赌劈甘蔗的年龄已经过去,赌输赢的兴趣已转移到掷骰子赌钱。将骰子抓在手中,奋力向大土碗里掷去,口里跟着喊出“快”、“臭”种种专用术语,沈岳焕便忘了周围一切,进入一种忘我境界。如果家中一早派他上街买菜,他就同一群小无赖跑到米厂天棚内玩骰子。如果手气好,赢了钱,便拿来立即买东西吃;若运气不佳,将买菜的钱输去,就悄悄从后门溜回家中,径直去找外婆,从她那里将输掉的钱补足。这办法极冒险,因此,他常常只拿出一个铜子下注,赢了便走,输了也不再来。这样,输赢数目少,家里很难觉察,敷衍过去也还容易。
由于赌术精明我不大担心输赢。我倒希望玩个半天结果无输无赢。我所担心的只是正玩得十分高兴,忽然后领一下子为一只强硬有力的手攫定,一个哑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
“这一下捉到你了,这一下捉到你了!”
先是一惊,想挣扎可不成。既然捉定了,不必回头,我就明白我被谁捉住,且不必猜想,我就知道我回家去应受些什么款待。于是提了菜篮让这个仿佛生来给我作对的人把我揪回去。这样过街可真无脸面,因此不是请求他放和平点抓着我一只手,总是趁他不注意的情形下,忽然挣脱先行跑回家去,准备他回来时受罚。
每次在这件事我受的处罚似乎略略过分了些,总是把一条绣花的白绸腰带缚定两手,系在空谷仓里,用鞭子打几十下,上半天不许吃饭,或是整天不许吃饭。亲戚中看到觉得十分可怜,多以为哥哥不应当这样虐待弟弟,但这样不顾脸面去同一些乞丐赌博,给了家中多少气怄,我是不理解的。
我从那方面学了不少下流野话,和赌博术语,在亲戚中身份似乎也就低了些。只是当十五年后,我能够用我各方面的经验写点故事时,这些粗话野话,却给了我许多帮助,增加了故事中人物的色彩和生命。①
沈从文传……从“将军”向士卒的跌落
从“将军”向士卒的跌落
“我那时太野,简直无法收拾。一到晚上,尽作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常常梦见自己生了翅膀,身不由己向空中飞腾,虚飘飘的,也不知飞了多久,突然看见满天金光,那金光异常强烈,又闪烁不定,照得我头晕目眩,全身燥热,急得我大叫一声,就醒转来了。……好多年后,它还使我半夜里无法安睡。这大概是因为小时摔跤,脑子受了伤的缘故。”1984年夏,当年的沈岳焕在北京崇文门大街的高层寓所内,和我谈起60余年前他的顽童生涯时,就是这样开头的。“什么时候摔的跤?”我问。
“摔了多次,爬树摔过,翻杠子也摔过。最重的还是在预备兵技术班的那一次。我攀上杠子,两臂向后反挂,准备作一次背车。不知怎么不小心,旋转时从杠子上猛地掼到砂地上,喉咙一下子跌哑了,想说话,却无论如何用力,也不出声。幸亏班长梁凤生赶紧将我扶起,架着我在操场上乱跑。跑了好一阵,才慢慢说得出话来。”
“关于预备兵技术班的起因,您在自传里说过。那是民国5年,地方上受上年12月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战事的刺激,感到军队非改革不能自存,凤凰镇守署便设立了四个军事学校:一个军官团,一个将弁学校,一个学兵营,一个教导队。如此说来,湘西地方军队也参加‘护国运动’了?”“当然参加了。当时田应诏任湘西镇守使,此人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和蔡锷同期,参加过辛亥革命,攻占雨花台,首先随大军进南京的军官里就有他。蔡锷的参谋长朱湘溪说他大少爷脾气,不中用,才转回湘西。‘护法’、‘靖国’等大规模战役,湘西方面都派兵参加过,曾兵出常德、桃源,进抵长沙。只是作首脑的割地自保情绪太重,战事一过,就又退守湘西。”
“凤凰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