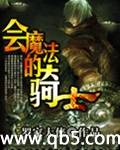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0)朱维纳尔在《生物看重荣誉》一书中说过:“宁要生命不要名誉”。——德文版原注
(21)德文版无此标题。——译者
(22)德文无后边“移居…;放逐”的标题。——译者
(23)指古罗马的海外省,其实是藩属国或被征服国。——译者
(24)德文出版者注“较低的家族”指“一个臣仆的占有物”。“母国”一词即现在说的宗主国。——译者
(25)德文版在此之后尚有“这就叫做驱逐出境”这句活。——译者
(26)在德文版中,这里还有一句话:“用德语中各民族的权利或国际法来称呼它,并不完全正确,应该用国家权利或国家法才正确”。——译者
(27)德文版中特别注明,这不是联盟而是结合。——译者
(28)康德所说的法律状态,当然是指法治社会。——译者
(29)毕声:全名为安东·弗里德利希·毕声(1724—1793),德国地理学家。——译者
附 录
关于法(学)(1)的形而上学原理的若干说明(2)
我所以要作些补充说明,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1797年2月18日《哥廷根杂志》第28卷对拙作进行了评论。评论广见卓识、审鉴严厉,同时也关怀并希冀《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能对科学有深远的裨益。我想以此评论作为评论拙作的入门,此外,也想把此说明作为这个体系的若干补充。
在本书序论的一开始,我的非常敏锐的评论家就遇到了一个定义——什么是渴望的能力?文章说,它是一种能力,通过它的想象构成这些想象对象的依据——这种解释可以用如下的理由来反驳:“一旦人们把渴望结果的外在条件抽象化,它将成为子虚乌有——但是,对唯心主义者来说,渴望的能力确实是某种实在的东西,虽然对唯心主义者来说,外部世界纯系子虚乌有。”回答是:难道有一种热烈的、然而同时又有意识使之成为徒然的渴望吗?(比如说:上帝啊,让那个人还活着吧!)这种渴望虽然在行动上是空洞无物的,然而在后果上并非空洞无物,虽然不能对外在物,但却能对主体(人)的内在本身产生强烈的效果(如使之生病)。一种渴望作为一种追求,通过想象构成依据,尽管主体看到,后者不足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这种渴望总是因果关系,至少在这个主体的内在方面是如此。——这里产生的误解是:(在上述情况下)由于意识到他的一般的能力,同时也是意识到他对外界的无能为力,因此这个定义不能运用在唯心主义者身上。因此,面对着对象物,在渴望能力的概念中,必然要想到想象的因果关系,因为这里谈的仅仅是(想象的)依据对一般效果(感觉)的关系(依据可能是外在的,也可能是内在的)。
1。对再次大胆提出权利概念的逻辑准备
如果熟谙权利科学的哲学家把自己上升到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高度,或者他们竟敢于这样坚持(没有这些原理,他们的整个法理学都将仅仅是一堆法律条文而已),那么,他们不能对保证权利概念分类的完整性漠然置之,否则,这个科学将不是理性的体系,而仅仅是拾捡而来的材料的堆砌。——就体系的形式而言,原理的细目必须完整,也就是说,必须指出一个概念所占的位置,按照分类的综合形式,这个位置对于这个概念来说应该是开放性的。人们以后也可以这样表述,即把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放在这个位置上,本身是矛盾的,是站不住脚的。
迄今为止,法学家占了两个共同的位置:物权的位置和对人权的位置。人们当然会问:既然还有两个作为先验分类的环节的位置是开放性的,单纯在形式上把两者结合成为一个概念,即建立在人的方式上的物权,正如建立在物的方式上的对人权一样,那么是否允许增加一个新概念?这样做虽然有问题,但是,是否必然会在一个完整的分类图表中碰到这样的概念,后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因为逻辑的分类(它从认识的内容——客体——抽象出来)总是二分法,例如,每一种权利,或者是一种物权,或者是一种非物权。然而,这里谈的分类是形而上学的分类,也可能是四分法,因为除了分类的两个简单的环节(项目)外,还有两种关系,即限制着权利的条件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一种权利结合着另一种权利出现,而出现这种关系的可能性特别需要加以研究。一种建立在人的方式上的物权概念是无论如何要排除的,因为不能设想有一种物会有对人的权利。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关系是否反过来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这个概念,即一种建立在物的方式上的对人权概念,不仅没有内在矛盾,而且本身也是一个必然的概念,(由理性中的先验得出来的)属于“我的和你的”概念中的概念,把人按照类似于物的方式加以对待,虽然不是指全身的各个部分,但是却占有他,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把他当作物来处置。
2。建立在物的方式上的对人权概念的理由
建立在物的方式上的对人权的定义可以简要地概括为:“这是一种人的权利,即把一个人除了人身之外作为物(3)来占有。”我特意说“一个人”(die Person);因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人(der Mensch)(4),如果他犯罪丧失了人格(成为农奴、卖身奴),是可以把他作为物来占有的,但是这里谈的并不是这种物权。
那么,前一个概念“作为法律天穹上的一种新现象”是一颗奇异的星星(一颗长到最大的星星,一种前所未见的,而后又逐渐消失的,也许会再次反复的现象),或者仅仅是一颗流星?这个问题现在应该研究。(5)
3。例证
拥有外在物作为自己的东西就是法律上的占有,然而占有是可能使用的条件。倘若这一条件仅仅是作为物质的条件而设想的,那么占有就是持有。——仅仅是权利上的持有,虽然不足以把持有对象说成是“我的”,或者使它成为“我的”。不过,不管出自何种原因,如果我有资格,迫切希望持有一个摆脱或挣脱了我的强力的对象,那么,这个权利概念不外是一种迹象而已(如果由原因产生的效果),表明我自认为有资格把它当作“我的”,我对它的关系也是理性的占有,而且也从这样的角度来使用这个对象物。
“他的”(东西)在这里虽然意味着对另一个人人格的所有权〔因为所有者不可能是一个人(der Mensch)对自己的占有,更不可能对另一种意义上的人(die Person)的占有〕,这仅仅指有享用权益是“他的”,即直接使用这个人,把他当作物一样来使用,使他作为手段为我的目的所用,然而不能损害他的人格。
但是,作为使用的合法性的条件,这个目的必须在道义上是必要的。丈夫(男人)既不能把妻子(女人)作为物那样享用而去追求妻子,不能在动物共同属性方面直接感受与妻子寻欢的乐趣,也不能仅让妻子献身于他而没有双方都献出他们自身的人格(即肉欲的或兽性的交媾),也就是说,不能在没有结婚的条件下发生关系。婚姻作为相互献出他个人又占有对方,必须在此之前缔结:通过利用对方的身体使自己不丧失人格。
没有这个条件,肉欲的享受对于原则来说(纵然不总是依据效果来看)是野蛮的。粗俗地说,或者女方是否由于怀孕和由此而来的,对她来说是致命的分娩而被搞得疲惫不堪,或者男方则是否由于女方经常要求使用男方的性功能而被弄得精疲力竭,这只是享受方式上的区别。一方对另一方来说,在这种相互使用性器官方面,确实是一件能够消耗殆尽的东西。因此,通过一项契约取得这种能够消耗殆尽的东西,可能是一项违反法则的契约。
同样地,丈夫和妻子可能没有生育孩子——双方粗制滥造的作品,双方都没有对孩子以及相互间承担责任要抚育孩子:这样一种情况就等于把获得的一个人当作一件物,仅仅在形式上看是如此(即按照纯粹建立在物的方式上的对人权来衡量)。如果孩子脱离父母的强力,父母(6)有权反对任何占有孩子的人,同时有权强迫孩子去做一切事情和听从他们的命令。当然,所要做的事情和命令与可能的法律自由不能相悖,因此,这也是一种用来约束孩子的对人权。
最后,当孩子成年、父母抚育孩子的义务终止时,父母还有权利把孩子当作服从他们命令的家庭成员加以利用,以维持其家庭,直至孩子离开父母而独立生活。父母对孩子的义务是从父母权利的天然限制而产生的。直到此时,孩子们虽然是家庭成员,属于这个家庭,但是从现在起,他们就属于家庭里的仆役。因此,他们无非是通过契约,作为训养物增加到家主的财富中去。——同样地,也可以根据一项建立在物的方式上的对人权,把这个家庭之外的仆役变为这个家主的财富,通过契约把他弄来作为帮工。这样一种契约不是一种纯粹雇佣的契约,而是献身给家主占有的契约,租赁的契约。租赁和雇佣的区别在于,租赁时,帮工受托做了规定了的和专门确定的工作,凡是有关家主福利(不是帮工本人的福利)的事,都允许叫帮工去做;相反,受雇做一定工作的雇工(手工工人或短工),并不委身为他人的财富,也不是雇主的家庭成员。——雇工有义务完成一定的劳务,但是在法律上不为他人占有,即使他居住在雇主家中,主人不能把他当作物来控制他,而是必须根据对人权,催促他完成通过法律手段命令他去做应做的、许诺过的劳务。——关于在自然法则学说中,一项陌生的、新增加的权利,就作这么多的解释和辨析,不过,这项权利以前已经一直在悄悄地应用了。
4。关于物权和对人权的混淆
此外,“出售废除租赁”(见31节)这个命题,也被指责为我在自然的私人权利(私法)中提出的异端邪说。
有人出租房子,在房客居住租期届满之前,就向房客宣布解除租约;如果他在不该搬出的时间内这样做,看起来像是对房客食言,初看起来似乎是违背契约所规定的一切权利的。——但是如果能证明:房客在签订租约时就知道或必然会知道: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出租人对他所作的许诺,自然地(不允许在租约中着重说明),也就是说,默默地与下述条件联系起来:只有在出租人在这个时间内不出售他的房子时才出租(或者在破产时不得不把房子交给他的债权人),这样,出租人并未违背他那根据理性的、本身也受制约的诺言,而承租人并不会由于在租期届满之前宣布废约而减少其权利。
因此,租约中所规定的房客的权利是一种对人权,某个人依据这项权利必须对另一个人尽些责任,它不是一种针对这个物的任何占有者的物权。
承租人本来能够保障自己在租约中规定的权利,可以获得一种对房子的物权:他只可以把租约刻写在出租人的房子上——作为固定在房子上的东西。这样做了,他就不会在协定届满之前因为财产所有人废约,甚至出租人亡故〔自然的破产或者文明的(法律宣告的)破产〕而被剥夺租权。如果他事先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想保持自己的自由的话,可以同别处订立条件更好的租约,或者因为财产所有者不让他在房子上刻写这样的义务,那就可以得出结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废约问题上(明文规定的期限除外)都意识到,他们达成一项默认的有条件的契约,也可以根据习惯,重新解除契约。通过出售废除租赁来证明这种资格,表现在由这样一种光秃秃的(7)租约所引起的某些权利(法律)的结论:因为承租人的继承者在承租人死后,并没有义务继续租赁,因为租赁只对某个人有约束,这个人一死,约束也就告终(但是,宣告废约的法定时间总得张榜告示)。同样,没有签订特别的契约时,承租人的权利也不能转移给他的继承人,只要他在双方都在世时没有专门达成协议,赋予他有资格确定一个后承租人,他就不能把这种权利转让给继承人。
5。关于刑法概念讨论的补充
人在国家宪法的纯粹观念中,已经涉及到惩罚公正性的概念,惩罚公正性隶属于国家的最高权力。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惩罚方式对于立法者来说是否无所谓,如果这些方式作为手段是用以消除罪恶(如把占有他人财产视为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在作案人的人格方面(即对于同类人来说),必须注意尊重人类,而且,惩罚仅仅是出于权利的原因。因为我认为法律上的反坐法(以牙还牙的惩罚)从形式上作为刑法原则还一直是唯一的、由先验决定的观念(8)(不是出自经验,认为无论用何种灵丹妙药,为了这个意图都是最强有力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