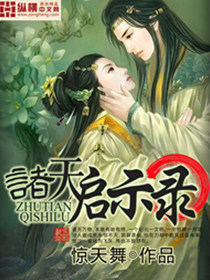南非的启示-第9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种族社会到阶级社会:宪政民主与南非多民族国家认同
这种从“黑白两党制”到“左右两党制”的变化对于南非这类种族矛盾复杂、仇恨根深蒂固、国家整合十分困难的社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以往曾经以南斯拉夫和印度这两个联邦国家作比较:这两国历史上都是缺乏统一传统,种族、民族、宗教、文化间积怨很深,族际国家认同缺少根基。但是印度一独立就实行了宪政民主下的“左右多元”政治,贫富各阶级选民通过代议制形成左右派各党进行博弈。而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都是跨族群的,博弈目的是在全国实现各自的“主义”,而不是闹独立,结果是越博弈国家认同越增进。而南斯拉夫实行“列宁式联邦”,不允许左右多元,却提倡所谓“民族平等”,结果每个民族都实行一党专政镇压异己,造成个个民族都有怨气,同时却允许每个民族的“共产党”突出个性、发展本民族认同。于是一有机会,各民族的“南共分支”便把本族的怨气引向他族,出现“族群多党制”,各党民意基础不是跨民族的“阶级”,而是各自“跨阶级的民族”,每个党都不以“主义”为诉求,只以“族权”为能事,小族争独立,大族谋压制。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这时又有米洛舍维奇之类的民族(种族)主义者废除“民族平等”,想建立以民族压迫求统一的体制,结果不但没能阻止国家分裂,反而使分裂变得流血成河。
印度和南斯拉夫的例子,以及种族隔离旧南非的例子都说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既不能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专政”体制下虚幻的“民族平等”基础上。
我们过去在“阶级斗争”名义下出现了太多的悲剧,造成如今谈“阶级”色变的后果。其实认真想来,多民族国家里如果能以“阶级认同”来淡化“民族认同”,那绝不是坏事。而真正的“阶级斗争”,即同一“生产关系”中不同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知识等)持有者为争取各自要素报酬最大化而进行的博弈,诸如劳资博弈、主佃博弈、债务人债权人的博弈等等。这种斗争通常都不可能是“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斗争。恰恰相反,由于真正的“阶级”是一种相对可变的、流动性的经济地位,不像民族尤其是种族那样固化,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博弈,尤其是同一生产关系中各方的“要素竞价”。在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应该算是最可能进行理性计算、讨价还价、折中妥协、共存合作的一类矛盾了。
而其他诸如民族、种族、宗教崇拜方面的矛盾不但对立双方身份固化,而且不是同一生产关系中的共存关系,加之这几种斗争主要是情感、信仰性的,往往没理可讲,无价可还,也难以妥协,变成“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都知道劳资谈判、主佃谈判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俄罗斯人和车臣人、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要达成妥协就困难得多;就算破裂,历史上真正的“工人起义”、“佃户暴动”不但极少见,其暴力规模也无法与民族征服、宗教“圣战”相比。
同时我们也知道,“阶级斗争”只有在代议政治体制下才能真正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而不是仅限于基层社会的纠纷。尽管“代议士”代表的不一定是“阶级”,但“阶级代表”却一定是接受了“阶级”选民委托的代议士。道理很简单:没有委托就构不成代理,而只有在代议制下,穷人与富人才可能自由结社形成工会、商会与政党,从而组织(不是“被组织”)起来,通过选举授权,委托其政治代理人“代表某某阶级”真正进行大范围的集体博弈,在国家政治层面争取利益。
在代议制政治舞台上,这些阶级“代议士”的斗争常常是激烈的,唇枪舌剑、嬉笑怒骂,甚至在镜头前推推搡搡,无处不在的争吵、斗争各方的互相“扒粪”、“抹黑”,让某些习惯于一片歌功颂德的人嗤之以鼻——但是实际上,这种斗争却极少可能是“你死我活”的。而产生“阶级代表”的过程更不可能充满暴力。相反,只有那些根本没有“阶级”授权、却拉“阶级”的大旗作虎皮的权力争夺,才与历史上“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皇权争夺那样动辄尸山血海。而这种争夺中据说是同一“阶级”中产生“代表”的过程,则往往比“阶级斗争”本身更血腥:谁不承认我是“代表”,我杀掉他就是了。正如德国左派作家布莱希特讽刺“民主德国”时所说:“如果人民不喜欢政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解散人民,另外选举一个人民。”'16'既然无需工人授权,“工人阶级代表”就像皇帝的宝座,斯大林杀了托洛茨基,他就是“工人阶级领袖”,而托洛茨基就成了“阶级敌人”。如果托洛茨基杀了斯大林,那就反过来,托洛茨基“代表”了工人阶级,斯大林就该是“阶级敌人”了。无怪乎那么多白俄贵族流亡海外斯大林可以不管,却对托洛茨基追杀到天涯海角,历时十年,终于在地球那一面把他用冰镐砍死——然而这样的斗争能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吗?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阶级斗争”并不可怕。而在多民族国家“左右”/“阶级”矛盾如果能够淡化民族、种族矛盾,这并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很好的事。这正是因为“阶级矛盾”要远比民族矛盾容易化解。比起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来,“阶级矛盾”更不需要以“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方式来解决,更不会损害、而只会巩固国族认同。“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失败,并不在于它主张用阶级矛盾来替换民族矛盾,而恰恰在于它不承认“左右多元”,而用所谓的“阶级专政”把本来容易化解的“阶级矛盾”人为地弄成了“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局面。这种理论在利益关系上把劳资对立人为激化成“阿拉伯以色列对立”的程度,在观念问题上像旧时宗教战争中“基督徒战胜穆斯林”那样去镇压“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在“阶级”内部争夺“代表”资格的斗争也变得如同争夺皇位般的血腥。于是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害,而各民族都受害的结果最终还是导致建立国家认同的失败。
但是“左右多元”的民主体制下,“阶级社会”却可以避免这种灾难。由于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非理性和难于妥协(南非实践的伟大恰在于实现了这种艰难的妥协),民主政治处理这类矛盾并不总是成功的(当然,不能说专制政治在这方面更成功)。但是民主政治处理“阶级矛盾”却容易成功。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搞民主制,尽量搞成“左右多党制”而避免出现“族群多党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甚至往往决定这类国家民主实验的成败。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个反面的教训,而印度(其实美国、瑞士等等也是这样)是个成功的例子,我们看到南非正在成为又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不仅在非洲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例子,在世界上也可以成为一个范例。因为与印度、美国、瑞士都不同,新南非的民主化本来出自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解放运动,“黑白两党”是一个没法回避的起点。可是新南非的政党政治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模式,国族认同将很难建立。道理很简单:选民的“左右”是易变的。这次大选我投左派的票,下次可能我就改变主意,成为右派选民了。因此如果一个党对自己的“主义”有信心,即使现在是少数党,它也会相信通过努力自己会变成多数党,而且信念越坚定,它越是希望争取多数,在全国实现自己的“主义”,而不可能希望离开这个国家。但是选民的族属却要固化得多,一个少数族再有信心,也不可能变成多数族,因此自我定位代表少数族的党易于产生离心力,而且信念越坚定,就越会走向分离主义。
新南非20年来政党政治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成功地向“左右多党制”转型,从而成功地强化了多民族国家认同。新南非的成功有力地反驳了那种所谓民族矛盾严重的国家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分裂的谬说,它证明恰恰相反:“左右多元”的民主体制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国家认同,代议制条件下真正的“阶级斗争”不但是温和的,而且恰恰有利于淡化民族矛盾,消除民族隔阂。
尽管南非治安不良,暴力犯罪频发,但南非的民主政治可以说是相当守规矩。南非政治博弈具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背景,但并不“你死我活”。姆贝基一派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但离开党照样可以搞政治。马勒马经常叫嚣暴力斗争,但他被“请出”非国大的过程却是完全和平的。运作正常的代议制民主一般都有个政治斗争从“实质化”到“形式化”的过程。初期的政治博弈一般都反映实在的社会矛盾和“主义”之争,各方背后可以看到社会分层明显不同的选民基础。但是,由于民主政治都要多数票支持才能胜出,而什么主张能够赢得多数,其实选择范围并不大,因此在一定时期过去、若干回合以后,竞争各方、尤其是最有竞争力的两大党立场往往会趋同,选民的“阶级背景”会趋于模糊,左派、右派都会趋于“中左”、“中右”乃至“中中”。这时竞选就会更多地流于形式化,更多地成为竞选者个人形象、竞选技巧上的竞争,从而给人以无聊的“政治秀”印象。其实,这正是民主政治运作稳定、成功,能解决的问题都已获得尽可能解决的体现。
代议制下的阶级斗争:新南非的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
南非的民主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因此,南非议会、非国大党内的各种民主场合的交锋具有明显的社会背景。纯粹比赛偶像魅力的“民主秀”成分较少。换言之,除了民主政治的程序优点外,南非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还是非常突出的。相对形象不佳的祖马能够胜过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姆贝基,就是因为祖马的社会基础比姆贝基雄厚。而王晓鹏先生提到的工会太强、罢工太多等等,也是目前南非“阶级社会”的写照。
种族隔离时代留给新南非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贫富首先存在于“黑白”之间。种族隔离时代最严重的1970年,黑人的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6。8%;种族隔离末期的1987年这个比值提高到8。5%;过渡期的1993年为10。9%;新南非初年的1995年为13。5%,2000年提高到15。9%;但2008年由于经济危机,黑人失业率升高,这个比值又跌到13。0%。'17'当年发生的“排外骚乱”就与此有关。
而另一方面,新南非黑人内部的贫富分化又比白人内部更高。2004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白人中仅0。36,并不高于欧美,而黑人中却达0。51,不仅高于白人,也高于有色人和亚裔,加上黑白差异,导致南非全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59。民主化以来,南非的黑白收入差距下降了。特别是由于姆贝基政府出台了著名的《黑人经济赋权法》(缩写为BEE,被戏称为“蜜蜂法案”),鼓励黑人企业家成长,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让一部分黑人先富起来”。十多年来“富黑人”(又称“蜜蜂富豪”)持续崛起,对缩小这种差异很有影响。
“蜜蜂富豪”的快速崛起不仅由于种族隔离的废除,与新南非的经济改革也很有关系。我以前曾指出,旧南非经济具有“种族社会主义”的特点,在白人私有经济发达的同时,为了“布尔人的团结”,给“穷白人”提供铁饭碗,并且强化白人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旧南非建立了庞大的国有经济。种族隔离末期南非出现经济危机,“种族社会主义”难乎为继,变革国有经济就成为趋势。非国大政府废除种族隔离后实行种族和解政策,并没有像“黑人统治”的津巴布韦等国那样打击、没收白人私有经济,但对于原来白人国家的国有经济则明显加大了改革力度。一方面让黑人进入国企,改变员工和管理层的种族结构,另一方面从长远讲为了推行强调市场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从眼前讲为了解决转型期国家的财政困境需要拍卖国有资产,于是非国大掌权后的南非也出现了一轮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在初期,这种改革只是使一些“穷白人”丢了铁饭碗,黑人并没有多少异议,无论从喜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的角度,还是从充实国家财政增加黑人福利的左派角度也都能得到支持。但很快,一些“有来头”的暴富者就引起了非议。如2004年10月媒体披露,南非公共投资委员会将出资购买国有南非电信公司(TELKOM)15。1%的股份(市值约60亿兰特,约合5亿多美元),并很快转卖给一个名为“大象”的黑人财团,而这一财团恰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