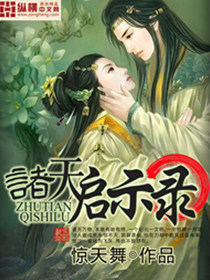南非的启示-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人当局利用因卡塔的保守色彩,给予暗中支持,使它成为黑人家园政治组织中唯一具有全国影响的党。因此非国大与因卡塔的对立可以说是集中了“黑白矛盾”、黑人诸部族间矛盾、激进党派与保守党派的矛盾、黑人解放组织的现代潮流与部落传统的矛盾、中央政府与黑人家园自治倾向的矛盾等诸多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是难于化解的。早在民主进程开始前的80年代,双方支持者就在祖鲁人聚居的纳塔尔省频起暴力冲突。民主进程开始后,因卡塔改名因卡塔自由党并宣布向全国各种族开放,它与非国大的冲突也很快扩大到纳塔尔以外,尤其是祖鲁族流动劳工集中的约翰内斯堡等南非政治经济中心地区。
南非白人中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也有宿怨。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在所谓“文明的白人”间发生的战争中以野蛮著名,英军大搞“三光”政策,大片地区的布尔平民被关入集中营,村庄夷为焦土,2万多布尔人妇孺在集中营里被虐待而惨死。人们至今犹有余痛。但另一方面,英裔在种族问题上远比阿非利卡人开明,而半个世纪以来南非一直是后者当政,并推行所谓反“英国化”政策,英、布之隙与“黑白矛盾”相交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此外南非还有有色人(混血人)、印度人等问题。在当今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众多积怨极深的种族、民族与部族同处一国,时逢世纪之交的空前剧变,从种族隔离到种族开放,从事实上的一党制(南非虽实行西方政体,但由于英裔的客居心态和布尔人的特殊的集体危机感,自1948年以来实际上一直是布尔人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到多党民主,不久前的阶下囚如今一举掌权柄。而所有这一切又恰恰发生在南非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和连续三年国民总产值下降的严峻背景下,这怎能不令人捏一把汗呢?如此危机之中而求返乱为治,似乎只能靠奇迹了。
奇迹来源于和解
就在南非大选前20天,夸祖鲁地区动乱还在加剧,几天内有120人死亡,因卡塔与白人右翼仍抵制大选并发出武力威胁。人们纷纷恐怖地谈论“非洲的波黑”。然而这时南非的政治气候已悄然由阴转晴:在非国大与国民党的努力下,不仅在全国,而且在祖鲁人中拥护大选的人也不断增加,布特莱齐实际上已是嘴硬手软了。这时曼德拉不失时机地向他伸去橄榄枝,在拒绝实质上的分治要求的同时作出了承认祖鲁王地位等让步姿态,布特莱齐也心领神会,在最后时刻作出了参加大选的决定。于是:几年来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在大选前几乎是戛然而止,全国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和平,整个大选过程也出人意料地严肃、平静而有秩序,投票率之高,各方对大选结果的一致承认,都超过人们的预想。
在这划时代的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中,非国大与国民党这一对老对手都取得了超过预料的成功。非国大得票率达62。5%,超过事前各种民意测验的54%—57%,国民党得票率为23。9%,也超过了事前测验的15%—20%,而因卡塔得票率则低于事前预计。可以说,大选的结果是:曼德拉赢了,而德克勒克也没有输。
大选之后一个月内,曼德拉总统已就职,新内阁已建立。约翰内斯堡股市行情大涨,国外对南非经济前景看好,投资意愿增加。继1993年年底南非经济开始缓慢复苏、通货膨胀率下降之后,当年经济又进一步好转。
总之,作为多种族民主国家的新南非如初生婴儿已经呱呱坠地。尽管她的成长过程可能多灾多病,但她能在如此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顺利出世,已堪称奇迹。当今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在剧变中经受不住震荡而解体、以致出现内战的有原苏联、原南斯拉夫与原捷联邦;民族压迫结束后各解放组织或各部族即互相火并、大打出手的有南非的两个近邻莫桑比克与安哥拉以及阿富汗等;固有的部族冲突或地域冲突使国家四分五裂的有非洲的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以及亚洲的也门等;由一党制向多党民主过渡中出现权威真空、政治动荡、社会失序的国家也不少。南非何以不然?
国际社会的帮助是一个原因,但这种帮助既不足以使和平降临波黑、卢旺达等国,又怎样保证南非的种族和平?
各方力量相对平衡、“可迫和不可迫降”也是一个原因。但“不可迫降”并不意味着就能握手言和,它更可能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还少吗?
用旧制度的危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或良心所向来解释这一切更属空洞无力。旧制度的危机可能导致“破旧”,但未必能导致“立新”: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种不是解释的解释,因为社会发展所忌讳而却发生了的事太多了。至于说民心所向,那么当时南非社会上各种激愤情绪的民意基础并不亚于理性。可以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跟着“民心”走,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使“民心”跟着自己走。
简单地说,南非“奇迹”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了理智。或者说,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这乍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奇迹”之难得正是因为这不易做到。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南非得以免于内乱,多亏了曼德拉、德克勒克(公正地说也有布特莱齐一份,尽管较为次要)的个人理智。法国《青年非洲》周刊在大选前夕说:“可能使南非在不可控制的恐怖活动中发生崩溃的唯一假设是:曼德拉遭暗杀。”一个路透社资深记者从波斯尼亚赶到南非采访大选后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双人舞虽然跳得很艰难,但他们给南非带来了希望。波斯尼亚没有出现这样的政治家,这就是波斯尼亚悲剧的原因。”
人们可以把曼德拉与德克勒克比之于英属印度的甘地与蒙巴顿。应该说,前两个所表现的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比后两人所表现的更为难能可贵,当然,这种比较仅限于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局面。
世人多以新印度归功于甘地,实则蒙巴顿亦有造于印度甚多。然而德克勒克比蒙巴顿更难得的是:蒙巴顿只是把印度交给了甘地们,而德克勒克则不仅把南非交给了曼德拉,而且还要作为曼德拉的副手(当然,同时也是政敌)同他合作建设新南非。蒙巴顿只是代表宗主国为其不光彩的殖民统治史赢得了个光彩的结尾,而德克勒克则作为南非土生白人的代表,在结束不光彩的过去的同时,开创了光彩的未来。
无疑,德克勒克作为“无路可退”的阿非利卡人的代表,在说服自己的选民顺应历史潮流、纠正以往的错误时要比蒙巴顿克服更多的困难。但历史会证明,他的努力除了使他所代表的势力卸除罪恶历史的沉重包袱外,不会失去他们应得到的任何东西。南非种族和解进程开始前夕,国民党与阿非利卡人中的一批开明派曾退党并另组民主党,主张顺应时势,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与黑人分享权力。结果应者纷纷,很快成为当时议会中第二大反对党,对国民党的地位构成了挑战。然而和解进程开始后,由于德克勒克采取主动,不仅接过了民主党的主张而且加以实践与发挥,从而不仅稳定了自己的队伍,而且得到了英裔白人日益明显的认同。民主党却因提不出更新的纲领而失去吸引力,影响趋于下降。
当然,目前的南非政局属于过渡性质,可以设想随着过渡的完成,白人政党的地位也许会再有所下降,甚至成为在野党。但无论如何,她在南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仍然将高于(比如说)史密斯白人政权结束后津巴布韦政坛上的白人力量。正如德克勒克在大选后所说:没有非国大的同意,他再也无法统治了。但同样,“没有人民以及我所代表的组织的支持,任何政府都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而历史也会铭记德克勒克个人在建立这样的体制方面做出的贡献。
与甘地相比,曼德拉受到的迫害要更为严酷,他身陷囹圄28年,几乎等于甘地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的全部时间。而他在和解进程开始后所处的位置则比甘地更为有利。然而28年牢狱之苦和胜利者的位置却没有丝毫损害他的冷静与宽容。甘地自始至终是个非暴力主义者,而曼德拉作为非国大武装斗争战略的提出者和“民族之矛”的首任司令,不是在失败的时候而是在胜利前夜提出反思并改奉非暴力原则,这无疑需要极大的理智与自我审视的勇气。可以说,“见坏不上,见好不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人性弱点,前者有利于专制,后者导致以暴易暴的可能。人们往往不敢反抗那只准拥护的政府,而同时又不愿拥护那可以反对的政府。这种“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的毛病是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畸形病。而能够有“见坏就上”的勇气,或者有“见好就收”的宽容,都是难得的,同时具有这二种性格的的人,就更不是任何民族都可遇的,而曼德拉最可贵的,正是这种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既敢反抗一个只准拥护的当局,又能宽容一个可以反对的对手的这样一种精神。今日的南非,能够阻止复仇主义灾难、恢复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的,可以说只有曼德拉。当然图图、德克勒克等人也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当哈尼遇害后在电视上出面呼吁人民保持理智与冷静的,不是德克勒克而是曼德拉;谴责自己一派中的恐怖主义者并支持警方予以处置的,是曼德拉;表示尊重反对派并声称“如果非国大领导的政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你们可以推翻她”的,是曼德拉。正是曼德拉,在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组织在过去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犯过侵犯人权的过失,并主持非国大成立调查委员会,公布本组织在国外集中营建犯人权的行为的报告。事实证明,这种坦诚的态度不仅无损于、而且大大提高了非国大的声望。
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难得的。民主进程的这几年恰逢南非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不景气,国家在经济困难的谷底徘徊,老百姓怨声载道。作为反对派的非国大完全可以全力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取得政治效果,更何况非国大传统经济纲领本来就是不以市场经济为然的。但曼德拉在审视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后认定了市场经济是方向,因而除了抨击现存经济制度中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的内容外,对政府的市场经济方针没有作更多的批评,反而一再表示要继续这一基本方针,留用现政府全套经济班子并对其工作予以肯定,同时放弃了非国大经济纲领中不切实际的内容。这种负责的态度,是他高于一般“政客”的可贵之处。
总之,南非的危机期待着“奇迹”,而“奇迹”产生于和解,像曼德拉、德克勒克那样具有理智与和解精神的政治家,有之诚幸莫大焉。
然而问题当然没有到此为止。前面说过,人民相信政治家,政治家表现出理智,是南非得以化险为夷之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君固材矣,奈国人之不信何?”
那么国人凭什么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一些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像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情形一样?可见其中又非仅理智而已。应不应和解是一回事,能不能和解又是另一回事,南非的启示于此值得玩味之处尚多。
理智与道义
如前所述,过渡期的南非之所以能转危为安,是因为“人民信赖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出理智,或者说,人民虽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
那么,政治家为什么能够表现出理智?识者云:因为他相信理智。这自然不错。然而在那样一个社会情绪亢奋的时刻,更重要的不是他相信什么,而是他能做什么。所以更确切的回答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除了表现出理智外,不需要表现出别的——他作为公平正义化身的道德形象,已经通过几十年的奋斗生涯得到了充分表现。他已无需“哗众”就能“取宠”。
而人民又为什么信赖政治家?识者或云:因为人民素质高,所以接受了理性原则。或云:因为人民素质低,所以只能唯领袖马首是瞻。也许二说各有所据。但我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从政治家身上除了看到理智之外还看到了别的——社会公正与道义。
就曼德拉而言,他在危局中之所以能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理智,当然是有其思想基础的。曼德拉所在的非国大在1912年成立(时名土著人国民大会)时本是以温和、改良、合法反对派的形象出现的,并在此后30年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形象。但是,由于南非白人当局的不理智和残酷镇压,致使合法反对派运动受挫,人们对改良失望。因而从其第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