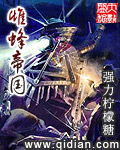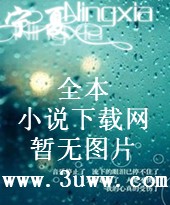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让陶澍梦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军机大臣潘世恩等四人,捧着六寸长宽的专书“印心石屋”的匾额给他,后面写了“御书赐之”,有道光皇帝的签名,还有两方皇帝专用的印文。
满朝臣子知道后,都羡慕得不行。这可是最高褒奖啊!
好事还没完。
过了一段时间,道光皇帝又召见他,专门问起:我给你写的“印心石屋”匾额收到了吗?陶澍赶紧叩谢,一高兴,又跟道光皇帝聊起天来,历数史上那些皇帝给大臣题匾的故事,后世全成了佳话。道光皇帝更加开心了,自己给陶澍题字,现在还只是新闻,将来也要成为历史佳话。他开心了,再问:我题的字,你准备挂到哪里?
陶澍说,准备刻在石上。再问:石门何人所建?答:天生的,非人力可为,有七八丈高。
道光皇帝一听,说:我上次写的太小了,那么大的石壁,要配大字,我另外再给你写幅大字,我大字比小字写得好。
陶澍一听,激动得不行。哪里有皇帝两次给臣子题字,而且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第二天,陶澍就收到了新题字。幅长九尺多,每个字高宽各在一尺六寸左右。他赶紧收好,不久就刻在家乡的印心石上。随后岳麓山、庐山、金陵等10多处地方,都刊刻上了。
自己两年前人生最得意的大事,居然传到家乡省偏远的醴陵县来了,自然高兴得来不及。陶澍同时想到了,能知道这件事的作者,对自己又如此了解,对时事又如此熟悉,一定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关键还是,对联概括得那么好,立意高远,文字大气,气势浩荡,抬人,又不着痕迹。
我们回到对联,就能看出玄机:
“春殿语从容”,有如临其境感,仿佛是现场描画出来的。左宗棠又没看到,却可以凭借想象,活灵活现地赞叹陶澍在道光皇帝面前从容作答,满面春光,如沐春风,这既显得君臣关系亲近,又显得陶澍不亢不卑,春风得意蕴含其中。
“廿载家山印心石在”,陶澍1802年中进士,十年散官,授职编修,后迁御史、给事中。 1821年调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 1823年授安徽巡抚。离开湖南做官, 20多年了,谁帮他记得这么清楚?
印心石本是他个人的自豪,经左宗棠这么一写,成了“家山”的自豪,也就成了所有湖南家乡人的自豪。既像在说事实,也在借事实夸人。
“大江流日夜”,说到了湘江与长江,即湖南与中国。湘江日夜不停地奔流,在出洞庭湖处汇入长江,指陶澍第一个将湖南人带进了全国,也暗指陶澍一生伟业千秋永在,取杜甫名诗“不废江河万古流”之意。
“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既是明说现在醴陵代表整个湖南,热切期盼热情欢迎陶澍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也暗借晋代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督八州军事”的典故'4',赞美陶姓远祖光荣的历史。这样将陶澍与陶家的祖先一并都表扬到了,历史纵深感很强,却又不显得突兀。
这么杂的事,这么多用意,简单两句话,要全部融合,高难度。
这副对联妙在,说是夸奖、吹牛拍马吧,又全是事实,看不出奉承痕迹。说是全在道事实、谈历史吧,寄托的情感,却在浩荡奔流,轰隆隐鸣,不可遏止,不像在客观述事。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评价大活人。对事外人而言,反正两方都完全不知情,全是陌生信息,怎么写都差不多;对被写的人,就完全两样了:你自己怎么样,想要表达成什么样?没有谁比你清楚。自己有时不一定能准确概括出来。别人评价,能说中一半,已经需要超凡功力,算“知人”的高人。能够说得让自己震撼,已近似“天人”。
对高官陶澍来说,左宗棠这副对联,巧就巧在,它像一次最逼真的进士考试,而且是开卷考试,陶澍既出考题,又现场阅卷。这样的考试最靠谱,这种对联,即使想要抄,找不到地方抄,因为现场命题作文,蒙是蒙不过去。考官的水平摆在那里,进门沿路,陶澍看过的劣质对联,还算少吗?
对智慧高超、阅人无数、经事累累的陶澍,不需要更多了,只要凭借这短短26个字,就能够准确地判断,信手写出这样一流对联的人,是个天才。
他再亲眼一见左宗棠这个壮实如牛、满身是劲的青年人,基本就可以判定:这样的人才,只要走对了路,一生会有怎样一个不可限量的前程。而且,他很可能已经在内心里掂量比较了一下,以自己的同龄之事做了比较,感到左宗棠论人比才,在自己之上。爱才是有才能的人的通病,陶澍内心里认定了,高兴是肯定的,只是他不会表现出来。一个经验如此丰富老到的大人物,不会在毛头小伙子前喜怒形于色。
这些,左宗棠自己就不一定知道了。一个25岁的小青年,聪明、有才能是一回事,但人生阅历、生活经验,几乎没有。天分再高,永远不可能代替阅历与经验。他也许只是觉得,遇到大人物了,本能想接近,通过他,带给自己帮助。但他的倔强与叛逆,个性与自尊,让内心里生出一种抵触的情绪,男人得靠本事拼出来,他不想通过任何人扶着自己成功,他只期望有个引路的人。
陶澍看似淡定,其实比他要急。不单因为他预感到身体快撑不住,在世时间不多了,作为湖南在官场上第一个考出去升上官的大人物,他得考虑为湖南留下自己百年后的东西。
从年轻时目睹复杂的官场关系,几十年来逐步经历满清官场争斗,对显规则与潜规则,明权力与隐权力都了然于心的高官大员,他这时有一个梦想,要将湖南一批有才能、有想法、有勇气的青年才俊,带出来,通过让他们抱团的方式,来改变湖南官场两千年来人才全面死寂的萧条状况。
左宗棠无疑是这样的青年才俊。因此,陶澍偶然发现了他,一方面要继续不动声色地考察他;同时,要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一有机会就要适时地提携他,让他尽快地找到用武之地。
这真是一次旷世奇遇,我们或许还有疑惑:陶澍真的就凭一副对联,敢如此全面肯定左宗棠?
事实上,在看到对联之前,陶澍对左宗棠的名字、事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一说就有点神了,难道陶澍有专门的情报人员,一直在暗地网罗湖南的年轻士子?
当然不是。
这一切,全因左宗棠一个同龄朋友的推荐。
朋友名叫胡林翼。
识左托孤
清朝官场,流行推荐。同乡、“同年”、同学、亲戚、朋友相互推荐,成为时尚。
明明有科举制度,全国人才全都被考试筛了又筛,朋友再推荐,岂不是画蛇添足?
原因在于科举考八股,选拔上的考生,不一定有办事能力。会背书、善空谈的官员,有几个无所谓,多了国家就头痛。管理国家,事情大,责任重,毕竟需要大批真正有才能、懂实干的人。那些被考试误筛掉的人才,要再被选上来,最好的途径,就是推荐。
推荐最有说服力的是“同年”或同乡。“同年”是指那些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时名字跟自己写在同一张榜上的人。用今天话说,就是跟自己在同一年同一科“高中”的哥们。官场上最铁的关系是“同年”,科甲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
左宗棠与胡林翼,是同乡、校友、朋友。同一年参加进士考试,但左宗棠没中,算不上“同年”。胡林翼推荐,多因他个人特别讲“哥们义气”。
左宗棠的好朋友不多,但铁哥们有。他独立不依,个性鲜明,不仅在清朝官场中十分另类,格外打眼,就是在封建官场两千年中比较,也是特立独行,反感他的人都敬而远之,喜欢他的人才会死心塌地。
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此孑然立世的人物,离不开朋友支撑。
胡林翼支撑他最铁心、最死心塌地。
胡林翼与左宗棠相同的一点,天分极高。当时湖南人才,论天赋他俩前两名。但就性格而言,他们是两种人。这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有关,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
一个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基本就定下了他的性格、习惯、偏好,看事情的眼光,做事情的风格。
左宗棠出身贫寒,从祖父起,每代人以耕读为生,都没有什么大成就。曾祖逢圣公只做到了县学生员。'5'祖父左人锦一生也只得了个国子监生头衔,也等于是个秀才,有资格去见县官,但没什么实权。父亲左观澜一生努力,才得了个县学廪(lǐn)生,也就是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左观澜起早摸黑,勉强维持一家温饱。
穷人的孩子能吃苦,早当家。毛泽东的家境跟左宗棠差不多,他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感受接近。左宗棠自己形容小时侯的生活,“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嘱儿孙咬菜根”。
与“咬菜根”的左宗棠相比,胡林翼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他家境富饶,有良田数百亩,雇工经常上百人,是真正的大地主家庭。胡林翼祖父以上,都有诗文著作传世,父亲兄弟四人,都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又是。
21岁那年,胡林翼与左宗棠相会在北京。两人年龄同,事情同,但压力不同,气质不同。胡林翼书香世家,以读书为职业,反正是要考的,哪怕考到80岁,只要没中,职业还是考试。所以他一点不急,带足钱在京城花天酒地。
左宗棠就不同了,考试需要本钱,他已结婚,要先养家,积足了本钱才能考试。所以1833年,两人同时落榜,一半像书生一半像农民的左宗棠极度失落,花花公子一样的胡林翼根本没当回事:早得很,急什么。他不急左宗棠会急,咬着菜根被含着金钥匙的人邀去一起玩,玩多了胃疼。
客观地说,胡林翼是个天才。这样生于富家,既有才气又有浪荡公子哥儿气质的男人,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在各种复杂关系中穿梭自如的灵活性,左宗棠再怎么努力,也学不来了。人天性会追求自己所缺的东西,这样两个人,会本能地相互吸引。两人果然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一面而定终生之交。
但世事往往就这么奇怪,你越不把它当回事,反倒越有那么回事。 1836年, 24岁的胡林翼,再次上北京参加会试,一笔写下去,中了进士。
胡林翼是命运的宠儿,他不但科场得意,情场也得意。嘉庆年间,陶澍以“给事中”(给读jǐ,给事中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的身份考察川东,经过益阳,偶然发现了7岁的小朋友胡林翼。陶澍看胡林翼小朋友很可爱,手忍不住去摸他脑袋,夸奖几句。没想到小小的林翼非常生气,抗议说:你知不知道,男子的头随便摸不得?!陶澍大为惊讶,觉得小朋友相当有个性,当即相中,收为女婿。'6'18岁那年,胡林翼在桃花江陶氏别墅与陶澍的女儿陶静娟结婚,正式做了陶澍的乘龙快婿。陶澍从娃娃抓起, 20年来对他进行系统的教育培养,为他成为名臣打下坚实的基础。
胡林翼身上有湖南人鲜明的共性:讲义气,够朋友。跟左宗棠结识后,见识了他的文才,十分佩服。恰好1833年左宗棠在京,一口气写了10多首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诗,胡林翼都读过。
进士虽然没考上,但左宗棠这些诗却在江湖上传开了,圈内人都知道他人牛气,大口气,有才气。 1835年,胡林翼带着这些广为流传的江湖诗,第一次向已做两江总督的岳父陶澍推荐左宗棠,“称为奇才”。
有了胡林翼这些铺垫,两年后陶澍意外遇见,又亲眼见识了左宗棠的作品,看到了他本人,心目中的判断得到印证。
陶澍认可,对左宗棠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他被纳入湖南官场人才梯队。
陶澍培养接班人的方式很特别,依然是前面的“胡林翼模式”——联姻。
但25岁的青年,已不是7岁小孩,陶澍找个什么样的恰当方式,来跟他提?
1838年, 26岁的左宗棠在京会试完毕,根据上次见面的约定,绕道去南京两江总督府看望陶澍。
一年不见,再见面陶澍很客气,安排专人招待左宗棠,让他的生活过得安逸又舒服。
但不知是陶澍事情多忘记了,还是他嫌左宗棠年龄太小,反正见面热过后,像再没当回事。一个月,两个月,时间像石上水滴一样漫不经心。左宗棠一直被凉在馆舍里,不被闻,不被问,当空气对待。
左宗棠一天到晚都等着被召见,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见。时间像千年溶洞里的水滴,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会掉下来。那样的干等,多无聊啊。左宗棠心气实在乱了,就偶尔出门透口气。这样,他就结识了陶澍幕府里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个叫陈公銮(luán,铃铛,代指帝王车驾)。
人无聊容易生事,人与人打交道,会发生故事。文人与文人打交道,总会扯上女人的事。野史说,陈公銮约他去玩,常一起游曲院。有天,陈公銮跟一个歌女开玩笑,问如果从良,愿意嫁给谁。歌女看着他们俩,不假思索地说,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