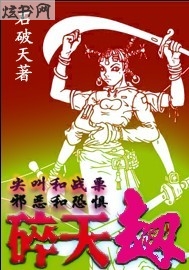上海生死劫-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你有好印象的。她们有没有打听我对文革的看法?〃我问。
〃那书记讲过你的态度是正确的,你记得吗?没关系,明天我去菜场见到她时,会把你这番话告诉她的。她每天早上要去取牛奶的。阿姨说着就回厨房去准备晚饭了。
她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无意中把要向支部书记汇报我情况之事泄露给我,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
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女儿也已经死了,我对上海别无他恋了。虽然在那时看来,要想离开中国的念头是太不现实且也决无可能,但我认为必须牢固树立这种念头,伺机争取机会。
看来,是上帝令我抬起双目,使我能看见地平线上遥远的青山。
第十四章寻求正义
我常常梦见女儿被残酷地折磨、受刑,在溅满血迹的房间里死去。醒来时我都喘不过气。我躺在黑暗中,心猛烈地跳着,一幕幕可怕的幻景继续出现。我决定亲自到南京路上海体育协会大楼详细地观察一下。在我健康情况许可下,应当立即进行这会使我伤心的行动。这样我能对曼萍死亡的地点有个明确的概念,如果情况许可,我还得进行一些调查。但我不能把这种意图让阿姨知道,我怕她可能会向居民委员会里的大姊汇报。所以我只能利用我每日外出散步的时间乘公共汽车至南京路。所以,我有意识将每日散步的时间延长至每天两小时。
〃你这几天外出散步走了这么多路!你的身体真的已健壮多了,你脸色红润。快歇一会!让我给你倒杯茶,〃我回到家里,阿姨常会直着嗓门说。
在我每天长时间外出散步已成了常规之后,阿姨不再对我离家过久而唠叨。我认为这已是我施展计划的时候了。
南京路是上海交通的主要干线。从外滩黄浦江通向西郊,横贯全市。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之前,上海体育协会大楼是国际青年会的总部。它位于南京路中段,面对过去的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公园。从我家去那里需要乘半小时公共汽车。正像上海的一贯情况那样,公共汽车总是很拥挤的。上了车,我没有力气往里挤,只得立在车门口,由四周挤满了的人群支持着才能站稳。站在我身边的那位女乘客时时把我的胸部挤得那么重,我想她可能已听到我咚咚的心跳了。一路上我非常担心,恐怕此去会发生一些想不到的情况。所以我思想上强烈迫切要去看看,但是情感上却又想回家。最后当公共汽车到了目的地的停车站,我仍犹豫不决。可是车上的人都要下去,我被挤出来的乘客带下了车,发现我自己已站在人行道上了。
我挤在人群中漫步走着,两眼望着马路对面那座大楼。体育协会隔壁是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两者都是三十年代的建筑物,但现在仍是上海市容的主要标志。这两所大楼上挂着的红布横幅在秋风中飘扬。横幅上写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政治是统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大楼屋顶上的霓虹灯又照着另一条口号,鼓励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当四周的人看到我抬头欣赏着上海城市的繁华街景时,认为我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外地人。没有人会特别注意我。我在人丛中摇摇晃晃地走着,两眼盯着上海体育协会的楼层寻找窗户。马路上的一群群行人猛力将我推来挤去。
人民公园门口,男女老少在排队购买门票。有些人在等着他们的朋友或亲人。我停下来和他们站在一起,隔着马路再望着对面那座大楼。但我只数到第八层楼,没有见到九层楼,八层楼之上就是倾斜的屋顶了。为了不想受人注意,我来回徘徊在公园门口,好像是在等人那样。我仍向上望着那大楼,但就是看不到人们说曼萍跳下来的九层楼。我一边分析着新发现的重要情况,一边漫步经过人民公园,然后又回头走回去。这时才看见上海体育协会大楼旁边的第九层楼及其上面的窗。那扇窗并非面对南京路。它位于大楼与一所很低的两层楼住房的狭弄上面。那扇窗户很狭窄,并竖着铁栅。一个人的身体能否从铁栅的空隙处挤出来,我尚不能轻易断言。
我所发现的情况和听人传说的完全不同,我需要时间来加以思索。我买了一张门票进入人民公园,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那里望得见对面大楼顶上的九层楼。我看着那装着铁栅的狭窄窗户,思索着我女儿死亡的真相。我认为除我所了解的以外,还有更多其他的情况。暖和的阳光带来一阵微风,刮得地上的秋叶沙沙地发响。我虽然听到马路上来往车辆的嘈杂声和人们的喧闹声,但在我充满了悲愤的内心却感觉极端的孤独,孤独得像一个被隔离在荒岛里的人一样。
我是否要再走向对面马路去敲体育协会的大门进去调查呢?我反复几次问自己,但不俄作出决定。一个小女孩骑了辆三轮脚踏车从转角的马路上过来,她的妈妈在后面跟着。当她加速前进时,她妈妈就叫着,〃慢慢骑!当心!〃但那个小女孩踏得更快了。她乌黑的眼睛淘气地向后看着她的妈妈。她们母女在我面前经过,消失在一群灌木丛后面。
当我离开公园走向公共汽车站时,我两眼看见到处都是曼萍,马路上的每个青年妇女和每个小女孩看上去都像是我的女儿。我心中一阵阵的刺痛,使我比在监狱里的任何时候感到更孤独更无助。公共汽车站里挤满了人,一辆车子开过了站也没有停下。我鼓足勇气坚决转向人行道,过了马路。在那体育协会旁边的狭弄口,有个青年妇女坐在一只矮凳上结毛线。
〃你住在这里吗?〃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继续结她的毛线。有些人从这里的人行道上走过,但没有往我这方向看。我发现这些房子是靠着体育协会大楼的墙壁造的,占了那条狭弄的一半面积。
〃你在找人吗?〃那青年妇女抬起头问我。
〃我是北京来的。〃我说谎道,〃我听说在一九六七年,一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从这大楼里跳窗自杀。你曾听到过这件事吗?〃我指着她后面的体育协会大楼。
她抬头摇了摇:〃没有。一九六七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是吗?那时这所大楼在修理,四面都是修房子的脚手架。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搬到这里住的。那些工人把这条狭弄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没有完工就走了。那我弄错了。〃我说着很快就离开了。她所说的是个活生生的事实,由此我可以肯定我女儿决非自杀的。
我可能在南京路上走错了方向,因为过了一会我发现自己走得比原来的地方离家更远了。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我'就上了车。经过一程颠簸不平的行驶,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家。当我打开大门,发现两辆自行车停在花园里,并听到楼下房间里,有人在说话。
阿姨在走廊里看到我就说楼下的房子已分配给姓朱的一家了。她还告诉我有关朱家的一些情况,但我没有去听她,因为我在思索着南京路上的新发现。
我女儿的死亡仍是件神秘的事,但我已有了比过去更明确的证据。她曾受到造反派的审讯,并死于他们之手是无可异议的了。假如她是被谋杀而非自杀,那不管怎样,我要找到凶手,看他是否已判刑。在中国杀人犯是要判死刑的。此后我脑子里不再看到曼萍在六月份初夏早晨的暗淡灯光下躺在人迹尚稀少的南京路上了。在梦幻中或一人独处的时候,总是看到她惨白的面容和失去生气的外貌。我也听到她的哭泣和怒吼。我向上帝宣誓,我一定要为曼萍报仇。
过了几天朱家搬来了。我正在考虑是否要下楼去招呼他们,说些客气话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可是朱太太先上来看我了,她的年龄和我相仿。染过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只假玳瑁梳子夹着,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我给她让座,阿姨送上来一杯茶和一只装香烟灰碟子。
〃我女儿艳和你女儿是同学,她们是好朋友。〃她很热情地说。
〃你女儿是否和你一起住在上海?艳是我的大女儿。她在北京解放军文工团工作。因为我丈夫是资产阶级分子,当红卫兵来抄家时,我们便被扫地出门,住在汽车间里。你能想象我们一家七日仅住一个汽车间?我们需要走两百公尺才能取水和上厕所。红卫兵要我扫马路,我的丈夫也不知被殴打批斗过多少次。我们只是个没有声望的小资产阶级,我们的钱并不多。只是我丈夫在解放初期曾开设过一个制造雪花膏的工场。〃她说话时显得很紧张,不停地吸着烟。
〃你女儿在部队工作,那你们应该得到照顾了。你们有否取得'光荣之家'称号〃我问她。有子女参军的家庭被称为〃光荣之家〃,共产党供给他们特别的配给品和一些特权。
〃红卫兵都把这些否定了,但现在又承认了。我们的成分又恢复了,并分配给我们这里的房子。我希望你们搬到这里来住会感觉很愉快。〃我很有礼貌地说。
她拉着我的手说,〃我老是讲我自己的事。你的遭遇比我们更坏。你被送进看守所,你漂亮的女儿又死了。我得知曼萍死后,就去信告诉我北京的女儿。我们大家是多么伤心!〃我不愿和她谈及曼萍的事,更不应为我的遭遇而向她诉苦,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
她笑着将香烟头在碟里揿灭,接着又点了一支,深深地抽了一口,然后吐出一阵浓烟说:〃我上来是和你商量有关电费的事。我总喜欢每件事情事前讲个清楚,你说呢?这样以后便不会有什么误会了。我的女婿是电工,他已发现这幢房子只有一只电表。你是否同意我们两家把电费平分,因为你住一层楼,我们也住一层。〃在我回答她之前,可能阿姨已在门外走廊里听到我们的谈话,这时她走进来说:〃阿哎!朱师母,我们得按照每户住着的人数来平均分担。你们有七个人,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将电费分为九份,你们付七份,我们付两份。不,虽然我们有七个人,但我们所占房间面积并不多。电费应该对分。〃朱太太对阿姨感到很恼火。
〃你们人多,当然你们灯也多,平均对分不合理。〃阿姨和她争论起来。
我出来作调解了。〃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其他邻居是怎样分派的。我要去看看鲁英,她是小组长,她也和好几户人同住。我们去问她好了。那也不妥当。除了你之外,每户人家分配到的居住面积都是一样的。你分配到的面积比人家的大。假如你的两间房子分配绐两户人家,那么这里也要住上六七个人。〃朱太太激动地说。
她将香烟揿灭在碟子里就站了起来。〃我让我丈夫来跟你谈谈。〃她离开房间自言自语地下楼了,也没有等我回答是否愿意见她的丈夫。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为电费而发愁。我搬到这里以来的几个月里,每月电费没有超过几元。
我听到有人从楼梯里上来了,一会儿,门就打开了。朱先生走了进来。他是个面部肌肉已松弛的浮华俗气的男人,可能他过去曾相当肥胖。当时阿姨立即跟了进来,站在我身边预备为我争辩。
〃我妻子告诉赞说,你不愿负担你的部分电费?〃朱先生开口就说。
因为他不懂礼貌,没有敲门便进了我的房间,因此我没有站起来和他招呼,仍坐在写字台旁边。
〃以后你要是来看我,请一定先要敲门。不能不敲门就进来。有自尊心的人必须保持文明的态度。告诉他。
他胀红了脸感觉到不自在。〃你是否要讨论一下有关处理电费的事?〃他问。
我严肃地说:〃不,我不愿再讨论有关电费的事了。下个月我就付一半电费。同时我还要装一只火表,这样以后就不必再有争论了。付多少电费是件小事情,你为何要斤斤计较。〃他自说自话坐了下来,脱口而出说:〃你不知道为何要斤斤计较?问题是为了钱!红卫兵没收了我的银行存款,我又没有工作。我和妻子每月每人只有十二元(按那时汇率约兰英镑)生活费。我的一个儿子又在待业,另一个儿子每月薪水仅四十元。我们还要照顾我们的孙子。他的父亲在东北。他们那里副食品缺乏,我们还要为他们寄食物邮包。〃我站起来向他表示这次会见已经结束了。我说:〃我很同情你的情况。既然你有困难,下个月我同意付一半电费。〃朱先生愁眉苦脸地咕哝着:〃我不是来向你求施舍的。〃就离开房间下楼了。
我看着朱先生弯身曲腰的后影离开了房间。对朱家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使我看到贫困竟会使人的风貌败坏到如此地步。
次日我向房管所申请购买一只电表,但房管所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每天去问询,但他们总是说我的申请目前尚不予考虑。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为我搬迁浴室的工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