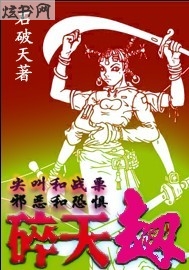上海生死劫-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缺口,我就得坚持斗到底。因此我毫不犹疑地将上次那段语录再抄了一遍,同样在自己的签名前加上〃一个无辜者〃。我的记性很好,所写的内容和上次基本相同。第三天我就把它交给了看守,之后,我立即又被召去受审。那审问员还是把我写的那份材料往地上一扔,还是散得个满天飞,又要我重写。
如是又重复了一次,那审问员对我说:〃你疯了吧?我们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和疯子铐在一起。我没有疯。假如你们认为我写的有什么不妥,你们可以指出,我愿意改正。你为何在印好的语录下面,再写上一段语录?又为什么要在签名前写上这样一个称呼?〃那审问员问。
〃我只是要使我写的东西能真实反应事实。〃我说,〃我要提醒你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我们要善于改正错误。我希望你们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改正对我案子的错误处理。至于在签名前加上这么一个称呼,我认为是很恰当的,因为我没有犯罪。假如你们一定要称我为'罪犯',那么,我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罪犯。你不老实交代罪行,还要费尽心思诡辩。〃那审问者说,但已经不再咆哮了。
〃我从没犯过任何罪行,你一定要这样说,那你必须用证据核实。当然我们要核实。但我们要给你杌会交代,唯有这样你才可得到从宽处理。我不是已经重复多次,我没有犯罪?我不是已经写了字据,证明一旦查出我真犯了罪,你们可以枪毙我?别耍无赖!你也不用焦急,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会枪毙你的。〃那青年工人对我叫嚣着。
〃回牢房去,重写。〃那审问员说。
那记录员又给我一卷纸,我跟着那看守回到囚室。
我打开那卷纸低头一看,发现第一页是张白纸,既没有印上语录,也没罪犯签名这一栏。我又写了一份情况报告。两天后交给值班的看守。
在那些没有和极左分子较量过的人看来,我与他们这种持久不息的抗争,或许会认为是无用又无谓的。但事实上这些人骨予里都是欺软怕硬的。假如我任他们随心凌辱我,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我在看守所的度日,将会更不呵设想。而且,我在审问室里所说的话,一字一语都录了音。我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盼着有一天,会有一个公正的人来调查我的问题。那所有我说过的,可能都会协助他给我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每天都在等着那审问员来提我去继续审问。但老不见人来提我。终于一天早晨,那个曾踢过我的军人看守走到我牢门口,把门敞开大声喝着:〃出来!〃待我俯身去取语录本时,那女看守跟着走进来,冷不防将我狠狠一推,我没思想准备,几乎给她推倒在地。
〃你去的地方不需要这个。〃她一把将语录从我手里夺去,往床上一扔。然后把我双手反剪向背后,那男看守进来抱一副手铐锁在我手腕上。那女看守又把我推了一下,我打了个踉跄,待我刚站稳,她又是一下。
〃快点,快点!〃她喝叫着。
我随着那些看守走出女牢,穿过大院子,来到大门进口处。那审问员和青工,还有另一个男人,都等在二道铁门口。车道上停着一辆白色小轿车,车上的引擎还在嗡嗡作响。
〃进去!坐中间。〃那审问员说。
我上了车在中间坐下,因为我的手给铐在背后,我只好挺着身子坐着。当下第一个感觉就是,汽车的座位非常软,我已有好久没坐沙发了。
审问员和青工分别坐在我两侧。还有一个人和司机,坐在前边。车子缓缓启动后,即加快车速驶出监狱大门。
他们要把我带往哪呢?是否为避免再与我交锋而把我送入精神病院?我肯定他们不会把我送去枪毙。因为死刑,往往就在监狱附近方圆之内悄然执行的。而且假如他们把我杀掉,便无法从我这里弄到认罪书了。可能他们存心让我活着受折磨,我看,送我去精神病院极有可能。但在那里我很难再继续抗争了,精神病患者的号叫声会令人意气消沉的。然而,我很快就发觉,车并没有往郊外的精神病院行驶。透过轻轻飘动的小窗帘,我看到汽车正穿过市中心闹市区,向西郊方向驶去。那里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这些熟悉的街道,唤起我对旧日生活的回忆。我们驶过一个马路拐角,我的家就已经近在咫尺了。那是第一医学院,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见识过文化革命那个批斗会的当天傍晚,就在这里遇见薇妮,从这扇大铁门里闪出来。这一切如今对我来说,已如隔世了。我不知薇妮现在怎么了?有无被送去五七干校?
车缓缓驶进我参加第一次批判大会的那所技校,我也是从那里,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七日,被送入第一看守所的。如今,已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旬了,二年多来,我一直戴着反革命那顶根本不存在的罪名的帽子。
几个男人,聚立在慵倦的初春的阳光之下,其中一人过来开了车门,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去,后面的人则猛将我的头揿下,因此,我目之所及,只能是前面那人向前移动的两条腿,一进门,他们便让我一人呆在里面,把门一锁。
那是间布满尘埃的空房间,里面只孤零零地搁着一张木条凳。窗上糊满了纸,根本看不到窗外。四堵墙面从地板到屋顶,铺天盖地妁贴满了大字报,在屋角还有一大堆。墙上那些大字报不是最近的,有些根本已撕破了,有些乱七八糟地一张张重叠着。待后来他们打开房门唤我出去时,随着门外吹进一阵大风,哗啦啦地又刮下了好几张大字报。
我坐在木条凳上,粗粗浏览一下那些大字报,我发现,他们把两年半来的旧大字报一一展览出来,只是为了对我展开一种心理攻势。签名的都为亚细亚的旧职员,有些是一个人写,有些几个人联名写,内容大都为揭发亚细亚,揭发我已故的丈夫和我自己。所列的〃罪行〃颇多,多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有些只是他们个人的臆断而已,我们的朋友和三个在我丈夫故后来沪接替他的英国经理,都被指控为与我有密切关联的〃外国间谍〃。好几张大字报里都点到斯谷特和奥斯汀的名字。那位我们公司聘用的白俄女秘书被揭为英国和苏联的双重间谍。我闭上眼睛,不愿再看见那些令人生厌的大字报。枯等了好一阵.我不知外面又是怎么回事,便倾耳听着,听得门外有脚步声,我就敲敲门。
〃你要于什么?〃个男人的声音问。
〃我能上厕所吗?〃一个女人来开了门,把我带往后面一个院子里,经过一溜宿舍似的平房,里面挨挨挤挤地排着一列双层床。后来我才知道,自一九六六年开始,那里就是隔离亚细亚旧职员的地方。
他们在那边办学习班,作永无止境的交代,一边还要劳动。但此刻,里面却是空无一人。远处隐约传来有人在做报告的声响。我想这功夫,里边的人大约都给驱去开大会了。
从厕所出来,我没再被带回那间满是大字报的小房间,而给带往一九六六年斗争亚细亚的会计主任和我自己的那个会场里。这时,后面的人猛力往下揿我的头,另外两个女人分别抓着我的双臂把我往前推搡着,令手腕上的手铐勒得我好痛好痛。这种暴戾的行为,是某些中国女性为着突出革命化的表现。
他们把我像只麻袋一样,半推半扔地弄进了会场,因为我仍被揿压着头,所以无法四下环顾一下周围环境。待我被令坐在地上时,她们坐在我后面,还是使劲地揿压着我的头。
在我坐下之前,从眼角里瞄到,地上已坐了满满的人。这个做法,是侮辱人权的。照中国的传统,只有奴隶,服刑的罪犯,或俘虏,才是坐在地上。会场上此起彼落的口号,也就是那早已听熟的一套。整个会场气氛,就意味着要把我打倒在地,踩个粉身碎骨。然后一阵脚步声,有人踱到会场前面,口号声渐渐停止了,一个青年后生开始主持会议。
〃就是她!〃他声色俱厉地叫着,我想这时,他一定手指着我被揿压着的头。〃我们今天把她带来了,把她的真面目置于光天化曰之下。我们要她明白,我们对她这张底牌是摸得一清二楚了。你们这些人,都参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所以,你们不同程度上都是有罪的人,你们也曾经为在二十世纪初就侵略剥削中国的帝国主义服务。亚细亚公司是个特务组织,是专为帝国主义收集情报。但是各人犯罪的深浅,是依据你们在公司的职位及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多少而有所不同。地位越高,罪行就越重。我们造反派是绝对公正的;假若你犯了百分之三十的罪,我们是不会判你百分之五十的。当然我们有量罪的标准,它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来决定的。
〃两年半以来,我们给你们集中办了学习班,改造思想,同时再参加劳动。你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了进步,提高了觉悟,不再抗拒改造,敢于站出来揭发敌人,那是值得表扬的。但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就出来一点。挤得重,就出来得多一点,我们不挤,它就什么也没有。好吧,要是你们仍负隅顽抗的话,自然我们就耍施加压力挤得更紧,直至全部挤光。
〃很快,我们就要允许你们中一些人回家。这对你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你们要记住,只有那些我认为可以批准的,才许可他们回家,其他的还要继续学习。什么时候你被准许回家,或者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办班劳动,那就完全取决于你自身。〃那人一味信口雌黄,扯着嗓门叫嚣着,看得出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只为着紧跟极左派而成为有些声望的造反派,这些家伙最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带来了梦想不到的个人飞黄腾达。他们把左派领导人如江青等奉为救世主,因为正是他们,将其从碌碌无能的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提拔出来。
扶他发言之中我明白了,坐在地上的一溜大都为公司过去的旧职员,现在正是鼓动他们起来揭发和批判我,以此来挽救他们自己。大家虽然都表示愿意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切早已事先安排好的。发言的一些人,都是经造反派物色并授意他们发言的内容的,发言稿会前都经造反派核准。即便在文革前,在中国,任何大会发言都得经过本单位组织核准。
那些我曾与之天天见面、共事有八年之久的老同事,一个个站起来开始了揭发批判,重复着在小房间的大字报里所写过的内容。他们神情沮丧,畏怯惶然,吞吞吐吐所揭示的,都是些荒谬透顶的捏造之事,所用的措词与他们本身是那么不相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很感羞愧和痛苦。那些蛮横的造反派,把这些人逼迫得堕落到如此地步,真令我万分痛心。但我还是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揭发,为此可以从中测探一下那些极左派人物的真正企图和目的。
地板很硬,我的头还是被后边的人死死地揿压着,令我的头颈好生酸疼。我挪动了一下身子,曲起一条腿,以将我的头,可以倚靠在膝盖上。这样,我就能看见我左边一个穿着蓝色上装的人的一角。因为我并不想把头抬得太高,宁可低垂着头。因此后面的人,渐渐地把揿压着我头的手,缓缓松开了。
那些亚细亚旧职员的发言,越发显得捕风捉影,任何一个对国外世界略有知晓的人,都会觉得他们的发言荒谬透顶,令人无法置信,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不过像是映出一场拙劣的、无头无尾的、无主题的间谍惊险片而已。
我听到那主持会议的青年,在唤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发言。
我身边坐着的那个穿蓝布上装的人应声站立起来,不知何故,那些极左分子把我安排坐在他边上。
陶方用颤抖不已的声音说:〃大家都知道,我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捕了,关在第二看守所。在那里,审问员和看守对我都很和气,他们帮助我通过学习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我慢慢开始认识了自己的罪行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衷心恳求争取宽大处理。正当这时,对我无比关心周到的造反派,又把我带回这里,让我的家属来探望我……〃显然他很激动,哆哆嗦嗦的,竟有一阵说不出声。
〃我的大儿子和媳妇,都是党员。我儿子受到政府培养,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我们全家都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情。每当我见到我妻子,儿子、女婿及我的小孙子时,我对自己罪行的悔恨,真是无法形容。〃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开始啜泣起来。
全场屏声敛气,寂然无声。淡漠的春日,从敞开的窗户投射而入,映照在我面前,我眼看着那抹光亮缓缓在地上移行着,不知这个无休无止的会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宣告结束。我只觉得又累又饿,但我暗暗警告自己绝不能松懈警惕。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陶受命的发言,并不是作为一种触动我的典型,因为我没有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