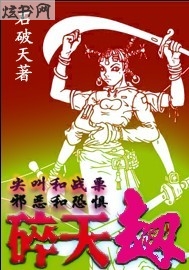上海生死劫-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监狱医院的候诊所,可谓为地狱一角。虽然没有人会被猛兽吞灭,在烈火中焚烤,或被丢入汹涌的大海之中,但它却是个惨不忍睹的痛苦的无声的地狱。那些裹着褴楼衣衫的憔悴不堪的病人,消瘦的脸上显出极度的痛苦,好像只是在延挨着等着死神的到来。不知是因为病魔的折磨,还是因为饥饿,或者两者都有,将他们摧残成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是医术超众的医生,也未必能恢复他们的健康。我听说过有关提篮桥监狱的惊人死亡率,现在亲眼目睹的这些病人,立即就会进入下一批的统计数目之中。
一些犯人伛偻着坐在木条凳上,边上还有许多病人,裹着棉被,就躺在搁在水泥地上的肮脏不堪的帆布架上。一个秃头老人,就躺在我面前,深陷的双目紧闭着,蜡一般的脸庞上,紧绷着一层近乎透明的皮,除了那张着的嘴巴还在痉挛地喘着气外,已是完完全全像个死人了。
室内的窗户都紧闭着,空气混浊得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我紧紧地闭着眼睛,以躲开那让人压抑难过的惨象,屏声息气地等着医生的传唤。
〃一八零六!〃一个穿着一身脏得近乎黑灰色大褂的护士,在候诊室门口叫道。
我跟着她走进就诊室,那女看守,已在那里与一位中年医生说着什么。房间颇大,正中生着一只火炉,一壶开水在咝咝作响。一张张小桌围炉而置,医生们就坐在各自座位上看病。这里根本不顾及中国的传统礼仪,毫无遗掩,男男女女的病人,就当众脱下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检查。医生和病人之间扯着喉咙大声讲着话,一片喧哗。当时我只以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不过只是对犯人而已。不料待我释放之后,才知道,在文革中,全上海的医院都是这样一个局面。
我十分紧张,思忖着,要是医生让我也要在毫无遮拦之中脱衣服,我该如何应付她呢?这时,她递给一支体温表,幸而没有其他要求了。量过体温后,她对那女看守说:她的体温很高,最好住院治疗几天。病房在五楼,怕她走不上去。还是用张担架把她抬上去吧!
〃还是我自己走上去吧!〃我恳求她。因为我实在不愿意躺在那腌瓒的担架上,那实在令人受不了。
那位医生满脸皱纹,两鬓已斑白了。她的目光详和又善良,似乎她很理解我的心思,知道我不愿碰那肮脏不堪的担架,因此她对看守说:〃你们可以乘职工专用的电梯,这样反比担架要快一点。她确实病得不轻,可能是肺炎。〃那女看守再押着我来到五楼病房。除了警告我不准与其他犯人患者议论各自案情外,还告诉我,我所需的脸盆和毛巾,以后会由其他送犯人来院的看守给我捎来。随后,她把我交代给一位衣襟前挂着个劳动改造牌牌的年轻女人。那边,还有一个值勤的解放军,在一边监视着我们。
窄小的病室里安着五张床。靠近门口的那两张已有病人了,我的那张床就靠着墙,中间隔着两张空床。那位正在服刑的女人,让我脱下衣服躺下。
我浑身躁热,四肢酸痛,现在能躺在一张真正的床上,多舒服呀!没有漂白过的床单虽然很粗劣,但却很干净。房里虽然还是冷,但被褥还是比较厚暖。我脱掉了棉袄棉裤,穿着羊毛衫裤躺下。那个年轻女人又抱来一床被子,压在我身上,我很快就入睡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昏迷不醒,有时恍惚能对四周环境有所辨认,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沉陷在昏昏沉沉的迷梦之中。待我终于苏醒过来后,发现我的手臂上插着输液管。这几天就是靠着输液来维持营养的。那位劳改女青年把体温计塞进我嘴里量体温。发现我已清醒了,便将我的输液管之类全拿走了。我虽然已苏醒过来,却还是觉得手足无力,依然想睡觉。
过了一会,她给我送来一碗热流质:〃把它喝了!〃她说。
我抬起僵硬的,像不属于我的手臂,居然还能把碗端稳,那碗流质全给喝下去了。它的味道很特别,后来才辨出,那是加进大量食糖的豆浆。因为我已好久没尝到糖的滋味,因此,不能即刻作出〃甜〃的反应。
现在感觉要好多了,头昏眼花也没有了,我觉得轻松多了。伸手摸摸自己的额头,烧已退了,额头略略有些汗蒙蒙的。那年轻女人手持一只小小的注射器,里面灌满了牛奶似的药水,要来绐我注射。她让我侧过身去,我很有点紧张,因为对看守所里那年轻军医的注射技能,我尚记忆犹新。不料这次,我却一点也未觉得疼痛,因为她的注射技巧十分娴熟,又快又好,简直是个专家。我肯定,她原先可能就是个职业护士。我很为她难受,她何以会来到这里劳动改造的呢?
晚上,她又送来一碗松软的米饭,一盆蔬菜,上面覆着一条油氽红烧鱼,还加着青葱和大蒜。鱼并不大,约六英寸左右长,但其味鲜美无比,全让我吞下肚了。我的盥洗用具已放在床边椅子上,地上还搁着一只扁马桶。我很想起身擦擦身子。
待那年轻女人把空碗收掉后,一个解放军就将病房的大铁门上了锁,然后走开了。这时,那另一张床上的女人,便踅过来了。
〃你昏迷了六天,他们以为你要死了。现在好点了吗?〃她消瘦得像根芦柴棒,两颊深陷,皮肤惨白干瘪,但一双眼睛却闪烁发光。她身上那件棉袄,已是补钉缀补钉了。看样子,她已有六十开外了,但那嗓音听上去,只像三十来岁。她讲得很轻,还不时往门口张望着。
我对她颔颔首微笑着。有她与我作伴,我感到很高兴,但我的体力,还令我无精神与她交谈。她挨着我床沿坐下。
〃你刚转到提篮桥?是什么时候判的刑?〃她问我。
记得女看守关照过我,不要与任何人谈及案情,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又笑了一下。
〃别怕,我不会去报告的。你知道,我们囚犯之间要互相保护才是。〃她对我说。停了一下,她又问:〃你得肺病了?这是肺病病房,因此我们的伙食较好。但明天我就要回牢房了,因为我已经不再吐血了。待我的病情再恶化吐血时,他们还会让我转这儿来休养,注射一些肺病特效针剂。他们给我们治病倒是不嫌其烦的。因为他们也不愿我们死掉。〃说着,她深深叹了口气。
〃真不幸,你得了肺病……〃我对她的病深表同情。
〃这样的地方,每个人迟早会患上这种病,那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互相交叉传染;想想看,二十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睡觉时,互相挨得紧紧的,怎能不传染?伙食又这么差,劳动量那么重!你要参加劳动?你干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她。
〃缝纫。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一周六天,我都在缝羊毛背心扣子,开纽扣洞。因为这些产品都要出口的,因此要求很高。我每月可以挣得几块钱,买点肥皂草纸。我丈夫没有能力再支付我的零用钱。我们有三个孩子。〃谈到自己的境况,她不禁悲从中来。只见她低垂着头,几乎要哭出来了。但她还是坐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她是希望有个人跟她谈谈心,对我来说,被隔离了这么久,有她在我身边作伴,也觉得很是安慰。
〃我原是一家工厂的会计,我丈夫是同厂的技术员。那工作蛮不错,但我自己不小心,把它弄丢了。〃她幽幽地说。
〃是在管理银钱出入时犯错误了?〃我问她。
〃不,我不做那样的事。我只是批评了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后来有人去报告了,他们就把我揪了出来。我不但不向支部书记道歉,还不服气,与他们抗争,又批评了他几句,我真太不懂事了!那支部书记发火了,把我的名字列入厂里的反革命名单里。我被判了十二年。你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吗?批评党支部书记并不是太严重的错误,十二年的徒刑太长了。这又有什么用呢。上级法院所做的,只是把案子再推到我们支部书记那里。公安局总是和支部书记站在一边的。你知道,古话说过:官官相护嘛。你在这里已很久了,待刑期满了,你们依旧可以全家团圆的。〃我试着安慰她。
〃我已快满刑了。希望再见到他们时,孩子依旧还认识我,丈夫也没有其他女人。在规定探望日子,他们来探监吗?〃我知道己判刑的囚犯送至提篮桥后,每月准许家属来探望一次的。正因为如此,许多长期搁在看守所的囚犯,宁可作假交代而判刑,至少他们可以见到自己的家属。
〃没有。我判刑之后,自己立即就要求他们与我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丈夫保住他自己的职务,保护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他们对待反革命家属是十分残忍的。我和丈夫感情很好,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当我提出要他即刻与我离婚,并不要他来探望我时,他哭得很伤心。他说我们就假离婚吧,其实他在等着我。〃我实在为她难过,但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她。她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之中,久久没有出声。然后,她转了话题:
〃你遇到那个女医师看病,那真是你的运气。她的医术很好。听说她毕业于美国一所世界闻名的医学院。这位医生十分和气,也体贴病人。我初进来时,她也是这里服刑的一个犯人。刑满后,她又回到这里来工作。听说她是自愿要求来的。在这里呆过的人,在外边是很难做人的。人们都不愿和刑满释放分子交往,单位领导也不敢分配他们合适的工作,更没有提升的希望,他们已成为一个有污点的人,总得受人歧视受人詈责。一旦成了反革命,便永远是个反革命。在监狱中受苦煎熬,出了监狱,也是无尽头的受苦煎熬,家属也陪着一起受罪,我在厂里冷眼见过这种情况,现在,我自己也置身其中了。有时,我真害怕离开这里再回到外边世界去。〃听说那女医生原也是提篮桥的犯人,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她那善良的外表后面,竟蕴藏着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不讨现在想起来,她的双目中除了温和与善解人意外,的确还深藏着一种别样的目光。对人生,她似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这令她表现得超然的睿智及宽容。
〃她是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由美国回来为人民服务的。她在那里本有个很好的职位,但她放弃了它回国了。我初见到她时,她讲话仍像外国人一样坦率。像她这样,当然会有麻烦的。〃她说。
一九五零年初,人民政府通过海外华侨中的代理人及同情者,秘密动员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结果这一号召广泛地激起了海外各地华侨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特别在美国。各行各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响应了号召。他们放弃了很为理想的职业及舒适的生活回到了中国。岂知事实上,他们并不受欢迎。有些领导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猜忌怀疑,对知识分子持有偏见。这样的政策,使回国的知识分子顿陷困境。由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让他们再回到美国。因此,他们唯有尽力适应中国的情况。有少数人去了香港,但大部分还是留在中国,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工作。许多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即使在反右中幸免于难的,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也被一网打尽。只有部分幸运者在周总理的力所能及的保护下才免于遭难。这是极左分子为政治而牺牲个体的人的实例。
我们默默地坐着,各人想着自己的心思。还有一张床上的病人,开始呻吟和咳嗽了。远远地,又传来开门的声响。那位坐在我床沿边的犯人有些害怕了,她转身对我道了晚安,就溜回自己床上了。
我睁大双眼躺着,思念着我的女儿。现在,她在哪里呢?她是否能安然地应付这错综复杂的大革命局面呢?我祈求上帝引导她,保护她。
次日早晨,我的脚一触及地面,依然感到虚弱无力,走动时只觉得气喘吁吁。此后我每天坚持走几步,后来可以在房里随便走动了。营养和药物令我的健康逐渐得以恢复。
那时,病房里只有我和那会计俩,另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一直不能起身。一次我走到她床边,但她眼皮也没睁一下,好像毫无觉察。在她枕边,放着半罐痰血。她的脸色,就像一张揉皱了的牛皮纸。她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除了咳嗽。午饭时,那个来劳动改造的女青年,用汤匙喂她。
我从未对那来劳改的女青年打听过她的问题,她也不敢冒险与我交谈。但我们互相以微笑来表示友善。虽然她每次给我送来营养菜,一但我发现她自己吃的,仍是一般囚饭或白水煮山芋。她衣衫褴褛,而且看上去衣不胜寒。见她的嘴唇冻得发紫,双肩耸缩着,我想把自己的一件毛衣送给她。那天事先我就把毛衣脱下,等她进来时就塞给她。因为有解放军在监视着,我也不准备与她说什么。然而她却怵然惊起,紧张地看看病房那端那个忧伤不已的会计犯人一眼,慌张地把毛衣退还给我。
一年后,我又因重病再进来时,她已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