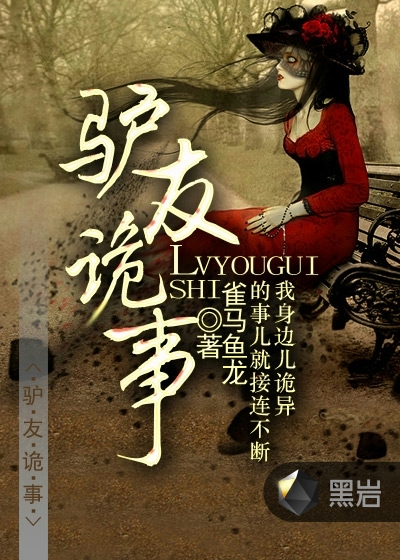唐人街故事-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工作上的“自私”,使得林怀耀忽视了家庭,忽视了对儿子的照顾。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他的儿子。但是现在他并不是想见儿子的时候就可以见到。“有一句广东谚语叫:如果什么都预先知道,那就不会有乞丐了。有时候碰到事情,你要做出的选择和决定,其后果自己是预料不到的。我们只能去面对。要是能回头,什么事都可以改变。我可能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但事实是你改变不了。也许事情能够补救,但能够补救并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那段时间,家里原有的生活模式突然改变。儿子年龄还小,并不能明白这种改变。他会觉得我对他照顾不周,对他的关注不够感到不开心。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压力。林怀耀说,刚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和儿子待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少,可说话不多,未必开心。后来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忙,要腾出时间陪儿子也越来越困难。但几年过去了,儿子成熟了许多,也渐渐地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因为彼此都懂得了珍惜。他们现在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也更像是一对父子。有时父子俩在一起还会玩一些比赛爬电线杆子之类的小游戏。林怀耀很享受跟儿子在一起的时光。
今年是多佛惨案4周年,林怀耀正在筹办一个纪念性质的座谈会,同时也呼吁政府修改移民条例。“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英国的移民政策使得多佛港的死难者没有别的途径,被逼走向这些蛇头。莫肯姆湾的情况也都是因为移民政策不让他们工作,就逼得他们去做一些危险的工作。我相信除非移民政策改变,否则这样的惨剧还会继续发生。这种惨剧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机率是80%以上。我希望通过社区的讨论和探讨可以反映社区的意见,使当局正视这些问题。”跟唐人街上浓烈的商业氛围比起来,林怀耀正在做的事情显得有些不合事宜。主动过来咨询的人寥寥无几。他说他们开这个座谈会,就是希望多一些人来提出意见。冷漠和拒绝的气氛包围着林怀耀和他的伙伴们,但是这似乎丝毫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热情。他说这已经就很好了。至少没有人走过来说,这些无证的工人应该送回中国。
来英国三十年,林怀耀从维护华人权利的活动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为做这样的工作使我长了见识。因为我面对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使我要寻求答案。这个寻求答案的过程,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是从其他人的不幸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我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如果我不处理的话我心里不好过。我有能力的,我就处理好。我去尝试。如果我尝试以后处理得了,我心里会很开心。我处理不了的时候会很沉重。我希望我不需要在‘民权'工作。因为只要‘民权'继续存在,就表示英国社会继续存在歧视华人的现象,英国的华人继续地受到袭击、受到歧视、受到滋扰。希望我不需要做这些工作。但是事实是另一回事。事实是只要英国的华人会受到歧视、袭击、滋扰的时候,这些工作就需要有人去做。我希望更多人来参与这个行动。”
附:2000年6月19日﹐英国多佛尔港的海关人员在一辆货柜车的集装箱内发现60名中国非法入境者。在前往多佛尔港的途中﹐集装箱的通风口被关闭﹐导致58人被闷死﹐只有两人幸运生还。
2004年2月,20多名中国移民在英格兰西北部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海浪卷走葬身大海。拾贝者大多没有合法身份。每人每天最多可获得30英镑的报酬,而“他们的头”每周则能获利600英镑。
2001年3月,英国爆发了20年来最严重的口蹄疫,《泰晤士》报3月28日报道引述一份尚未发表的政府报告;指最先发现口蹄疫的农场;是因为农场主从一家非法进口东亚肉类的华人餐馆收购泔水喂猪所致。华人餐馆顿时成了口蹄疫爆发罪魁源头的替罪羊。4月8日,全英中餐馆还共同停业两小时,以抗议上述无理指责。此外,伦敦华人还为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共有160个华人组织参加,游行人数至少有1500人。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1)
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岁月。一批共和国的同龄人,奔赴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命运之手的推动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越境到缅甸参加游击队。刘义是一位至今仍然生活在金三角的老知青,回首过往的峥嵘岁月,流浪生涯,他重拾热带丛林里的记忆碎片,向我们讲述他那一段漂泊的人生。
刘义,原名候景贤,他现在生活的地方是泰国清迈府一个名叫热水塘的村庄,这里是国民党93师残部在泰北的一个难民村。村里住着的都是当年部队的眷属,大概有一千多户人家。这里的人都说汉语,学中文,让人觉得自己并没有远离中国。刘义是这里唯一一所中文学校的副校长。由于白天学生要学泰文,所以中文课一般都安排在晚上。学校里的这些孩子虽然懂中文,但是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方块字的符号,然而中国对于刘义来说却是不能抹去的胎记。
动荡的岁月 动荡的心
1949年刘义出生在云南玉溪的易门。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对童年的记忆却是残破不全。父亲对他来说印象模糊,因为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投入监狱时,他只有5岁。15岁时,在亲戚家寄宿不久后,他就意外地接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我走进龙泉镇的时候,发现好多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门口烧了一堆草。这是我们本地的风俗,人死了家里那些草就拿来烧在门口。那个时候我两个妹妹还很小。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给我母亲垒坟。小的妹妹就说,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成熟了,长大了,有种责任感了。那个时候我下决心,无论如何要给这两个妹妹读书。”
没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时代宣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于是,满怀着一腔热血,刘义积极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通过行动洗刷掉自己家庭出身的污点。然而一张朋友给的100斤大米的粮单,却又将他推入了深渊。
“我的罪名是盗用国家备战粮食。那天晚上在粮食局,一进去以后就拿绳子把我绑起来了,绑起来就叫我交待偷了多少粮食。我已按实际情况说了,但是他们不信。不信以后就把我吊在那个大梁上。当时吊上去的时候,我不像一些人吊上去就鬼喊大叫,反而是若无其事,闭着眼睛养精神。这更把那些造反派激怒了,放下来以后就打。打的时候,有个女的就掐我的脸和嘴,半张脸全都被她掐破了。整个一晚上他们对我就是打了又吊上去,吊上去又放下来打。本来是一百斤的粮票折,最后搞成了三千多斤,就说我偷盗了粮食局的大米三千多斤。这个还不是我主要的罪名,主要的罪名就是因为在晚上批斗我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以前朋友送我的一把少数民族用的刀。他们就问我这把匕首是要杀哪些革命群众,杀哪些贫下中农。我那个时候打晕了,心也打横掉了,我说全部杀。其中有个人就问我,伟大领袖你杀不杀,我说杀,就是为这句话,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当时很恨,恨不得放把火,把整个龙泉镇烧为一片平地。我曾经有过这种打算。后来我一想啊,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受累,所以我才没有放这把火。”
1968年,毛主席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时间全国城乡都沸腾了。刘义这个没有立案定罪的学生也开了证明,去到位于中缅边界的盈江县插队。当时社里有14个同学,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当初大家比较天真,总认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多就是下乡几个月就回来了,哪个想到下去以后就像石沉大海。我的盈江县知青潘金生潘连长,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你们来到盈江就要生根扎根在盈江,死将来也要死在盈江。那个时候大家听了很寒心,觉得大概这辈子回不去了。”在农村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大家的思想都开始动摇了,1972年知青开始返城调动,调走的欢天喜地,调不走的唉声叹气,那个时候绝望的情绪像流感一样弥漫在周围。晚上男生轮流喝着口缸里的甘蔗酒,喝醉的号啕大哭,感叹命运的不公平。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2)
峥嵘岁月 游击生涯
后来有传闻说已经有许多知青越界到缅甸参加缅共闹革命,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对返城调动彻底失望的刘义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创造一个转折点。“在一次外出买牛的时候,和我相处最好的方宇仁送我到了51号界碑。当时我走到界碑的时候,我就停一下,转过头来看一看,再看方宇仁,他正在把眼镜拿下来擦眼泪,我看了一眼扭头就下了界碑。下了界碑呢,走下去是个竹林,竹林背后就有几间茅舍,茅舍上空飘了一面红旗,上面有个五星,那个时候心情很激动,就像以前那些革命青年奔赴延安,见到延安的宝塔一样。那个时候我下决心在缅共好好的干,我想我一定就是要活出个人样来,给那些人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人。”
在缅北的丛林里,刘义和许多四面八方赶来的知青不期而遇,在持续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数以千计的中国知青前仆后继,像飞蛾一样扑向金三角的游击战场。
第一次穿上军装时,自豪的刘义恨不得马上回到中国,让家乡的人看看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他所在的特务营大多都是知青,个个热情似火,写决心书,请战书,在热带丛林中辗转征战,憧憬着有一天能打到仰光去,解放全缅甸。然而一场南下战役的失败,改变了整个形势,根据地不断缩小,兵源也渐渐减少。更可怕的是游击队内部,也开始进行残酷的阶级清洗,知青成了地位最低的五等兵。“我们的生或死变得无足轻重,我亲手埋过一个知青李玉昆。那次他出去侦查,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些农民种着的洋瓜,他就准备摘几个洋瓜回来做菜吃,结果踩着独立军埋的地雷,当场就把他的右脚炸断了。把他抬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那天晚上他就叫啊,‘哎呀,哎呀,你给我一枪吧。’因为他和我稍微好一点,就对我说你一定要补我一枪啊。我们是蒙着耳朵睡啊。他受的伤没人能管得了。当时那些卫生员也处理不了,最多就是拿点酒精,拿点纱布,包扎一下。一直到天亮的时候他就死掉了。死掉了就把他抬出去,抬到一个稍微平整点的地方,我还给他打了个相纸,打了个相纸后就挖坑,拿那个大衣布给他包起来,埋的时候唱唱国际歌,就那么草草地埋掉了。”
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刘义对自己的处境时时感到茫然。“当夜幕降临时,我坐在山坡上,远处的景颇族战士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笛声回荡在山谷久久不散。那一刻我忽然恍惚起来,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呢,我们的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明天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而谁又会来埋葬我呢? ”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3)
死里逃生 马帮游走
冥冥之中总有一双手操纵着每个人的命运,它们分别叫做偶然和必然。许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义悄悄离开了部队,然而逃兵的身份必然会败露。所幸的是被缅甸政府军抓到后,他并没有被枪毙,而是被关在了腊戌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了几个中国人,日后他们一起逃亡,成了真正的生死之交。
陈厚本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现在也是一新学校的副校长。“刘义和我现在既是同事,又是有过生死之交的同乡。二十多年前我们一起被关在缅甸监狱,后来又一起在押送回中国大陆时跳南坎江,所以我们又是难友又是同乡,有几层的关系。我跟刘副校长稍有点不同,我当时出来是戴着两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当年是北京俄语学院毕业的, 1958年,也就是我毕业的那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开除团籍,当时我是团支书。 1979年,邓小平出山那年,补发了我这个改正决定,错判。还补发了个毕业证。当时被打成右派时,就要带罪工作。我就又被分回云南一个叫云龙的地方,最边疆的云龙一中教书。哎哟,工作真是困难。你教得好点,学生对你反应好,他们就说你是拉拢学生,散布资产阶级思想;你要教得不好,那是破坏生产,就更不得了。哎哟,真是左右为难。”
当时在腊戌监狱的陈厚本属于非法入境的政治嫌疑犯,在大陆已经妻离子散。1974年的夏天,刘义,陈厚本和与他们关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