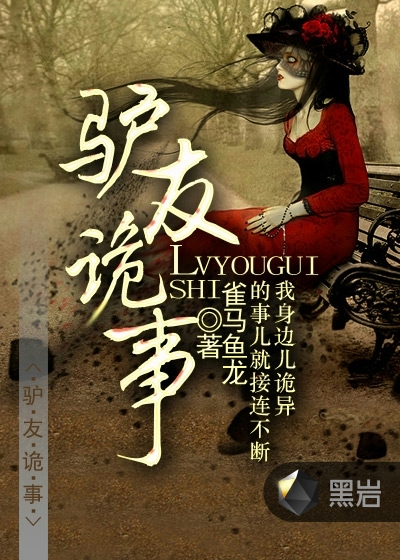唐人街故事-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里丹青】整理
第一部分光荣与梦想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刘长乐
由凤凰卫视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唐人街》,因其涉足地域之广、拜访人群之巨、创作立意之高,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遍访世界各地透视全球华人状况的史诗性电视作品。
摄制组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近40个国家,访问了从普通移民到华商侨领,从小留学生到管理高层的各界各类华人华侨,对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况、心路历程、周边环境和文化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片中一段段或感人至深或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凝结成一部恢弘的海外华人创业史、奋斗史、功德史和发展史。
许多观众已注意到,拍摄《唐人街》的这群年轻电视人,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有着不同于他人的选材角度和拍摄风格。但他们的镜头语言力求客观真实,他们的采访也充满了人文关怀。这群大多非科班出身的年轻电视人,在凤凰提供的广阔平台上发挥了他们的潜能,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并由此得到了锤炼,走向成熟。
《唐人街》是凤凰卫视继“千禧之旅”、“欧洲之旅”、“非洲之旅”之后的又一次大型电视行动,如果说前三次电视行动是对异彩纷呈的异域文明的解读,那么《唐人街》解读的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是矢志成为世界顶尖华语传媒的凤凰卫视的一贯宗旨和光荣梦想,《唐人街》的摄制工作便是努力实现这一宗旨和梦想的一次成功实践。有专家预言,21世纪是龙的世纪。《唐人街》真实地记录了龙行天下的艰辛和豪迈,也揭示了中华文化和异域文化从水火不容到最终水乳交融、共同组成璀璨瑰丽的世界文明的必然规律。
最近,《唐人街》获得中国纪录片学术奖特别奖,观众和专家的肯定和褒扬,相信是对凤凰人最大的鼓舞。目前,《唐人街》已完成了50集的拍摄和播出,行百里者半九十,摄制组仍在全球各地紧张地拍摄,我向他们道一声平安,也希望通过他们向全球华人道一声平安。
第一部分家中走天下,枕边看异乡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 刘泽彭
那天,和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聊天,听着他“向华人报道世界的信息,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的滔滔宏论,忽然想到,也许,他和他的凤凰卫视就是海外华人故事最合适的讲述者。
后来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几个月后,我就泡一壶茶,和众多凤凰卫视的收视者一起,跟着镜头,走进一条又一条的《唐人街》,家中走天下,枕边看异乡了。
《唐人街》既不粉饰海外华人的幸运,也不夸大他们的窘困,客观探求,平静沉思,关注平凡,领着观众去阅览一个个命运的流程和生活的切片,看他们的欢喜,听他们的歌哭。
他们个人的际遇和命运有时候就是一个民族的际遇和命运。海外华侨华人乐于看到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更乐于看到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因为,中国的发展既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之福,也是几千万华侨华人的福祗所系。
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是中华文明的神经末梢,他们为生存和发展告别祖籍国,用艰辛和勤勉经营自己的生活和生意,用和平与奉献的方式获得住在国的居留权,用他们的努力和成功为所在国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用他们的人生尝试着在经济融合的层面之上,人类不同民族之间消除歧见、和谐共进的空间与可能。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思索。
《唐人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宽广公允的叙述平台。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消弭了事实与镜像间的界限,我们可以在弹指之间触摸到遥远世界的人与事,而对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探访与问候,拉近了全球华人的距离,而这,正是凤凰卫视全球化视野和大中华概念的传播诉求之初衷所在。
我们要感谢凤凰卫视,感谢《唐人街》摄制组的辛劳,正是由于他们使得我们与全球华侨华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也把全球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
第一部分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故事(1)
俄罗斯,这个浩瀚的国度在上个世纪的74年间曾经叫做苏联。苏联的存在改变了20世纪人类的历史,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命运。如今这一片大地已历经风雨,改弦易帜,但时间的印记是无法抹去的。在她的首都莫斯科,我们结识了几位曾经在前苏联留学,后来回国工作,最终又定居莫斯科的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洋溢着对祖国、对莫斯科、对自己母校的无限热爱。
新中国成立之初,莫斯科曾经是点燃无数中国人心中激情的伟大的城市。1953年,一批风华正茂的优秀中国青年肩负着祖国的使命来到苏联,进入刚刚落成的莫斯科大学学习。邹厚工、韩存礼和陈先就是其中的三位。
邹厚工迄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留苏学生的选拔过程:我是1952年在沈阳参加全国第一次统考的,考后把题目拿回来对了一下,基本上没有错误的地方。如果要说有什么地方扣分,那就是作文了,个别的字句、标点符号等扣分,其他的我都是分数很高的。这样我就考上了。当时我那个省选了18个人到北京俄文专业学校的留苏预备部,用一年的时间学俄语、经受政治审查。选拔留学生肯定是政治标准第一,当然你也要学习好,家庭比较清白,各方面都要好。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新中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过程中,急需大批高级专业人才。当时国家提出了全面向苏联学习,培养一批“红色专家”的口号,对精挑细选出来的留苏学生寄予厚望。尽管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但在留苏学生出国前,国家给每个人发了两箱子衣服,其中有毛料的西服、中山装,还有领带、袜子等一应俱全。运载首批留苏学生的列车从北京前门老火车站出发时,教育部长亲自送行,场面非常热烈,大家的心情都格外激动。
邹厚工和陈先、陈滋康夫妇在莫斯科大学期间都是地质系的学生。他们对50年前的学校状况和学习仍旧记忆犹新:1953年莫斯科大学第一批入学的就是我们,当时学校漂亮极了,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全都是新的,能够来到这么一个高等学府学习,大家特别高兴。我们到宿舍里一看,感到真是上了天堂了,一人一个房间,两个同学用一个洗澡间,还有一部电话,走廊里是红色的地毯一直铺到头。当时在整个苏联,包括其他国家,大学生的这种住宿条件是唯一的,哪里也没有。就是50年后的现在,这种条件也不多。那时在地质系的大楼中,宽敞的大教室可以容纳几百人上课。大教室两边的墙上挂着《苏联地质构造图》、《苏联矿产图》等大型教学地图。教师拿着教鞭往图上任意一处一指,学生就应该能答出来所指地方的地层构造、矿产情况等。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有的中国留学生俄语不过关,听不懂课,急得把书都撕了。因为听说祖国急需地质勘探人才,而培养我们这样一个大学生一年就要花费25个农民的劳动,所以我们的负担特别重,整天就是啃书本。第一个学期比较困难,但学校共青团组织选派了优秀的俄罗斯同学来帮助我们,这样我们才慢慢好一点。
从某种角度上讲,地质专业是一个很浪漫的专业。中国留学生和俄罗斯学生在野外是非常开心的。上二年级时,地质系的同学们一起到黑海边玩,俄罗斯的女同学都穿着三点式泳装,而中国同学还羞羞答答地穿着长袖衣服,大多数也不会游泳。邹厚工的语言基础比较好,而且天性活泼,在比较保守的中国学生中显得与众不同,俄罗斯同学把他称为“最俄国式的中国人”。也许是外向开朗的性格使然,他在莫斯科大学结识了他的第一位妻子——同校的漂亮姑娘柳芭。
韩存礼刚到莫斯科时在另外一所大学的经济系就读,1957年为适应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需要转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他的回忆里充满自豪与激情:“当时中国留学生是非常排场的。那时两国的货币比价是一块人民币兑换两块卢布(1955年时的旧卢布),我们当时一个月发500卢布,相当于250块人民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连部长也挣不到250块钱。这仅仅是助学金,其他的费用咱就不知道了。学费、住宿咱就不管了,反正都是两个国家的事了。所以那时候不想别的,就考虑如何学习就行了。我们几个就属于比较啃书的人,我现在的口语也不大好,主要是因为老是闷在屋子里念书。后来,我们的俄文老师给我们买了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票,说你们不能这么待在屋子里学习,列宁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就这样把我们都轰到大剧院看戏去了。所以在俄罗斯人中间,想起我们这帮留学生都特别留恋。你看莫斯科街上的老头老太太,一谈到过去5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都非常佩服。他们说中国人有铁的纪律,不打架斗殴,不抽烟喝酒,就是一心一意地学习,星期天图书馆阅览室的人都是中国人。给他们的印象是中国学生特别勤奋。”
第一部分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故事(2)
那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所有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永远留在了莫斯科。韩存礼说:“当时中国上万上亿的人,有多少人能够来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呢?我出国之前,班里的同学觉得我要到莫斯科去了,到红场去了,能看到克里姆林宫了,大家都争着跟我照相,觉得我能把他们的心意也带到莫斯科来。可以这样讲,5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的那几年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也正逢一生中的大好年华。”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访问苏联期间来到了莫斯科大学,向中国留学生们发表了那篇非常著名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一番话使在场的所有中国留学生热血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
1958年,第一批留学生完成了在莫斯科大学的学业,回到了中国。此后,中苏关系暗流涌动,直至冰封阻隔了将近30年。邹厚工、韩存礼和陈先夫妇的命运由此变得曲折不平,难以捉摸。
1958年,当邹厚工准备回国的时候,他和妻子柳芭已经有了一个四个月大的女儿传苏。当时柳芭还在念四年级,她推着婴儿车到站台上同自己的中国丈夫告别。1959年柳芭毕业后来到北京与邹厚工团聚。当时邹厚工在航空物探部门工作,柳芭到北京广播学院担任俄语教师。不久,他们的第二个女儿传华也出世了,姐妹俩的名字寓意着这对异国夫妇对中苏关系的美好愿望。这个四口之家在北京度过了一段平安快乐的日子。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个共产党的关系开始变化,而后逐步影响到国家关系。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两国关系加速恶化,最后走向公开的破裂。在两国关系的阴霾笼罩下,1965年柳芭决定要带一个孩子回苏联,这个原本美满的家庭不得不面临着骨肉的分离。邹厚工觉得小女儿传华的性情不如姐姐那么开朗,万一受到“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好影响,忘了国家忘了本,就白生这个孩子了。于是就毅然让传华留下,让柳芭带大女儿传苏回国。分手前,全家到北京的丽影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张全家福。
现在供职莫斯科广播电台,担任中文播音员工作的邹传华对当年亲生父母分别的那一幕仍然刻骨铭心:“全家分开时我和父亲去南京,我们先上火车,母亲来送行,我就记得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哭,哭得非常伤心。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因为旁边的人都围着,他们可能觉得不理解吧,反正哭得非常伤心。”邹厚工当时想,最多三年,中苏关系就会和好,全家就可以重新团聚。毕竟都是马克思的弟子,都是共产党,怎么会长期为了一点理论上的事情闹得那么厉害?然而,事与愿违,这个家庭从此天各一方,邹厚工与柳芭的人生轨迹也出现了重大的曲折。
中苏交恶后,邹厚工因为曾经留学苏联和娶了一个苏联姑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在南京看守所被隔离审查了7年多。最初,小女儿传华自己在家里觉得很自由,因为没有人管她了。但时间一长,家里见不到亲人,而且听到周围的人议论她爸爸妈妈是坏人,是“苏修特务”,小传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无名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