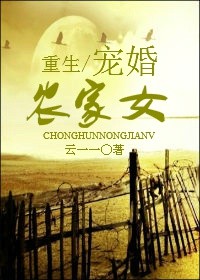中国式结婚-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还笑。”她也难为情地笑了。“不跟你还跟谁?”
“谁知道你跟谁啊。”
李燕琪瞪了他一眼,不说话了。
“生气了?”刘明宇试探着问,“肯定是生气了。”
“没有。”李燕琪嘟起了嘴,“为什么不尊重我的意愿?”
“没有不尊重你。”刘明宇安慰她,“跟你说着玩的。”
“走啊。”刘明宇走了几步,发现李燕琪没跟上来,站在原地不动,“怎么不走了?”
“我发现你这人特没情趣。”
晚餐选在大理极负胜名的“洋人街”吃。这条街有着很浓的西方情调,餐厅除了西餐厅外,还有一些韩国餐厅。每家餐厅都以英文和中文标示,门前摆放着一些原木桌椅,有的还铺盖着淡雅的格子桌布。每张桌子上还都放着一小盆鲜花,有雏菊,剑兰,康乃馨等。餐厅的装修也极有异国情调,音响还都不错。“天啊。我真喜欢这里。”刘明宇叫道。点了比萨和意粉。店里放的音乐象是西藏的音乐,空灵而低沉的乐声环绕在整个餐厅。窗上还挂着一些看来是精心挑选过的西藏的图片和饰品。
但是,李燕琪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从饭店里出来,李燕琪站在一边忧心忡忡地看刘明宇在街边挑选当地的几件工艺品。古寺晚祷的钟声响了,一下接一下,沉闷悠远,大理古城上空梵音萦回飘荡。
看着刘明宇兴高采烈的样子,李燕琪吞吞吐吐地问他:“刘明宇,你……会不会有一天离开云南?”
“是。”刘明宇立即站住,点了点头。
“那我们怎么办?”
刘明宇卡住了。是啊,该怎么办呢?刘明宇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很久了,一直不敢面对。他一直觉得,他像一个浪迹天涯的旅人,冒然闯进这块神奇的红土地,闯进这不染凡尘的仙境,目的就是为了与她邂逅,然后再伤害她。刘明宇说不清楚是不是爱她,也许当时并不爱她,只是寂寞而已。多少天来,他总是陷入矛盾中无法自拔,无法决定应该去爱爱他的人,还是去爱他爱的人。直到临近分别,他也没有弄清这个问题。数年以后的一个春风朗朗的上午,他再次遇见将要出嫁的李燕琪的时,他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十年之后,当刘明宇看到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及其续集《2046》时,他突然发现,电影居然与他的某些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王家卫说,《2046》是一列开往虚幻回忆的火车,每个人都想要去乘坐2046,寻找自己曾经遗失的记忆,残缺的梦想,丢失了的爱人,可是过去的已经早就过去,美好回忆每一次重温都是残酷。数年之后,当他在漫长的、如梦般的、倏然飘逝的时光里回忆从前,在如落花般的似水流年中感叹时,他吃惊地发现,原来不经意间他已经搭乘了这趟列车。
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一九九二年,云南,刘明宇无意间坐上2046这趟列车,为的是到达未来,但寻找的却是过去的回忆,列车前进的方向与其张望的方向始终是相反的,从而构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悖力。
刘明宇不敢回忆,他没有勇气开启记忆的大门,那些痛苦的记忆在脑海里堆积如山,只要稍稍开启一点缝隙,便争先恐后,鼓涌而至——一九九二年秋天的云南让他终生愧疚无比。
第七章 李燕琪
同样的时间与空间复制另一份记忆,这份记忆是李燕琪的。
此刻,她正站在他曾经住过的房间,心里默默地念他的名字:刘明宇。
她转回头,望着空荡荡的房间,不敢相信,时光竟如此真实地流淌过去了,而她却如同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后什么也没。
昔日她如此熟悉的这个房间已经不认识了她,好像来了一个新主人。尽管她做出一副心境坦然的老朋友的模样,它依然显得有些冷漠和一声不响。
她知道,自从他离开这个地方之后,这里的时间就停滞了。
她抬头望了望窗外,阳光明媚。尽管已是冬天的,云南的季节仍然是翠绿的,只有梧桐树才会心事重重又无可奈何地摇落一树枯叶——的确已经是冬天了。近处,江水一改夏和秋的桀骜不驯,温柔得尤如一个豪门闺秀,静静地流淌着,倒映着青的山、绿的树、白的云、蓝的天,色彩明暗交错,绿白互衬;远处,是弯曲的公路,冷漠的群山,以及无边无际的蓝天白云。
群山之上暗淡的杉树、挺拔的云南松以及姹紫嫣红的丁香,都在小风里挥舞着嫩绿的翅膀,给白色的云朵和含情脉脉的薄雾镶上了—簇簇花团,暖融融的连成一片。太阳疲倦地枕在树叶上安歇地睡着。
远处飘出来—缕若有若无的乐声,是一个女人低低地在吟唱,像唱歌,又像在叹息:过去的永远过去了,未来,永远是新鲜的。以前,他也会唱这首歌。
她关上了窗子,一点也不想再听到这首歌。
多少天过去后,她仍然记得他离开云南的那一刻。她和他在这间屋子里坐了一夜,第二天在这间屋子里分手。她望着绝尘而去的他,心中搜寻着那些日子里他所有的音容笑貌,觉得满满一怀抱的幸福被猛然抽去。“再见,刘明宇。”她轻轻的说,然后她蹲在地上哭了。
她钻进被窝里,蜷缩着膝盖,双臂抱在胸前,侧身而卧。她仿佛躺在海边金黄色的沙滩里,暖暖的阳光穿透沙粒涂抹在她的皮肤上,又从她的皮肤渗透到她的血管中,金色的光线如同大麻,在她的血管里迅速弥散。她立刻觉得身体酥软起来,昏昏欲睡。
当她的手指在那圆润的胸乳上摩挲的时候,她的手指在意识中已经变成了刘明宇的手指。刘明宇的手指抚在她的肌肤上,在那两只天鹅绒圆球上触摸……洁白的羽毛在飘舞旋转……玫瑰花瓣芬芳怡人……艳红的樱桃饱满地胀裂……秋天浓郁温馨的枫叶缠绕在嘴唇和脖颈上……她的呼吸快起来,血管里的血液被点燃了。
接着,那手如同一列火车,呼啸着,沿着某种既定的轨道,渐渐远离……
在她的记忆长河里,她能清晰地看见他。她把他在脑海中所有的影像慢慢地过了一遍,细细地回味一切,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就像口述很久以前大理国的传说,代代相传直至永久。她永远也忘不掉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她正坐在服务台前,喝着茶,漫不经心地看着一辆县公路上行驶的卡车下面卷扬起来和尘土。扬尘中,他进来了,提着一个包,背着一把吉它,一副疲惫的样子。他身子瘦、高、硬,行动就像草一样自如而有风度,泛黄的头发在耳后长出不少,几乎是乱蓬蓬的,好像他刚从大理的下关旅行回来,还没有及时拢整齐。
按传统标准说,他不算帅,也不难看。她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一种饱经风霜的苍老神态。他狭长脸,高颧骨,头发从前额垂下,衬托出不大的眼睛,有点像一个浪漫骑士。他当时对她微笑着说她在晨曦中脸色真好,真滋润。
“你怎么老是笑?你叫什么?”他点了一根烟,东张西望,问她。
她并不觉得这很唐突,于是告诉他名字:“李燕琪”。
“好听的名字。”他笑了笑,他的声音始终和他的眼睛一样,总能飘得很远,有些心不在焉,但总是吸引人。
“你呢?”她径直问,她觉得,在她和他之间,存在着一种属于缘份的东西,这东西命中注定无法躲避。
“刘明宇。”他看了看她,黑白分明的眼睛如寒水沥沥。
她镇静地盯着他,他叹了口气。
“没有人为讲自己的名字而叹气的,”她笑了,“除非是逃犯,或者……”
“或者什么?”他追问了一句。
“傻瓜。”她说。
他努力地笑了笑,似乎没有完全成功。那个时候,他总是那样,疲倦不堪,满脸的茫然和无助。她的心底,有那么一丝东西微微抽动了一下,像是某种冲动又像是满腹爱恋和心酸。她真想走过去,紧紧地拥抱他一下。但是,她没有。她知道,今生今世再也忘不了这个人了,有种朦朦胧胧的东西,悄悄泛起。李燕琪从此便感到,她和他之间,或许会发生点什么不一般的事情。
刚来的第二天,他发了高烧。她用湿毛巾给他擦胸,她记得,他似乎为自己的裸胸而羞涩和不安。他想抬起手扯上被子,却疲乏得连手也抬不起来。
“别动。”李燕琪说:“你真了不得,发烧到摄氏39°呢!我现在给你用凉毛巾擦身子,物理降温。”
刘明宇愣愣地看着她,呆了一会儿,点点头。
他一连躺了三天三夜,她就在他床边守了三天三夜。除了吃饭,上厕所,她一直坐在他身边,喂他药,喂他水。困了便把腿伸到另一把椅子上,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当他退了烧从昏睡中醒来时,她便用快活的笑声赶走他的寂寞和疲乏。
他用令人窒息的长吻,回报她的照料,而且答应做他的男朋友,带她一道去河南。
她很快沉浸在快活的幻想中,忘了父母。而且,她还几乎相信,他的承诺马上可以应验。结婚,是件大事,至少得有半年一载的准备,对于将要嫁给的这个人,也至少得有相当岁月的了解。要走上真正的婚嫁之路吗?她才十六岁,似乎还早着吧?
“顺山倒喽……”在随后的日子里,她喜欢看他在油锯轰鸣的林场里忙碌,他量木材查码单时认真的样子,他的心事苍茫,他的歌声忧郁,他的饮酒大醉,他的逍遥无边,他的呼吸,他的默想,他的自语……
闲暇的时候,他就坐在林场旁的草地上弹吉它,她安静的坐在一旁听。他一边弹琴一边轻声跟她谈话,总是告诉她他觉得她多么好看,他多么喜欢她。我给你唱支歌罢,他说。她不置可否,只对他笑笑。他低声的唱着《流浪歌手的情人》。她静静地看着他,被他的声音感动。
“云南是个神奇的地方。”他说。
“诸葛亮在这里七擒过孟获,”她微笑着,“汉武帝、唐玄宗、忽必烈曾先后血洗过这里,吴三桂、陈圆圆,林则徐都来过,你也来过。”
“还有凤尾竹、雪莲花、桫椤、望天树、《五朵金花》和《阿诗玛》、美丽的西双版纳、美丽的清晨、美丽的阳光,还有美丽的你。”他说。他走到她面前,伸一小束野花:“谢谢你陪我的这些日子。”
她在他温柔地笑容里接过花。十六岁前,从来没有人给她献过花,即使是特殊的日子。
“云南还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他问。
“多了,”她骄傲地说,“云南有十八怪。”
“十八怪?哪十八怪?”他问。
“小和尚可以谈恋爱,石头洞里有村寨,娃娃出门男人带,姑娘叼烟袋,粑粑叫饵块,老太爬山比猴快,草幅当锅盖,竹筒当烟袋,草绳当裤带,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萝卜当作水果卖,三个蚊子一盘菜,青菜叫苦菜,火车没有汽车快,鸡蛋栓着卖,姑娘叫老太,东边下雨西边晒,背着娃娃谈恋爱。”
“背着娃娃谈恋爱?这里可以先尝后买?”他兴奋了起来。
“去你的!这只是云南少数民族试婚习俗的遗留,一般是女方有了小孩才能到男方家举行婚礼。”
“试婚?不错不错,想不到思想这么开放。怎么能叫遗留呢?分明是先进嘛。那姑娘叫老太是什么意思?你叫老太?”
“我有那么老吗?”她笑道:“只有少数民族才这么叫,叫小姨为舅老太。”
“老太爬山比猴快可以理解,小和尚可以谈恋爱怎么解释?小和尚可以谈恋爱?”
“傣族少年都要进佛堂学习,佛堂即学堂,并非大乘佛教里小和尚的概念。”
“哦。”他点点头。
“还有更怪的呢。有一种苦冲人,尚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期,还有一种摩梭人,仍然保持走婚习俗。”
※※※※※
脚被剌穿的那个晚上,他对她说:“你真的很漂亮。”然后一把抱住她,把她搂得紧紧的,在她的脸上,肩上印满无数个吻。
她猛地推开他,坐起来。两个人谁也不说话,急促地喘着气,彼此在暗黑中寻视对方。
但最终,她的防御还是宣告了崩溃。
他的手颤抖地滑过她的胸脯,她本能地捂上自己的胸,又突然推开他的手。他迷惑一会,声音发颤地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夜里,躺在他的怀里,做了个梦。
她置身于一片竹林之中,碧竹高耸入云,密密排列着,有轻烟或薄雾笼在眼前,微透着沁肤的凉意。她在林中奔跑,似乎在寻找什么人;又象是被什么人追赶,一颗心凄凄惶惶的悬吊着,除了自己的喘息,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她困难而费力的迈着步子,常感觉来路被阻了,却又豁然开朗……她一直跑到一道小溪旁,不得不停住,溪水揣急,没有可以跨越的石块,也没有渡船,她极为不甘的停下来,然后,便清楚的听见一声叹息,悠长、缓慢、深沉、男性的叹息……她醒来,冷汗涔涔


![[古穿未]星际宠婚封面](http://www.cijige2.com/cover/0/12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