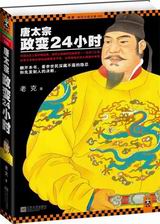小时代3.0刺金时代恢复连载:最小说-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雪糕走后,我便一个人上班。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坐在前台,有旅客来了就帮他们登记入住。不断地接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夫子庙青年旅舍。”“不好意思,今天已经没有标准间了,只有床位了。”“嗯,好,我已经帮您预订了,到时候凭着您的有效身份证就可以入住了。”……每个晚上,都重复着这些话,却没有感到过厌倦。
住青旅的,几乎都是背包客,他们背着大大的行囊,钱很少,梦想很多。他们从世界各地过来,住在这个小小的旅舍里,共用着一个小小的房间。晚上,他们坐在旅舍的客厅里,喝啤酒、聊天,我喜欢坐在前台,静静地听他们说话。
等到凌晨1点多,客厅里的客人基本上散尽了,我就关好大门,锁好抽屉,把客厅里的电灯都关掉。这个时候,我可以躺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儿。
不过,通常睡不过10分钟,就会被敲门声或者电话吵醒。
有的时候半夜里突然下暴雨了,我就要走到阳台上,把旅客们晾在外面的衣服一件一件收进来。手忙脚乱一阵后,坐在空空的大厅里,望着窗外安静的秦淮河,那个时候,心里有一点儿落寞。
有一个北京男生,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南京。抵达旅舍已经是凌晨3点多,但是他不回房间睡觉,一个人坐在大厅里喝酒,他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喝酒,直到天亮才上楼回房间。后来的几天,白天他在房间里睡觉,晚上就一个人在大厅里喝酒。
还有一个韩国人,在大连读书。中文说得不好,却很喜欢和旅舍的人聊天。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和他聊天。有一次和他一起出去吃饭,我们走进了一家很普通的餐食店,我点了牛肉饭,他吃卤肉饭。最后付账的时候,他一定要帮我付钱。我不好意思,他说:“我比你年纪大,应该我来。”
后来,我们去南城墙附近散步。日落黄昏,很多老太太在城墙下放着录音机跳舞。她们放的曲子是《大长今》的主题曲。
最好的夏天(4)
“大长今?大长今!”他激动地叫了起来。
“呜啦啦,呜啦啦……”他手舞足蹈地边唱边跳起来。但是,他唱着唱着,就哭了。他说,他在中国读书,已经两年没有回国了。现在,他一听到韩国歌,就会哭出来。
我傻傻地站在旁边。那个时候,我并不能理解他的那份心情。但我知道,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秘密吧。那个秘密,可能是一件事,也可能是一个人。那个人站在他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有一件在自己心里珍藏着的事情,或者一个人,该是多么幸福的事。
辛苦地通宵工作,但还是出了差错。有一天早晨,和玉姐交班的时候,在核对账目的时候,发现少了两百块。算了好几遍,还是少两百块。没办法,只有自己掏出两百块补上。可是,我也没有两百块钱啊,只能先记在账上,从后面的工资里扣了。
后来,我越想越郁闷,越想越气,明明都按照程序走的,怎么会少两百块呢?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补救的方法。
青旅里有两台电脑,那两台电脑上网是要收费的,4块钱一小时。但是很多旅客都只上几分钟,所以就不问他们要钱了。其实即使他们上几个小时,如果他们没有自觉地付账,我也不会去问他们要钱。
但是后来,只要有人用电脑,我就盯着,留意着他们的上网时间,然后向他们收钱。那些钱,我不记到账上,自己私藏起来,补到那两百块里面。不到一个星期,那两百块钱竟然就存满了!
我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感到窃喜。补回的这200块钱,无论王叔怎么查账都查不出来的。
后来我打电话给雪糕,告诉他这件事,他惊讶地说道:“原来你也想到了这个方法?!”
旅舍里有一台咖啡机。如果旅客要喝咖啡,前台就给他们磨。那咖啡豆一般般,却要10块钱一杯。除了一些鬼佬,很少会有人点旅舍的咖啡。
一天晚上,旅舍里来了三个毕业旅行的大学生。我和他们在大厅里聊得很开心,一直聊到凌晨。他们点了咖啡,在大厅里面喝。最后结账的时候,他们付钱给我,我一开心,就摆摆手说:“不用啦,我请你们!”
本来想算啦,如果不记到账上老板也不会发现。后来作了很大的思想斗争,还是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30块钱加到营业额里。
后来,那些聊得好的客人,每次去收他们的钱,我都下意识地想说:“不用啦!我请!”我暗暗嘲笑自己,真是打肿脸充胖子,自己一个晚上才赚那么点儿钱。但是,那份心情是真的,那种,想和他们分享快乐,想带给他们快乐的心情。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我领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工资,860块。
王叔数钱的时候,我的心怦怦地跳,大气都不敢出。他点好钱,把钱递给我。我接过钱,手还有一点儿颤抖。
拿到钱的那个中午,我连午饭都没有吃,就兴奋地拿着钱坐公交车去商场里,打算给爸妈买一份礼物。在公交车上,我还在想,到底买什么呢?我越想越兴奋。但是,等下了公交车,我的手一摸口袋钱包没了!
我摸遍了所有的口袋,还是没有。我掏出另一个口袋里仅有的几个硬币,重新坐上公交车,回到了出发地,低着头来回找着,还是没有。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肯定是刚才挤公交车的时候,被小偷偷走了。钱包里,不光有我的第一份工资,还有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我愣愣地站在车站里,站了好久,才万念俱灰地走回旅舍。走到了阳台上,忍不住哭了起来。边哭边骂,越哭越伤心。
李奶奶看到我,就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钱被偷
光了。”她说:“在哪里被偷的啊?”我没有回应她,又捂着脸哭了起来。我觉得自己完蛋了,现在连回家的钱都没有了。
过了好一会儿,王叔走了过来,说:“走,我带你去报案。”于是我就跟着他去了夫子庙派出所,作完笔录后,走出派出所,王叔突然说:“你等一下。”然后,他走进了一家饭店旁边的火车票代售点。
他买了一张第二天回杭州的动车票给我,然后说:“你先回家再说,不要着急。”
我说:“我会把钱还你的。”
他笑了,说:“没事没事。”
我们走着,他突然又说:“你回去,总得带点儿东西吧,好不容易来趟南京。”他又带着我去了一家咸水鸭店,买了一只咸水鸭给我。“你先放心回家,派出所这边一有消息我就会打电话给你的。”他边走边说着。就这样,落魄的少年,两袖清风,提着一只咸水鸭,回家了。
【2009】 我上大一那年,有一个朋友要去南京旅行,让我帮他预订青旅。我答应了,于是就从网上找到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嘟嘟”声响了好久,才被接了起来。“喂,你好,这里是夫子庙青年旅舍。”是一个陌生男生
的声音。
“喂……”话才刚说出口,就莫名地哽咽住了。
“喂,你好,喂?还在吗?”
“在在,不好意思……我想预订后天的一个床位……”
我们讲完,挂了电话。突然,我脑中浮现出了一个画面。一个瘦小的男生,穿着背心坐在前台,左手抓着话筒讲电话,右手拿着一张报纸使劲地扇着。南京的夏天,气温逼近40度,窗外的秦淮河似乎都泛起了蒸汽。梧桐树上的蝉鸣,一层又一层地在城市上空回响。
那个男生,是18岁的我吗?
想着想着,就湿了眼眶。
。。
是我不是梦(一)
文/野象小姐
光一下子涌入,趴在玻璃柜上午睡的徐智博吃力地睁眼。
“喏,”西瓜风铃被撞得叮叮响,女孩将一只冒凉气的碗啪地搁到玻璃柜上,“阿嬷叫我拿给你。”转身离开,旋起一小股热风。
这是谁?
揉揉眼睛,木门扇几下“吱嘎”扣回来。屋里空气暖融黏稠,端起碗,薄荷凉茶味儿扑面而来。
傍晚,地面余热未散尽,站在门口伸懒腰。见隔壁凉茶铺的阿嬷在木桩上支起圆板,另一只手掖着碗碟。两个小孙子在一边绕着筷子和黑狗嬉闹。
“阿嬷开饭好早,今天什么菜?”
“芋头蒸排骨啦、豆腐捞饭啦……”
“这么好!”
“想吃就动作快点儿,”阿嬷挑眉,“年轻人懒死了整天不做饭。”
“智博!今天阿康伯炖鸡了。”摆台球生意的阿康伯赤膊坐在榕树下,朝他招蒲扇。他“嘿嘿”笑两声,回屋把空凉茶碗拿出来还给阿嬷,拎把竹椅凑过去。
“宋家阿嬷,那是小英吧?”阿康伯筷头指向不远处。树荫下,女孩长头发圆脸,一个人坐在青蛙凳上埋头吃饭,是中午送凉茶那个。
“回来过暑假嘛。”阿嬷忙着招呼另两个顽童。
“哎呀!小时候在这儿也念了好几年书,有七年吧!怎么生疏起来了,吃个饭跑那么远。”阿康伯瘪起肚子,扯起嗓子喊,“小英!来阿伯这儿吃鸡肉。”
原来是宋小英啊。智博碗里被阿嬷摁了好几块排骨,三两步又辗转到阿康伯饭桌前。望过去,女孩背影脆落,猛一伸腿吓得悠闲踱步的鸡乱窜。
天黑了,石桥上亮起灯。帮阿康伯收拾碗筷,听到大娘们的碎语。“学建筑哦,大学二年级。”“好像是得了什么病吧,脑子里的病,被劝退学。”“不是,听说是和老师好上了。” “哎,别说了别说了,阿嬷听到该伤心了。”
是我不是梦(二)
刻着“徐记钟表”的牌匾挂在门额上,繁体字的写法和力道,足见历史久远。店面经过祖辈三代,的确旧了。工作不复杂,无非修表卖钟,偶尔替人鉴别古董表。爸爸去世后,徐智博一人经营。
又是正午。整条街被浓重树荫笼罩,枝条拂入门前的溪水中。知了热闹,声音却遥远得很。金色光斑跳跃,风掀得树叶“哗啦”响。
钟表店半掩着门,门板上挂着把长柄伞,几支顽童随手撂下的风车斜插在上面。玫红色的九重葛从屋顶垂下。屋角弃置着台绿冰箱,被碎石和藤蔓包围。这高温多雨的季节,盆栽长势奇好,大大小小的瓷盆摆满门庭,堆上小石桥。
“哐!”徐智博被惊醒,推开纱门探头瞅。原来倚在木梁上的自行车被风刮倒了。走过去扶起来,转身看见长头发女孩,穿浅绿背心短裙,坐在门边长椅上,手里冰棍只剩最后几口。
“生意惨淡啊。”女孩清朗一笑。“嗯,天太热。”徐智博还没从午睡中完全清醒,头晕,“进来坐。”
满屋形态各异的钟表,墙上挂的、地上摆的、橱窗里码的,争先恐后咔嗒响。“我记得,初中早自习大家都背书,你老爱躲在书后面哼歌。”小英坐在椅子上笑起来。
“是吗?”
“你坐我后面嘛我记得可清楚了……八年,咱俩八年没见了是不是?”小英伸手拨电扇格罩。印象中,他是对世界怀有淡淡敌意的少年,“你经常哼那歌是什么?”
“忘记了。”
“徐爸五年前过世了?”
“嗯,跟我弟。”徐智博眉目如浅墨,轻描淡写得不可思议。小英默默点头,抬眼看他。头发嘴唇薄薄的,模样跟初中差不多,除了个子拔高了些。他自小妈妈就死了,听阿嬷讲,后来十六岁那年弟弟落水,徐爸跳下水救他,最后两人都被大水冲走了。
阿嬷是小英的祖母,在这条街上卖了几十年凉茶,小英从小被她抚养,和徐智博是邻居。小学到初中一直同班,初二那年她被做生意的爸妈接回城里便再没回来。分开时两人才十二三岁。
屋里有许多钟,指针跳得不整齐,每一秒都能听到好多咔嗒声。于是一秒似乎变成好多秒。
小英每天捧碗凉茶给智博,有时是薄荷,有时是荷叶,或者酸梅、雪梨、玫瑰花、桑葡,用青花大瓷碗盛得满满的。人一熟,话便多起来。没过几天,两人又如小时候般热络。
一次,电视里放台湾偶像剧,小英在智博家握着遥控器自顾自抱怨:“编剧五十岁、导演四十岁、演员三十岁,拍一个他们想当然的二十岁就是偶像剧?两个长相好看性别不同的人凑一块儿就叫爱情?批量产出的都市爱情能感动谁呀?能取悦谁呀?当观众全是白痴啊?无聊。”接着转头对智博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挺愤世嫉俗的,一张不理人的死脸,几年不见怎么变这么温吞?”
智博说:“我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自打我爸和弟死后,老是做噩梦,吓着吓着就豁然开朗了,对人对事有了全新的态度。”接着又补充道,“虽然还是经常被噩梦吓醒。”
小英啧啧两声,说:“难为你了,做噩梦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徐智博冷笑两声,对这娘气的形容表示不屑。
小英腾地爬起来,在凉席上盘腿摆出苦口婆心的姿势。她说:“缺乏安全感很正常啊。你首先得正视自己,你不用对生活负全责。没安全感的人总觉得必须要做点儿什么,或必须处于焦虑状态才能应对未知的变化。你得学会承认一个事实,人生本来就是不安全的,即使你没有经历失去爸爸和弟弟的不幸,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