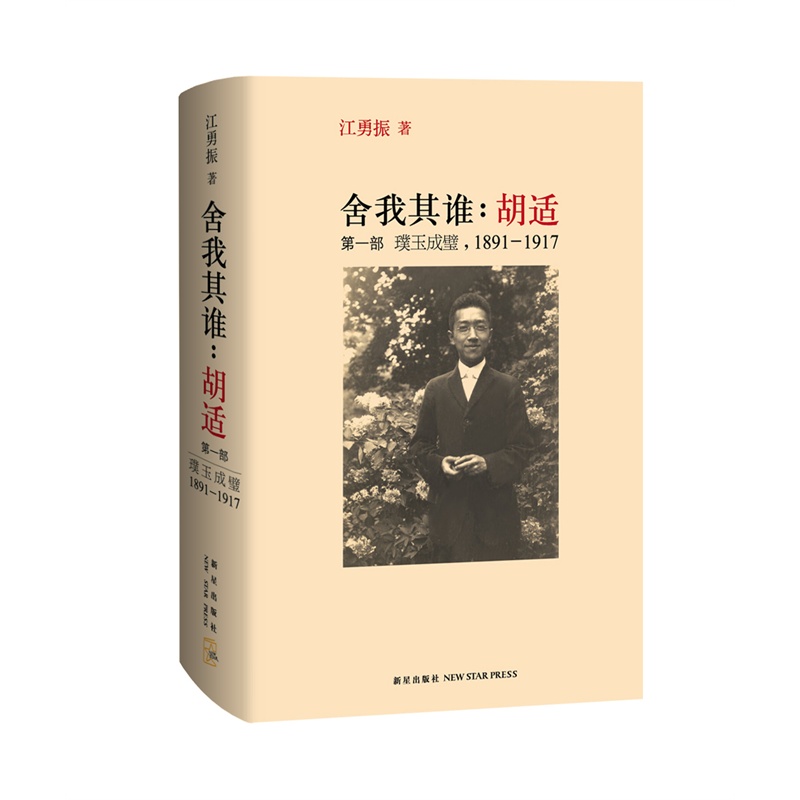舍我其谁:胡适-第1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实耳),盖此书所志不在状人,而在状一种困苦无告之人群,其中本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也。二、剧中主人既是一群无告之识工,其人皆如无头之蛇、丧家之犬,东冲四突,莫知所届。读者但觉其可怜可哀,独不知其人所欲究属何物,此其与他剧大异之处也。读《西柴》'《恺撒》'者,知布鲁佗'Brutus,刺杀恺撒者'所欲何事,亦知高西厄司'Cassius,刺杀恺撒阴谋主导者'所欲何事。读《割肉记》(Merchant of Venice)者,知休洛克'Shylock,以放高利贷致富的犹太人'所欲何事。读《哈姆雷特》者,知'此'丹'麦'王子所欲何事。独读此剧者但见一片模糊血泪,但闻几许怨声,但见饿乡,但见众斗,但见抢劫,但见格斗,但见一股怨毒之气随地爆发,不可遏抑。然试问彼聚众之工人所要求者何事、所志在何事,则读者瞠不能答也。盖此剧所写为一般愚贫之工人,其识不足以知其所欲何事,其言尤不足以自白其所志何在也。”此种体近人颇用之,俄国大剧家契可夫(Tchekofv'Chekhov')尤工此。'6'
胡适对十九世纪西洋戏剧的兴趣,主要在于其写实主义的角度。用胡适在日记里所用的名词来说,就是问题剧。他在记录他读赫仆特满的《东方未明》的同一天,也就是1914年7月18日的日记里说:“自伊卜生'易卜生'(Ibse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社会剧,又名‘问题剧’(Problem Play),以其每剧意在讨论今日社会重要之问题也。业此最著者,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为赫氏,在英为萧伯纳(Bernard Shaw)氏,在法为白里而氏。”'7'
在留美学生里,像胡适这么用功、兴趣这么广泛的人是不多见的。他不但自己读书、勤于听演讲,还组织读书会跟同学一起砥砺讨论。比如说,胡适在1914年7月18日的日记还记他组织了一个读英文文学名著的读书会:“发起一会曰读书会,会员每周最少须读英文文学书一部,每周之末日相聚讨论一次。会员不多,其名如下:任鸿隽、梅光迪、张耘、郭荫棠、胡适。余第一周所读二书:Hawthorne;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霍桑,《七个尖角屋顶之屋》';Hauptmann; Before Dawn'赫仆特满,《东方未明》'。”'8'
除了听演讲、组织读书会,胡适还勤作笔记。光是在7月18日,他就记下了两本剧本的读后感:
上所举第二书'《东方未明》(Before Dawn)'乃现世德国文学泰斗赫仆特满(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最初所著社会剧。赫氏前年得诺贝尔奖金,推为世界文学巨子。此剧《东方未明》,意在戒饮酒也。德国人嗜饮,流毒极烈,赫氏故诤之。全书极动人,写田野富人家庭之龌龊,栩栩欲活,剧中主人Loth and Helen尤有生气。此书可与伊卜生社会剧相伯仲,较白里而(Eugène Brieux,18581932)所作殆胜之。'9'
又:
今日又读一剧,亦赫氏著,曰《织工》(The Weavers),为赫氏最著之作,写贫富之不均。中写织工之贫况,真足令人泪下。书凡五出:第一出,织工缴所织布时受主者种种苛刻虐待,令人发指。第二出,写一织工家中妻女穷饿之状。妻女日夜织而所得不足供衣食,至不能得芋(芋最贱也)。儿啼索食,母织无烛,有犬来投之不去,遂杀以为食。种种惨状,令人泪下。第三出,写反动之动机。兽穷则反噬,固也。第四出,织工叛矣。叛之原因,以主者减工值,工人哀恳之。主者曰:“不能得芋,何不食草?”(此有“何不食肉糜”风味。)工人遂叛,围主者之家,主者狼狈脱去,遂毁其宅。读之令人大快。第五出,写一老织工信天安命,虽穷饿犹日夕祈祷,以为今生苦,死后有极乐国,人但安命可矣。此为过去时代之工人代表。今之工党决不作如此想也。此老之子妇独不甘束手忍受,及工人叛,妇持斧从之。其子犹豫未去,闻门外兵士放枪击工人之声,始大怒,持刃奔出从之。老工人犹喃喃坐织门外,枪弹穿户入,中此老,仆机上死。俄顷,其幼孙奔入,欢呼工党大捷矣。幕遂下。此一幕写新旧二时代之工人心理,两两对映,耐人寻味。令人有今昔之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此旧时代之心理也。“人实为之,天何与焉?”“但问人事,安问天意?”“贫富之不均,人实为之,人亦可除之。”此新时代之心理也。今工人知集群力之可以制资本家死命也,故有同盟罢工之举,岂得已哉!谁实迫之而使至于此耶!此剧大类Mrs。Gaskell’s“Mary Barton”'盖丝蔻,《玛丽·芭屯》,描写维多利亚时代的下层社会',布局命意,大抵相类,二书皆不朽之作也。'10'
7月30日,他又读了“瑞典戏剧巨子施吞堡(Strindberg)短剧名《线索者》(The Link),论法律之弊,发人深省。伊卜生亦切齿法律之弊,以为不近人情,其所著《玩物》(A Doll’s House或译《娜拉》)中之娜拉与奸人克洛司达一席话,皆论此题也。”'11'年12月,秋季班结束放圣诞节假的时候,胡适又读了七个剧本。他在12月20日的日记里说:
连日读赫仆特满(Hauptmann)两剧:一、《韩谢儿》(Fuhrmann Henschel);二、《彭玫瑰》(Rose Bernd)。又读梅脱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梅氏为比利时文学泰斗,为世界大文豪之一)四剧:一、Alladine and Palomides'《爱乐婷与帕洛米底司》';二、The Intruder'《不速之客》';三、Interior'《屋内》';四、Death of Tintagiles'《婷绨凯之死》'。又读泰戈尔(Tagore,印度诗人)一剧:The Post Offce'《邮局》'。三人皆世界文学巨子也。'12'
胡适对戏剧的涉猎让他对戏剧的品评颇有自信。这个自信甚至在他广泛地涉猎十九世纪西洋戏剧以前就已经有了。比如说,我在第四章分析过他可能是在大三上学期所写的读书报告:《哈姆雷特:一出没有英雄的悲剧》。他在这篇报告的结论说:
我们在本文里追溯了哈姆雷特的一生,发现他——用我在本文启始所说的话来说——一丁点儿英雄的气概也没有。让我再征引歌德的话来说:“他有一个优美、清纯、高贵、道德的本质,但没有作为一个英雄所应有的勇气;他心中的重负'母亲跟毒死自己父亲的叔叔结婚'压跨了他,他既担不起又放不下。他所面对的是作不到的——不是作不到,而是他作不到。”对他来说是太难了。我们听到他呼号着:
这整个世界都脱序了。喔!真是厄运,
让我来这世间就是要我去拨乱反正!
这就是哈姆雷特,就是一出没有英雄的悲剧里的“英雄”。
不只是哈姆雷特不够英雄,这出戏里没有一个称得上是英雄的人物。那乱伦、杀人的克劳底尔司(Claudius),用麦考莱的话来形容,“整个人就是匕首与面具”,最后死在自己的“回头箭”下。皇后呢!就像哈姆雷特对她说的:
喔!不要脸!妳的羞耻心到哪儿去了?
至于娥蜚(Ophelia),她既没有蔻黛丽(Cordelis)'《李尔王》的幺女'优雅的顽强,也没有茱丽叶狂热的爱,也没有马克白夫人的“不男不女”(unsexedness)。她的柔弱几近于曲承。'剧中的'莱提司(Laertes)呢!海司里特(Hazlitt)说他“有点好自吹自擂”。可他顺从克劳底尔司的诡计要去害哈姆雷特。还有那鄱罗尼尔司(Polonius)'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翻成“潘老丈”',那个最圆滑的笨伯,他深谙人世间所有的教训,却栽在不知“好管闲事会惹祸”的道理'这是哈姆雷特在第三幕第四景刺死鄱罗尼尔司以后说的话'。
喔!好一群傀儡、笨伯和丑角!喔!真是一出没有英雄的悲剧!然而,大家都喜欢这出戏。看着《哈姆雷特》里的这些傀儡、笨伯、丑角在那儿扯淡、蒙骗、说谎、毙命,大家都为之欢呼、落泪、叫好、拍手。人人都说莎士比亚最绝妙的作品是《哈姆雷特》。这原因何在呢?我觉得理由很简单。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斥着傀儡、笨伯与丑角的舞台。傀儡、笨伯与丑角是众多、遍在、近在眼前的;英雄则是少见、稀有的。怯懦之行天天可见;英雄事迹则仿如凤毛麟爪。我们喜欢司各特(Scott)'Walter Scott,17711832'的小说,因为小说中有英雄人物。我们喜欢阿拉丁'《十字军英雄记续》里的人物'、犹太女子萝蓓卡'《艾凡赫》里的人物',因为他们是英雄、稀有的。然而,我们更喜欢撒克里小说里的贝姬、斗宾少尉'《浮华世界》里的人物'和艾斯蒙'《艾斯蒙传》',正因为他们不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像你我他一样的实际、平凡和所在皆是。就像虚荣的女性喜欢顾影自喜一样,这平凡的世界在这出莎士比亚的杰作里看到的是自己的写照——那没有英雄的悲剧。'13'
如果我们觉得《哈姆雷特:一出没有英雄的悲剧》的结论颇为熟悉,那就是胡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易卜生主义》思想的雏形。胡适的思想里自有他精英主义的部分,虽然他也深信民主制度的功用与价值。但这都是后话。胡适显然相信在人类社会里,大多数都是平凡的芸芸众生,特立独行的英雄乃是少数。这些“英雄”用他在写给梅光迪的一封信里的话来说,是“天生的贵族”(natural aristocrats),以别于那些命好,生在帝王、将相世家的贵族。这些“天生的贵族”是带领社会进步的要素。可惜胡适这封信现已不存。我们只能从梅光迪的回信推测胡适信中的大意:
来书所主张之实际主义'写实主义',与弟所恃之humanism(姑译之为“人学主义”可乎)似多合处。足下之第一条,迪极赞同。第二条亦无所置议。惟第三条就字面论之,似有不能全然了解处,请再一言之可乎?迪谓今世风行社会学说(social philosophy),似多分“社会”与“个人”为二物,尤有流弊者,乃在偏重社会方面。有个人作奸犯科,自命为社会改良者,乃归其过于社会,以为社会上某某制度、某某法律若革去,则其社会中份子自可皆归于善。此种改良,以迪观之,乃倒行逆施耳。故今之西方社会上,其改良家愈多,其社会腐败乃愈甚。此非悲观之言,乃实境也。何则?由其个人(社会分子)腐败也。故言“人学主义”者,主张改良社会,在从个人做起,使社会上多有善良个人,其社会自善良矣。孔子之言曰:君子修其身,而后能齐其家,齐其家而后能治其国……欲改良社会,非由个人修其身,其道安由?足下所称之“natural aristocrats”'天然贵族',即弟之所谓humanists(人学主义家)也。此种人无论何时,只居社会中少数。不过一社会之良否,当视此种人之多寡。'14'
梅光迪对许多社会学说——包括胡适——把“社会”与“个人”一分为二的批判是有见地的。然而,他也为成见所囿,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于个人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是个人的腐败。这是传统儒家从修身出发的政治社会哲学的一支,与典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汇流。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传统个人主义的观点。从留美到1940年代初期的胡适,一方面想用社会立法来救济传统自由主义的不足与缺失,一方面又要确保少数特立独行的个人不被社会上平庸的大多数所迫害、淹没与埋葬。这种“社会”与“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紧张与矛盾如何取得创造性的均衡,是胡适在他人生不同的阶段、扮演不同的身份、面临不同的事例时,所必须权衡、加持或割舍的。在他留美的后期,胡适着重的是他从易卜生的戏剧所悟出来的特立独行的个人。
'1' 胡适致《甲寅》编者,无日期'1916年秋',《胡适全集》,23:8283。请注意,《胡适全集》主编系此信为“约7月左右”,误。胡适在信尾签名:“胡适白自纽约”。胡适是在9月20日搭夜车离开旖色佳的,次晨抵纽约,搬进哥伦比亚大学。换句话说,这封发自纽约的信只有可能是该年秋天写的。
'2'“English Professors to Give Readings,”Cornell Daily Sun; XXXIV。100,February 14,1914,p。8。
'3'“Professor Sampson On“The Modern Drama,”Cornell Daily Sun; XXXIV。24,October 18,1913,p。1。
'4'“Professor Sampson to Discuss Maeterlinck,”Cornell Daily Sun; XXXIV。95,February 9,1914,p。4。
'5'“Schiff to Introduce Prof。Ernst Elster,”Cornell Daily Sun; XXXIV。95,February 9,1914,p。1;“Hauptmann a Leader of Naturalist School,”Cornell Daily Sun; XXXIV。136,March 28,1914,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