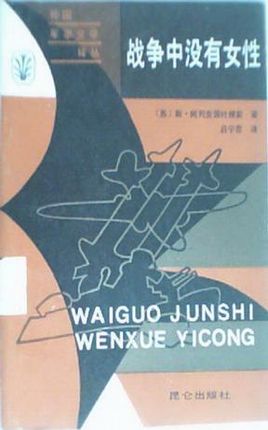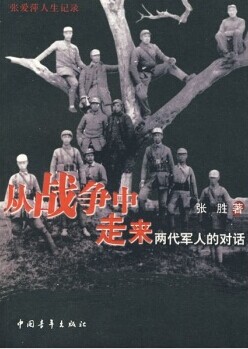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十六(日)
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
接下来是周恩来批的五个字:周恩来已阅。(原件没有注明日期)
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按惯例理解是三个字:“知道了。”如果你非要说,是经过某某批准的,也无大碍。这也是一种艺术。一个八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就这样被打倒了。
在“文革”中,每一个被打倒的干部,都有他自己特殊的经历,但在他们这些故事的背后,多多少少都会找到许多相近似的地方。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县委书记,有多少是被群众揭露出来然后被群众打倒的?所谓的群众运动,说到底都是上面的旨意。无怪“文革”中流行一句话:“什么叫群众运动?实际就是在运动群众。”
远在广州的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特地写来揭发信:“张爱萍和彭德怀关系很深。林副主席指示,军队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最近又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我建议总参党委对张彻底审查。此信如你认为有必要,请转呈林副主席一阅。”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黄永胜这封信?这封信源于军委办公厅向全军发过的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送交揭发批判张爱萍反党言行的材料。奇怪的是,现在居然找不到文件签发人是谁,这样一个发到全军的通知竟然没有人对它负责。
父亲停职后,每日的“功课”就是被拉去批斗。总参、总政、空军、海军、国防科委以及下属的各科研院所;有斗他个人的,也有陪绑的,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彭真……有关的和无关的。
他说:“开始我还注意听听,都是些言之无物的东西,就由得他说吧。被斗的没有哪个服气的,我印象中,彭老总的头总是昂着,那些人整他就更凶。所谓搞你喷气式,就是把你的胳膊拧到背后向上抬,逼迫你弯腰低头。”
通常是一早被押走,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喷气式”和挂“黑牌子”无情地损伤他的身体。父亲左臂负过伤,每次批斗都被人强拧着。一次他终于大汗淋漓昏倒在地上了。空军的一个干部将他扶到后台,给他水喝。父亲说:“我没有能问他的名字,但我很感激他。”
妈妈说:“成天提心吊胆的。只是,人的承受能力往往连自己都会吃惊。后来摸出点规律。一般都是清晨4点,警笛的怪叫声一响,就知道来抓人了。赶紧弄些吃的,否则一天下来,人都虚脱了。只要人能回来,就是好的。”
但有一天,他没有能够回来。
1967年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
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
专案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
1967年6月7日,中央专案组二办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信,指控“在张爱萍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
9月19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
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党委领导人立即指示:“拟派人去上海调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查阅敌伪报刊、档案和党史绝密资料,提审在押人员等,请张春桥帮助。”并在公函上亲笔批示:“同意写信请春桥同志帮助。”时间是10月18日。
12月14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一份自首书。南京军事学院造反派送上报告:“张爱萍原名张瑞,曾在伪苏州反省院自首。”
他完了!张爱萍彻底完了!大喜。又是这个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
12月18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
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
1967年12月26日,父亲被宣布正式逮捕。
两个月后,苏州消息传来,张瑞不是张爱萍。真他妈的扫兴。好在此时已经将张爱萍以审查为由关押入狱,反正目的达到了。他们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面前,任是铁人也得招供画押!
父亲被抓走的这天,正是12月26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铁窗生涯。
妈妈回忆这一天:“下午,单位来人,说急着要找份文件,催我快去单位。我心生狐疑,交代了你爸爸几句,就匆匆跟他们走了。到单位等了很久,主任才进来,他说接上级通知,现已对张爱萍实行隔离审查。我立即要求回家,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还能不能见到,这种生离死别的事,在那个年月看得太多了,但他们不许……”
妈妈在民航局工作,是经吴法宪介绍的,吴的夫人陈绥圻“文革”时是民航革委会成员。她们还曾是患难之交。
我读过一部苏联纪实体的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这部百万字的长卷引起了我对往事痛苦的回忆。苏联大清洗期间的捕人方式是在夜间,在寂静的深夜里将你从睡梦中拖走,让你连裤子都来不及穿。相比之下,我们要仁慈得多了,略施小计,从好处想,或许也是避免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场面。
父亲对这一天的回忆是:“你妈妈一走,专案组就来了,蒙上了我的眼睛,我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我想要等到你妈妈和三子、艾子回来,临别,也该给你们留下句话啊!但已经办不到了。直到5年后,出了狱,才知道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
我那年在军队,几十年过去了,在父亲平静的叙述中,我仍然能看见他像犯人一样被蒙面押解的那一幕,我的心在作痛。
“车子绕了很久。解下蒙布,是一间潮湿的小黑屋。我不知道是在哪里。”
“有一块床板,一张小凳。窗户都糊上了,灯老是亮着。皮带、鞋带都没收了。走路要提着裤子,睡觉脸要朝外,坐着要双手抱膝。门上有个小洞,外面蒙块黑布,便于向里观察。一人两个碗,开饭时从门底的洞递出去。上厕所要提前报告,有时等不及了,屎尿就拉在裤子里。除了提审就是写交代材料。”
我妈妈接着讲:“我预感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曾相互勉励,我说,只要你挺住,我就能挺住。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临别和你爸见一面。他们一直关我到深夜,估计是那边都办完了吧,才放我回家。看见三子脸上挂着泪睡着了,他看见我就哭了,说爸爸被他们抓走了。其实,你爸被抓走时,三子已经放学回来了,被他们关在外面,他是在窗户里看见你爸爸被带走的。”
父亲在生活上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在人际交往上,也不是个爱计较小事的人,但他也绝不是个能随便就冰释前嫌的人。从“文革”后期被放出来,一直到他老年,他和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这段经历。看得出,这在他心上留下了多大的伤痕。
他说:“这一夜,我眼泪一直在流,天亮了,枕头全都打湿了。斗罗瑞卿,是用箩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我当时就把拳头攥起来,你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但现在我很绝望。我想不通,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会落到这步田地。”
“我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租界里的英国巡捕房,流血负伤不下十几次,不论怎样困难,我从未流过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都是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我的戎马生涯中只打过一次败仗,中了敌人的埋伏,(注:本书第一章有详述)毛泽东知道了,还鼓励我说,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你们都知道的有一首歌,唱的是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实在是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打了败仗,尚可原谅,而今天,为什么就非置我于死地呢?”
无论这个故事讲过多少遍,偶然碰及到这个伤口,我们全家人,讲的、听的,总会是泣不成声。
3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从1966年下半年始,家里的这种状态,再加上因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问题而背上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在部队这样一个思想、纪律、言行高度军事化的集体里,我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连队也没有整过我,只是上面经常会问到我,看到连长、指导员及周围的同志们因为我而如临大敌,我时常会歉疚。我总是自觉地按他们的要求汇报思想,说到伤心处往往眼含热泪。连长赖子英是个武夫式的军人,见不得别人伤心,赶紧打断岔开。政工人员相对就冷静得多了,告诉我日记信件应该主动交给支部,以示自己对组织的坦诚,组织对每一个愿意革命的同志还都是一视同仁的。家里寄来的信件很难得再收到了,也不知是投递的差错,还是有别的原因,没有根据的事不好瞎说的。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成了个珍稀动物,除了受到特别的关照外,我不再有同类。家在千里之外,渺无音信,我常一个人坐在营房边的山坡上,望着落日。
父亲早些时候曾给过我一封信,是写给温玉成的,温是广州军区副司令。父亲说,其他人都不太熟,如果真的有什么难了,拿着这封信找找他,看在老战友的情分上,或许能帮帮你。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岌岌可危的处境。信上说,目前每个人都在接受考察,在考察中把子女牵扯进来加以责难,是不大妥当的。
他已经对自己和孩子们的命运预感到什么了吗?
我来到军区司令部大门。
我曾多少次进出这里,但那是执行任务,而今天怀着个人的希求,以戴罪之身偷跑出来,我难免惊恐。我被盘问,说是找温副司令,一个电话打进去了。好长一会儿,回话说,温玉成副司令到北京开会了,先把信留下,在这里再等一等,有人出来见你。焦虑中正巧碰上军区青年部张部长路过,我曾是军区树立的学毛选和五好战士代表,自然很熟悉。他说,怎么会呢,温副司令刚才还在给我们开会呢。我疑窦丛生,不安起来,既然没有结果,还是快回去的好,但我已经走不了了。“嘎”的一声,一辆吉普停下来,保卫部门来人了。在审问我的过程中,我听出来,是军区打电话到团里,说你们的兵都跑到温副司令家里闹事了,被截在军区司令部门口,要团里马上来人处理。我不想去设想这和温玉成副司令是否有直接的联系,我只见过他一面,他来检查工作,团里汇报我是刺杀标兵、特等射手,他说:“先叫他当个班长试试!”
这件事发生后,再把我留在支左部队显然是不合适的。我被遣送去到罗浮山脚下的留守处农场,开始了一年的喂猪生涯。砍树劈柴,清理粪便,下河捞水浮莲,这是猪能够吃的东西。在烈日下,我赤膊挥动着利斧。我的功力渐长,一斧子下去,碗口粗的木头保准会一劈两半飞出好远,好个一分为二,清脆而且利落,路过的老乡常会有喝彩声。看着罗浮山飞溅的瀑布,看着连绵起伏的重峦叠嶂,震耳欲聋的“文革”口号、头晕目眩的红色海洋,渐渐离我远去。
弟弟从东北插队的边远山村里来信了,他写道,《基度山恩仇记》里有这样一句话:“当上帝还没有把他的全部秘密揭示给我们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只包含在这四个字里:‘等待’与‘希望’。”
留着我这样的人,终究是个麻烦。一年后,在坦克团指导员和两个战士的护送下,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望着窗外飞驶而去的南国风光,回想4年前父亲在原子弹试验的戈壁滩上给我写下的话:“到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热泪盈眶。
真像是一场梦啊。
一个背包,一个挎包,和当年离家的时候一样。
当我猛地出现在妈妈面前时,她先是一愣,随即泪如雨下。我紧紧地抱住她,很久她才说出话来:“怎么这么瘦啊?”
“爸爸,他在哪?”
妈妈打开抽屉,摸索了一会儿,打开了一个手帕包。啊!那是一块劳莱克斯表。我当然认识!这是父亲的!它光彩夺目,名贵、脱俗,是表中之王!
妈妈告诉我,爸爸在被抓走前的一些时候,有一天又被拉出去批斗,他走出家门又折回来,把手腕上的这块表褪下来说:“留给阿胜吧。”
啊,父亲,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