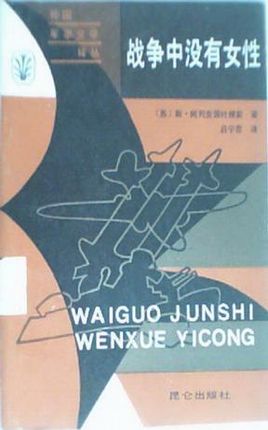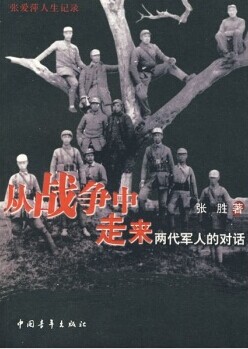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老总、张鼎丞等领导来看望父亲,走后,妈妈听见他们询问医生,议论的声音很低,断断续续地,但妈妈还是隐约听到了“……废了”两个字。
她的奶水就在这一刻再也没有了,从此,我再没吃过妈妈的奶。现实是残酷的,但她必须和他一起承担。
1946年6月下旬,大规模内战爆发。8月9日,随着泗县之战失利,淮北形势急转直下。9月19日,淮安被占。不久,两淮丢失。
在这之前,粟裕和父亲这两个华中军区的第一和第二副司令,曾有过一场关于作战方针的讨论。他们两个共同之处是都不同意放弃华中,分歧是坚守华中,究竟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粟裕认为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运动战打击北犯之敌,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为日后在华中立足奠定基础。父亲则认为,在来势凶猛的敌人面前,不应匆忙应战,应以有限规模的运动战结合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做好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长期准备。华中江河湖汊,四通八达,完全可以与敌周旋,避其锋芒后,坐待战机。
现在,究竟谁的意见更为合理,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父亲在病榻上收到了9纵政治部主任张震寰和宣传部长赵易亚的信,信上说,两淮丢失了。据有的老同志回忆,当父亲读到信中叙述的两淮失守与淮北失陷后,我军民撤退时的慌乱与匆忙,以及地主还乡团残害根据地群众的惨状,他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我没有向父亲核实过这个细节。他是在为曾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牺牲的这块土地的丢失而伤心呢,还是在为自己这时多么的无奈而悲泣呢?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只说了一句话:“粟裕同志在苏中七战七捷的消息传来,我真为他高兴。可我每天只是头痛,痛得像裂开了一样……”我找到他当时写的诗《捷报》:“七战连捷敌难逃,运动战和游击战,胜券稳操。”日期是8月1日在淮安。他在病痛的折磨中,为战友七战七捷的胜利而祝贺,同时也为无法亲自去实践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主张而耿耿。
两淮失守后,华中党政机关后勤人员从沭阳方向撤至山东,地方人员因撤退不及遭受很大损失。我们也随父亲转移到临沂。不久,临沂也告急,组织上又决定父亲转道大连养伤。
这本不是他该去的地方!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面前的是关乎着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如果说,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还只是排练;到了解放战争,则是大戏开场了。经历了在分散的根据地上游击作战的共产党军队,今天,他们将整合起来,以野战军为单位,与这个18年的宿敌,进行最后的决战了。一场大兵团会战的宏伟剧幕已经徐徐拉开,刚刚被提拔到战区领导岗位上的他,本来是可以一展风采的,而现在,在大战来临之际,他不得不与老弱病残为伍,颠沛在后撤的路上。这对他,不仅是焦躁和苦闷,简直是一种惩罚,命运的惩罚!
这次负伤给父亲带来了终生的遗憾。整个解放战争辉煌的战史上,消失了张爱萍的名字。皖东北的大地啊,伴随着我的降临,带给父亲的却是灾难,难道冥冥之中,真的会有什么暗示吗?
4 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
在浩浩荡荡北撤的人流中,有一副担架,抬着一个昏昏欲睡的伤员,他头上缠满了绷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伴随他的是他的妻子,怀里抱着的是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8名警卫战士护送着,他们走得很慢很慢,匆匆而过的士兵们都好奇地回过身来,当他们认出担架上这个双目紧闭、昏睡不醒的人是他们的司令员时,他们向他致以军礼,然后又匆匆赶路了。拥挤的道路渐渐变得空旷,他们翻山越岭,跨河涉水,蹒跚而行,曾几何时,这个在江淮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此时只能躺在担架上听天由命了。
淮安丢失后,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这个词了)先自蒙阴到临沂,然后过沂水、诸城、莱阳、烟台,从蓬莱登船,到大连。这一带,我后来在总参工作时,曾多次组织过实兵演习。这是当年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战场,其实地形并不十分复杂,从苏北平原到鲁中南山区,仍属丘陵地,地势虽多有起伏,但并不险恶,用现代作战的理念来看,和我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并不是理想的战场。为此,我惊叹当年华东野战军居然能在这里纵横驰骋、决战决胜,消灭了蒋介石正规军和各种武装247万之多。每念及此,大有愧对先人之感。
妈妈和父亲同命运。
父亲负伤后,组织上明确告诉妈妈,把你的工作交代一下,好好照顾爱萍同志,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你今后的工作。妈妈回忆说:“听那口气,好像你爸爸已经永远是个需要照顾的残废人了。我真的不敢去想……”此时的父亲不过35岁,妈妈只有26岁,都是人生最灿烂的年龄。妈妈18岁离开了豪门之家,抱着“国家有难,巾帼不让须眉”的人生志向投身抗日洪流。当翻天覆地的时代大变革到来时,命运却对他们作出了如此残酷的判决,他们当真是会绝望的啊!
去大连这一路,她又要照顾担架上情绪不安的父亲,又要照看嗷嗷待哺不满周岁的孩子。父亲负伤后,妈妈一急之下没了奶水,我经常在路上饿得哇哇乱哭。走了一天的路,宿营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老乡借口大锅,熬米粉糊糊给我吃。米粉是她自己做的,先把米烤焦了,碾成粉,吃时加水搅拌熬成糊糊。妈妈说,我那时总像疯了似的,两个勺子都喂不过来。
从临沂往北是沂水,过了沂水就是敌占区,沿途有敌人的封锁线,碉堡、炮楼处处可见,鬼子和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枪,等待蒋介石政府的接受和改编。听爸妈说,一路上大多是昼伏夜行。过封锁钱的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伸手不见五指,为了肃静,连马蹄子都用棉布和麻袋片包起来。人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在这样寂静的夜晚,一声哭啼,引来了敌人,8个人的小分队是不堪一击的,何况沿途还有许多跟上来逃难的老乡呢。为了让我熟睡,行前特意用米糊子把我喂饱了。但临近村头时,我突然号啕大哭……真是鬼使神差!
每当父母讲起这段经历时,总会补上一句:“你啊!从小就让人闹心。”这大概也是种暗示,怪不得我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视为是个不安定因素。
走了一夜的路,住下来,大家都能休息,只有妈妈忙着号房子、筹粮,与当地党的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再就是照顾爸爸和我,弄饭、换药、洗洗涮涮的。还要计划明天的行军路线,甚至给警卫班上课,给个别战士做思想工作。妈妈说我真是她的克星,夜里行军骑马抱着你,一颠就睡着了,白天大家睡了你就闹。为了怕我吵闹,总是抱着你到村头去哄,可你精神大着呢。她说,那时真累啊,一倒头就睡着了,就是在老百姓半尺宽的长条凳上也能美美地睡上一觉。睡觉时怕我乱爬,就像拴小狗似的,用绑腿布一头拴住我的脚脖子,另一头拴在凳腿上。
妈妈说,那时她什么愿望都没有,唯一的就是想睡个安稳觉。就这样,也不知熬了多久,突然有一天,她一点觉也没有了,困乏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按现代医学的说法,大脑精神和情绪控制的记忆产生了,这就是失眠。直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每晚她还是离不开安眠药。
战争中的女人啊!
大连,是座美丽的如梦幻般的城市,异国风情的小屋,栉鳞彼伏、依山傍水,比比皆是。在领略了幽美如画的海天山色之后,日俄战争遗留的碉堡、堑壕和街区深巷里破烂不堪、低矮潮湿的小窝棚,以及随处可见的和服、俄文招牌,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曾经有过的殖民地的屈辱历史。
这是一座极特殊的城市,它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取向也是多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连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了中国,但实际上为苏联军队所占领。他们也奉行国际主义,同情中国共产党,暗中赞助并提供便利;但不允许中共进行公开的活动。应该说和平已经来到了这里,但就像所有经历了战乱的城市一样,秩序混乱,物资匮乏,粮食、药品、燃料,弥足珍贵。电力不足,电灯的灯丝总是红红的,像是烛火,在黑暗中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妈妈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一个小小的电炉,在微弱的电压下,一壶水足足要烧两小时。临来的时候,组织上给了些大洋。随着战事越来越扩大,一些伤病员和领导干部的家属也陆续转移到大连,生活成了最大的问题。妈妈把这些大洋兑换成卢布,分给了大家。
父亲除了昏睡就是抱个收音机不放,是那种用干电池的像电台一样的军用收发报机,缴获日本鬼子的,一天到晚地听有关战事的进展。他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经常拒绝吃饭,成天不说一句话。后来,我听说脑外伤病人的特征就是脾气、情绪异常的焦躁和暴烈。总得要补充营养啊,妈妈是整天去弄吃的。有一次,好不容易搞了点牛奶,热好了端上来,好劝歹劝,不料父亲手一挥,就将牛奶打翻在地上,恶狠狠地说:“要吃你吃!”妈妈说,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默默地流泪。她说:“一个病人,你能拿他怎么办?”
“你爸爸总是头疼,他会死死地抱住自己的脑袋说,头要裂开了啊!疼得没办法时,就使劲往墙上撞……他整夜整夜没法入睡,全身疼痛,我就给他揉。祸不单行,你爸又得了急性盲肠炎。手术是个日本医生给做的,你想怎么能不让人揪心?可有什么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看着他动刀子。我累一点没关系,就是担心。你想,四肢、五官残了,别人还可以帮一下,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脑子要是坏了,那可全完了,真就是个废人了。”
妈妈每到医院给爸爸送水送饭,把我先喂饱了,拴在桌子腿上。等她回来,我都尿得湿透了。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日子。
妈妈说,在和爸爸的一次争执后,她冲出家门。她找到刘尹兰大姐,诉说内心的苦闷,求大姐帮她找份工作。她还年轻,她要革命,她不能把自己的一生糊里糊涂地葬送在这毫无生气的日子里。刘尹兰当时负责铁路医院的工作,作为女人,她能理解,说你就来我这里吧。妈妈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亲了亲我,就带上了门,这一去,她真的不想再回来了。
她能走得出去吗?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当她面对一个躺在床上受伤的丈夫,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时,她能迈出这一步吗?在寒风中,除了无助的失声痛哭外,除了默默的叹息自己的命运外,她还能做什么呢?妈妈说,她就这样,一个人沿着岭前的那条小路走了很久很久,前面就是大海……
从此,她就不再去想了,不再去想未来,不再去回忆少女时一切美好的梦境。她将她的青春和对未来的憧憬,“葬送”在陪伴病中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的漫长的日子里了。
当我长大以后,当我也恋爱,当我也有了爱我的女人的时候,我才慢慢地搞懂,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纯为什么会离开他。据杨纯的密友,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回忆,她们之间就杨纯的第一次婚姻曾有过一段对话:
“我的婚姻解体了。”黑暗中,杨纯静静地说。“为什么呢?”唐棣华轻声地问,她忽然间为自己忽略了好友的情绪而自责。“因为我还没有学会为他做出牺牲。”……(注:选自《一个女兵眼中的黄克诚将军》199页)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让爱他的女人为他做出牺牲的;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甘于为她们所爱的男人去牺牲的。
这应该是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呢?
妈妈比爸爸小9岁。爸爸出身在四川东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家境并非富庶,他种过地,放过牛。
可妈妈就不一样了,浙江宁波镇海的小港李家,可是个了不起的名门望族。到了我外公那代,正是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中国大门的时代,伴随而来的是西学东渐。外公李善祥,性格开朗,敢闯敢干,思想新潮。年轻时接触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是一个实业救国派人士。小时的娇宠,使他养成吸食大烟的恶习,参加革命后,决心戒烟救国。他把自己捆在床上,责令家人无论怎样都不许松绑。现在人们常说戒烟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我外公就是登上了这个青天,戒掉了大烟。我外婆出身贫寒,但我外公破除门第,硬是迎娶了她。外婆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作风,真诚善良、助人好施的待人态度,立马引起了李家长幼上下的尊重。她的到来,在这钟鸣鼎食之家,犹如刮进一股清新的风。外公当年是镇海地方长官,为破除旧习树立新风,自己剪掉辫子,让外婆剪成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