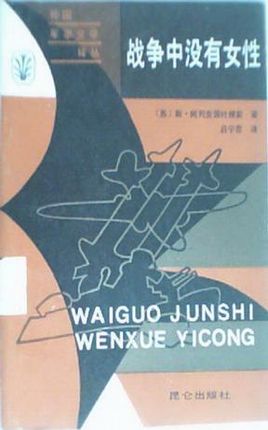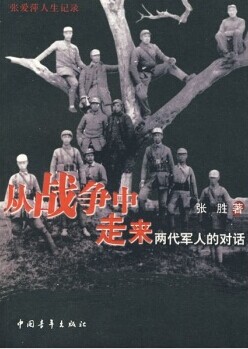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黄克诚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华中局会议上说,不是我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军部对反摩擦、反扫荡作战指导原则有问题,要加以纠正。黄认为曹甸战役与黄桥战役不同,不宜打。黄桥战役是自卫反击,曹甸顽军则已退守,不能算是有理;黄桥是运动歼敌,而曹甸是攻坚,不能算是有利;黄桥结束不到两个月,再打曹甸,不能算是有节。
我问父亲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刘、陈要打曹甸,要我们配合打车桥,进一步压韩德勤。黄不干,认为攻坚不值得,伤亡太大。黄直接给八路军总部彭德怀那里发电请示,引起刘、陈的不满,彭也不好干预,要黄还是听刘、陈的。最后,还是没有打下来,伤亡较大,从此,彼此就有不同意见了。”
也有些研究者认为,黄克诚狠抓根据地建设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巩固的政权是难以抗击强大于我数倍之敌的。但在毗邻敌心脏地区,造成过大的声势,尤其是在根据地的敌我态势没有调整、战场建设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急于扩大对敌占区文化界、知识界的统战影响,势必过早暴露自己,造成被动。
这些分歧,一直延续到15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和彭德怀被打为反党集团。在揭发批判的热潮中,华中抗战的老账又被翻出来了。除了重提黄克诚在作战中一贯消极、右倾保守外,还提到了这次盐阜地区反扫荡,说黄是放弃指挥,退却逃跑,化装隐蔽。上纲到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王明路线,黄克诚是一个言行不一、不向党交心的伪君子。
在3师工作过的许多同志认为,黄克诚同志是掌握了反扫荡的全局的,将作战交由张爱萍副师长机断指挥。在敌反扫荡前,从最坏处准备,跳出敌包围圈,以利前线指挥员放手指挥。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黄一直没有离开过盐阜地区。
父亲说:“工作中有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把这些分歧带入政治领域,是错误的,有害的。党应该吸取这个教训。”父亲顶着高压,在黄克诚庐山落难时保持着对他客观的评价。他说:“我永远不会去做这种卑鄙的事情。”
黄克诚岂能不明白呢?他在《自述》中写道:“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要表现一下。也有几个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黄克诚是条硬汉。“文革”中,专案组知道他当年受过华中局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他揭发当时的领导人。他说:“我们是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有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他们叛党。”
难道历史真的是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姑娘吗?革命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历史,战争年代不能回避,现在回忆历史就更用不着回避。
3 我是他的“克星”
1945年是让历史难忘的一年。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句号;终极武器原子弹,在日本岛国炸响,十数万天皇的臣民,在几秒钟里化成了灰烬,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雅尔塔协议签署,由此划定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冷战格局。
这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同样是辉煌的。经过整整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是整整一代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为代价,留给后人的一份遗产。这次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从此由衰败走向振兴。
我,也在这一年降临到人间。
妈妈说,生我的那天,月亮像个银盘,特别亮,亮得都有点儿凄惨,秋风习习,吹过空旷的田野,将世间的一切都吹得似有似无一般。
是难产。整整折腾了一天,大人孩子像过了趟鬼门关。妈妈说,你生下来不会哭,胎死腹中?也是命不该绝,正巧有个妇产科的医生从上海来根据地,就住在隔壁。她听说有新四军家属要生孩子,怎么就听不见动静呢?是医生的天职吧,过来一看,说是被羊水噎住了。吩咐打两盆水来,一盆热的,一盆凉的,就这么来回地浸泡,再拎起双脚打屁股,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
父亲是在我出生的两个星期后才见到我的。国民党李品仙部为夺占徐州,由蚌埠星夜北上。父亲任淮北我军前敌总指挥,4纵在王必成率领下为右路,9纵在张震率领下为左路,阻击来犯之敌,发起了津浦路破袭作战。大战在即,父亲在去前线之前,兴冲冲地赶来看了妈妈和我一眼。
妈妈回忆说:“你爸看了一眼说,丑东西!又说,再丑也是我儿子!就急匆匆地走了……”有一种说法,出生的磨难,预示着人生的艰辛与坎坷。也不知是指大人还是孩子。路加福音,……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我来的真不是时候。父亲这一走,可就是从生死界上擦肩而过了。
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当外部的压力消失的时候,国内两大政党、两个阶级的斗争便骤然升温,内战的烟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毛泽东发表了他那段为国人熟悉的精彩讲演:“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的话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意志和立场,但仅仅一个月后,1945年9月17日,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就致电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提出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下,具体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毛泽东立即回电赞同。面对400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共产党是没有力量和国民党硬碰硬的。他们主动放弃了南方8个解放区,做出收缩南部,巩固华北、山东、华中,控制热察的决定;不到一个月,又进一步明确为放弃华东、华中、中原、华北,只坚守山东、陕甘。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集中力量抢占东北。今天看来,在两大政党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中,共产党人的这第一脚,充满了狡黠和智慧。刘少奇也因此以他的雄才大略又一次赢得了自己在党内的声望。
首当其冲的又是华中。
国民党17个军约50万人分批向华东解放区推进,在夺占南京、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后,沿津浦路北上,直逼华北、东北。
华中局一分为二;新四军一分为二。新四军军部移往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留下的另组成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黄克诚率3师抢占东北走了;罗炳辉的2师和父亲统领的4师,一分为二。2师之4、5旅,连同整个7师都调往山东。4师9旅调山东,4师11、12旅和2师6旅留在淮北。粟裕、叶飞的1师留在苏北。新四军的抗日健儿们,8万北上,5万坚守华中。
陈毅、黄克诚走了,而父亲和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留下来了。中央来电“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父亲和粟裕被分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华中军区开始叫苏皖军区,寓意着苏中和淮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人联手保卫华中,准备迎接国民党从大后方调来的百万大军。
按父亲自己的说法,抗日战争是他步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成熟了,他不再只是个猛打猛冲的拼命三郎了,他的战略头脑、指挥才能、坚韧吃苦的品格和大刀阔斧的作风,逐渐为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所认同,开始有人欣赏他了。
彭雪枫牺牲后,由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华中局曾动议从八路军中选派干部,但最终中央议定是由父亲来接替。他独闯皖东北的战略眼光和胆识;与盛子瑾统战中展现出的政治斗争的谋略;创建九旅的建军治军能力;以及在盐阜区反扫荡中所表现出的指挥艺术和英勇牺牲精神,这些业绩,都成为举荐他担任这一职位的重要筹码。当然,他长期在江淮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大战来临之际,考虑到华中腹地由苏、皖两个战役方向构成,中央又委以他华中军区副司令的重任,和粟裕分别负责苏北和淮北的对敌斗争。他似乎走到了他的同辈们之前,成为新四军抗战初期旅团一级干部中的佼佼者。父亲有理由接受这一切,因为,这不是靠人际关系,不是靠投其所好,不是靠压抑自己的个性换得的;而是靠浴血奋战、靠不计名利、靠张扬自己的个性赢得的。现在,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幅的主要方向上,掩护华东我军的战略转移和展开,面对百万敌军压境,站在抗击国民党进攻的最前线,应该说,这既是中央对他的器重,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不知为什么,父亲总好像不愿意多谈他这一段的历史。但我还是从当年他留下的诗篇中,窥探到他的心态。他写到:“抗风暴,挽狂澜,胆气豪……手挚龙泉剑,腰斩长蛇津浦。”
在重大的挑战面前,他的人生,理应更加精彩。
当时华中军区驻地在淮安,周恩来老家。从淮安出发到津浦路前线,父亲的习惯是骑马,红军时他任过军委骑兵团团长,骑术、劈刀、马上射击都是挺在行的。这时部队已经有卡车了,大家都建议汽车要快得多,他犹豫了一下,就改坐汽车吧……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汽车当然要比马快。是缴获日本人的那种大卡车,他坐在驾驶舱,参谋等随行人员在后面车厢里。你想,缴获的车已经破旧,当时又没有修理厂,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赶路。离前线不远了,遇到老百姓支前的运输队,马车、排子车、独轮车,把个路堵得严严实实。汽车过不去,天又下着雨,走了一天了,父亲说,既然要等,不如下去搞些吃的东西来吧。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回身要向后面车厢里的人交代些什么……车缓慢地向后滑动,旁边刚好有一堵墙,他的话音还没落,头就被夹在车门和墙之间了……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为什么不骑马?为什么要坐这辆破车?为什么不冲过去,要停在这个鬼地方?但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命!
据在现场的作战科长孙公飞回忆:“我听到首长在前面驾驶舱讲话,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探头一看,啊!可不得了了,血从司令员被挤住的头上涌出来……”
慌乱中有人说,不能倒车,一发动,车身一震,脑袋就挤碎了,只能缓缓地把车推开。人是当时就昏死过去了,血从眉骨处汩汩流出。
华中军区后勤卫生部的王广胜当时在场,他说:“头盖骨从眉骨处裂开,或许是他戴的帽子救了他,帽檐折下来垫了一下。首长醒来后就开始大口吐血……”
我问父亲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细节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醒过来后,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天旋地转的。”
很痛吗?我问。
“没有十分的疼痛。我觉得自己还行,我还是明白的。战斗马上要打响了,让部队知道了,可是大忌。淮北我熟得很,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作战科长孙公飞回忆:“我看首长渐渐有些苏醒了,就说,要赶快向陈毅司令员和华中局报告。他双眼紧闭,好像听到了,手指动了动,我知道他不许我们说。”“他一直这样躺在担架上,眼睛睁不开了,电报由我念。他不需要地图,他在这里创建了根据地,他对这一带太熟悉了。”
卫生部长王广胜说:“首长是颅脑损伤和严重脑震荡,我警告他,一定要静卧,不能再这么干了,否则要留下后遗症的。”
妈妈说:“我听到前方传来的消息,就到华中局去问个究竟。邓老(邓子恢)安慰我说,估计不会太严重的,前线说,他一直还在指挥作战嘛。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周后,战斗结束。父亲强撑着参加了庆功大会,他要给部队讲几句话,他刚走上主席台,就一头栽下去了……
这时上面的领导同志都还不清楚父亲的伤势,从来往电报看,一切都正常。战斗结束后,陈老总要父亲立即赶赴淮安,参加军调小组,说是美方的雷克上校已经到了。一见面,吓了一跳,陈老总叹道:“咋子搞的嘛?受了如此重伤,咋还呆在战场上!”
妈妈说:“无怪陈老总都吓了一跳,我见到他时,你爸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脑袋肿得好大,都认不出原样了。你爸这个人啊,别人的话都不听。脑震荡的人是不能再受震动的,他不要战士们受累抬他,坚持要把担架放在车上,那时都是泥泞路,一路颠簸下来,哪还有好的?”
陈老总、张鼎丞等领导来看望父亲,走后,妈妈听见他们询问医生,议论的声音很低,断断续续地,但妈妈还是隐约听到了“……废了”两个字。
她的奶水就在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