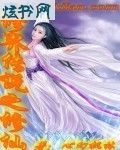іВ¶АРгИ«ҙ«-өЪ97ХВ
°ҙјьЕМЙП·ҪПтјь Ўы »т Ўъ ҝЙҝмЛЩЙППВ·ӯТіЈ¬°ҙјьЕМЙПөД Enter јьҝЙ»ШөҪұҫКйДҝВјТіЈ¬°ҙјьЕМЙП·ҪПтјь Ўь ҝЙ»ШөҪұҫТі¶ҘІҝЈЎ
ЎӘЎӘЎӘЎӘОҙФД¶БНкЈҝјУИлКйЗ©ТСұгПВҙОјМРшФД¶БЈЎ
БнТ»·ҪГжЈ¬ПөҪyөШЕъЕРЎёОТӮғөДФ’ЕЙЎ№Ј¬ЦёЖд1929Дк9ФВөЪ¶юҙОҙъұнҙу•юНЁЯ^өДЎёХюЦОӣQЧh°ёЎ№ЯЎ®ұіНРВеЛ№»щөДЎёЦРҮш№І®aЦчБx·ҙҢҰЕЙХюҫVЎ№Ј¬ЕcК·М«БЦЕЙУ^ьcТ»ҳУЎЈм¶КЗРыҒСЎёҝӮҺЦЎ№ЎёФЪАнХ“ЙПәНХюЦОЙПТСҪӣЛАНцЎ№Ј»ЎёОТӮғәНЯ@Р©·ЦЧУҹoҪzәБөДХюЦОөДәНҪMҝ—өДкPӮSЈ¬Я@Р©·ЦЧУӣЈ§УРФӯ„tЈ¬·ҙҸНҹoіЈЈ¬ҒЧЧЕоIҢ§өШО»Ц»УРОЫИи·ҙҢҰЕЙөДЖмҺГЈ¬“pүД·ҙҢҰЕЙөДРЕСцЎЈЦРҮшөД·ҙҢҰЕЙҪMҝ—І»ғHКЗФЪЕcК·ҙуБЦЦчБxҠ^фYЦРҲFҪYРОіЙЈ¬¶шЗТнҡҸДЧФјәөДк ОйЦРЦріцЯ@Р©К·М«БЦөДЧЯ№·ЎЈЎ№
ФЪЎ¶ёжН¬Цҫ•шЎ·ЙПәһГыөДИЛлSббУЦұ»ЦР№Ій_іэіцьhЎЈУРИЛУГөДКЗјЩГыЈ¬ИзЎёАи°ЧВьЎ№јҙАиІКЙҸЈ¬ЯҖУРНхОДФӘөДЖЮЧУИ~УўЎЈ1930Дк5ФВ7ИХөДЎ¶јtЖмЎ·ЙПөЗіцБЛЦР№ІЦРСлҪMҝ—ІҝЦВАиІКЙҸЎўИ~УўөДРЕЈәЎёДгӮғФSҫГК§ИҘБЛЕcьhөДкPӮSЈ¬І»ЧФ„УөД·eҳOөДХТьhЈ¬Я@КЗТ»·NУРТвлxй_ьhөДұн¬FЈ¬ЦРСлІ»ЦӘДгӮғЧЎФЪәОМҺЈ¬ҹo·ЁЕcДгӮғ°lЙъкPӮSЈ¬ПЈНыДгӮғЛЩФO·ЁҢўЧФјәөДөШЦ·Ҫ»ҒнЈ¬·с„tЯ@КЗУРТвлxьhЈ¬ьhФЪҪMҝ—ЙП‘ӘҪoТФЧоббөДМҺ·ЦЎЈЎ№Я@ұнГчЈ¬ЦР№І®”•rЗеіэьhғИНРЕЙ·ЦЧУөДЯ„УКЗПа®”ҲФӣQәНҸШөЧөДЎЈ
ё»УР‘т„ЎРФөДКЗЈ¬ЎёОТӮғөДФ’ЕЙЎ№өДЎёҝӮҺЦЎ№Ј¬ТІЧчіцБЛТ»ПөБРй_іэӣQ¶ЁЎЈЎёК®ФВЙзЎ№іЙБўббЈ¬ЛыӮғЧlШҹЎё·ҙёпГьҷC•юЦчБx·ҙҢҰЕЙ„ўИКмoөИИЛПтОТӮғЎӘЎӘ·ҙҢҰЕЙҮАЦШЯM№ҘЎ№Ј¬ҒKҢў„ўИКмoЎўНхОДФӘөИИЛй_іэЎЈЈ§18Ј§Н¬•rЈ¬ғИІҝФЪҢҰҙэкҗӘҡРгЕЙҶ–оЈэЙПЈ¬ТІ°lЙъ·ЦБСЎЈУЙм¶К·МЖЎў…^·јЎўҸҲМШЦчҸҲФЪЎёИэӮҖ—lјюЎ№ПВҝЙТФОьКХкҗӘҡРгЕЙЈ¬БәҺЦҶМ№Ҙ“фК·МЖөИЎёКЬБЛкҗӘҡРгҪреXКХЩIЎ№Ј¬Йҝ„УЎёҸV–ЈьКЎҺЦ•юКРҺЦ•юёчЦ§ІҝёчҪMйLВ“ПҜ•юЧhЎ№Ң‘РЕТӘГЈыЈәЎёКДЛАІ»Н¬кҗӘҡРгЕЙНЧ…fЈ¬·с„tПгёЫ…^И«уwН¬ЦҫГ“лx·ҙҢҰЕЙЎ№Ј§19Ј§ЈЁ®”•rПгёЫНРЕЙҪMҝ—ҢЩм¶ҸV–ЈьКЎҺЦКВ•юоIҢ§ЎӘЎӘТэХЯЈ©ЎЈБәЯҖПҜ’ФФ“ЕЙЕcҮшғИНвНЁРЕөШЦ·Ј¬ҪШБфНвҮшјДҒнөДОДјюЈ¬”аҪ^Ф“ЕЙөДҪӣқъҒнФҙЎЈһйҙЛЈ¬ЎёҝӮҺЦЎ№ЧчіцБЛй_іэБәҺЦҶМәНҸҲҺҹөДӣQЧhЎЈЈ§20Ј§ббҒнТтһй…^·јФЪ№ӨИЛЯ„УЦРұ»І¶Ј¬ҒKІ»ҫГЛАм¶ЙПәЈдоәУӣЬӘzЦРЈ¬БәҺЦҶМУЦ»ШҒніЙһйЎёОТӮғөДФ’ЕЙЎ№өДоIРдЎЈ
„ўИКмoЕcЎёК®ФВЙзЎ№өДәПЧчТІІ»йLҫГЎЈТтһйЛыФЪЕъЕРкҗӘҡРг•rЈ¬ҲФіЦХJһй1923ДкҮш№ІәПЧч•rЛыәНҸҲҮш cЦчҸҲөДЎёјУИлҮшГсьh¶шҢҰҮшГсьhөЎ№ӨКЗІј –КІҫSҝЛВ·ҫҖЎ№өДУ^ьcЈ¬м¶1930Дк7ФВ19ИХұ»ЎёК®ФВЙзЎ№й_іэЎЈЈ§21Ј§
ЕcҙЛН¬•rЈ¬ФЪкҗӘҡРгЕЙІ»ҪУКЬЎёОТӮғөДФ’ЕЙЎ№өДИэӮҖ—lјюҒKЧФРРіЙБўЎёҹo®aХЯЙзЎ№РЎҪMҝ—Ј¬іц°жҷCкPҲуЎ¶ҹo®aХЯЎ·ббЈ¬ЎёҝӮҺЦЎ№јУҸҠБЛҢҰкҗӘҡРгөДЕъЕРЎЈ1930Дк7ФВЈ¬°lұнБЛЎ¶Ҫoҹo®aХЯЙзТ»·в№«й_өДРЕЎ·Ј¬ПөҪyҮА…–өШЕъЕРБЛкҗӘҡРгөДБщҙуеeХЎ®ИзПВЈә
ЈЁТ»Ј©ЎёІ»УВёТөДіРХJЧФјәФЪТ»ҫЕ¶юОеЁC¶юЖЯДкёпГьЦРЛщ·ёөДҷC•юЦчБxеeХЎ®Ў№
ЈЁ¶юЈ©ЎёХЎ®ҮшХюІЯөДеeХЎ®Ў№ЈЁЦР–ЈьВ·Ҷ–оЈэЈ©
ЈЁИэЈ©МбіцЎёҹo®aлAјүЕcШҡЮrҢЈХюЎ№Ј¬ҢҚлHЙПКЗЎё№ӨЮrГсЦчҢЈХюЎ№
ЈЁЛДЈ©ЎёҢҰм¶ИәұҠЯ„УПыҳOөДғAПтЎ№
ЈЁОеЈ©Ўё№АУӢДҝЗ°•rҫЦөДеeХЎ®Ў№
ЈЁБщЈ©ЎёҢҰЮrГсҶ–оЈэҝЙҗuөД‘B¶ИЎ№ЈЁЎёјtЬҠҫНКЗНБ·ЛЎ№Ј¬ӣЈ§УР„ЩАыЗ°НҫЈ©
ҸДТФЙПЎёОТӮғөДФ’ЕЙЎ№ЕъЕРкҗӘҡРгөДБщҙуеeХЎ®ҒнҝҙЈ¬ЛыӮғЕcЦР№ІЛщЦ^ЧуғAЎёГӨ„УЦчБxЎ№еeХЎ®өДАнХ“ЎўВ·ҫҖЎў·ҪбҳЎўХюІЯәНІЯВФ·Ҫ·ЁЙПЈ¬ҢҚФЪӣЈ§УРЙхьNҙуөД…^„eЎЈНРЕЙғИІҝЦ®йgөДфY ҺЈ¬ЖдТвҒKІ»ФЪёпГьВ·ҫҖөД…^„eЈ¬¶шФЪм¶іЛҙуёпГьК§”ЎөДОЈҷCЈ¬ЖуҲDИЎҙъЦР№ІөДоIҢ§өШО»Ј¬ХэИзНРВеЛ№»щПлИЎҙъК·М«БЦЎўНРЕЙҮшлHИЎҙъөЪИэҮшлHТ»ҳУЈ¬І»Я^КЗҷаО»Ц® ҺЎЈЯ@ТІҸДёщұҫЙПФЈ§¶ЁБЛЛыӮғІ»ҝЙДЬУР°lХ№әН„ЩАыөДЗ°НҫЎЈ
иbм¶ТФЙПёчРЎҪMҝ—Ц®йgЎё»м‘рЎ№өДЗйӣrЈ¬БнНвТ»Р©ДӘЛ№ҝЖ»ШҮшббЯҖФЪУОлx о‘BөДНРЕЙҢWЙъУЦФЪ№І®aьhәНТСУРөДНРЕЙҪMҝ—Ц®НвЈ¬іЙБўБЛөЪЛДӮҖНРЕЙРЎҪMҝ—Ј¬Я@ҫНКЗЪwқъЎў„ўШ·өИЖЯИЛҪMҝ—өДЎё‘рфYЙзЎ№Ј¬ҷCкPҲ󡶑рфYЎ·ЎЈкҗӘҡРгЕЙФш ҺИЎЛыӮғВ“әПЈ¬һйҙЛЈ¬ҺЧҙОГШГЬ•юТҠЪwқъЎЈЪwқъ»Ш‘ӣТҠГж•rөДУЎПу•rЈ¬К®·ЦёРҡUёпГьҡqФВөДДҘҫҡҢҰкҗФміЙөДЙоҝМЧғ»ҜЎЈЛыХfЈә
өЪТ»ҙОТҠГжКЗФЪЙПәЈМб»@ҳтТьҢ’ЧЎМҺЈ¬°ҙХХјs¶ЁөД°шНн•r·ЦЈ¬ОТөҪббІ»ҫГЈ¬кҗӘҡРгТІҒнБЛЈ¬Чш¶ЁббЈ¬ЛыҸД‘ССYМНіцТ»ӮҖьI°ьЎЈОТҶ–ЈәЎёАППИЙъЈ¬ДгЯҖӣЈ§УРУГЯ^НнпҲЈҝЎ№ЛыХfЈ¬ЛыйLЖЪәҰОёІЎЈ¬ҪьҒнУИЙхЈ¬ГҝМмЦ»ДЬТФьI°ьідрҮЎЈОТҝҙЛылmИ»әҰОёІЎЈ¬ө«ҫ«ЙсЕcОТПлПсөДІ»Н¬Ј¬ОТУXөГЛыҹбЗй¶шУЦәНМ@Ј¬Я@әНОТТФЗ°ТҠЛы•rҙуІ»ПаН¬ЎЈФЪҙуёпГьЖЪйgЈ¬ОТЗ°ббТҠЯ^ЛыИэҙОЈәөЪТ»ҙОКЗФЪТ»ҫЕ¶юОеДкТ»ФВөЪЛДҙОьhҙъұнҙу•юЈ¬ОТБРПҜ•юЧhЈ¬ОТТҠЯ^ЛыЎЈөЪ¶юҙОКЗФЪТ»ҫЕ¶юОеДкОеФВПВС®Ј¬ОТөҪҸVЦЭҢҰ—оПЈйhЬҠк ЯMРРІЯ·ҙ№ӨЧч•rТҠЯ^ЛыЎЈЛыҢҰОТәНЪwЯmИ»Ўў…ЗЙЩД¬ЎўМХ№віұЛДИЛУHЧФЧчБЛЦёКҫЎЈөЪИэҙОКЗН¬ДкБщФВЦРС®Ј¬ҸV–Јь—оЈЁПЈйhЈ©„ўЈЁХреҫЈ©ЕСҒyКВјюҪвӣQббЈ¬ҸV–Јь…^ОҜ•шУӣкҗСУДкЕЙОТ»ШЙПәЈЈ¬ПтьhЦРСлҝЪо^ҲуёжКВЧғҪвӣQҪӣЯ^ј°…^ОҜ№ӨЧчЗйӣrЎЈЛыВ ббІӘИ»ҙуЕӯЈ¬ҙуБRкҗСУДкЈ¬ө№К№ОТЕӘөГІ»ЦӘЛщҙлЎЈЛщТФЛыЯ^ИҘҪoОТөДУЎПуКЗјТйLЧчпLЈ¬ҢЈҷMӘҡ”аЈ¬КўҡвБиИЛЎЈЯ@ҙОТҠГжЈ¬ДЗР©¬FПуФЪЛыЙнЙПНкИ«ПыК§БЛЎЈЈ§22Ј§
ЪwқъҪУЧЕХfЈәФЪХ„Ф’ЦРЈ¬ЛыБчВ¶іцҢҰөЪИэҮшлHөДІ»қMЎЈЛыХJһйЦРҮшёпГьК§”ЎЈ¬өЪИэҮшлHІ»ДЬӣЈ§УРШҹИОЎЈЛыЦ®І»қMКЗХfЦРҮшёпГьК§”ЎөДИ«ІҝШҹИО¶јНЖФЪЛыөДо^ЙПЈ¬ЛыКЗІ»·юҡвөДЎЈө«ЛыТІХfЯ@І»КЗ·юҡвІ»·юҡвөДҶ–оЈэЈ¬¶шКЗИзәОҸДК§”ЎЦРИЎөГҪМУ–өДҶ–оЈэЎЈ
Я@ҙОТҠГжббЈ¬ЪwқъәН„ўШ·¶юИЛФш°бөҪТьҢ’өДФәЧУғИН¬ЧЎБЛТ»ӮҖФВЧуУТЎЈФЪЯ@Т»¶О•rйgЈ¬кҗӘҡРгҒнЯ^ИэЎўЛДҙОЎЈЕнКцЦ®ЎўаҚі¬члЎўБ_қhөИИЛТІҒнЯ^Ј¬п@И»ТӘ ҺИЎЛыӮғјУИлНРкҗЕЙЎЈө«КЗЈ¬Ъwқъ°l¬FЈәкҗӘҡРгөИИЛіэБЛІ»¶ЁЖЪіцТ»УНУЎҝҜОпНвЈ¬ЎёӣЈ§УРёь¶аөД»о„УЎЈТтһйЛыӮғГҝӮҖИЛһйК№ЧФјәФЪҮшГсьh·ҙ„УҪyЦОПВДЬЙъҙжПВИҘЈ¬ҫНІ»өГІ»ТФёь¶аөД•rйgЎўёь¶аөДҫ«БҰГҰм¶ӮҖИЛөДЙъ»оЎЈҸДТьҢ’ЙнЙПҝЙТФҝҙіцЛыГҰм¶Ң‘ЧчЈ¬Йъ»оКЗПа®”ЖDҝаөДЎ№ЎЈТтҙЛЈ¬ЎёОТәН„ўШ·®”•rІ»ПләНЎәҹo®aХЯЙзЎ»өДИЛЯ^·ЦҪУҪьЈ¬ТІІ»ПлИлЛыӮғөДЎәв·Ў»Ў№ЎЈФЩҝј‘Ј§өҪЖдЛығЙЕЙөД оӣrЈ¬ЎёОТӮғТІПлөҪЯ@Р©ЕЙ„eІ»•юйLЖЪҶОӘҡҙжФЪПВИҘЈ¬І»КЗЧФЙъЧФңзЈ¬ҫНКЗ„ЭұШ•юЪ…ПтҪyТ»Ј¬ТтһйЯ@Р©ЕЙ„eЛщұ§өДН¬ҳУКЗНРВеЛ№»щөДУ^ьcЈ¬өҪ•rФЪҪyТ»ЙМХ„ЦРј°ҪyТ»ҪMҝ—ЦРОТӮғТІҝЙТФҒЧТ»О»ЦГЎ№ЎЈм¶КЗЈ¬ҫНФЪ1930Дк12ФВЈ¬В“әПНхЖҪТ»өИ№ІЖЯИЛіЙБўБЛЎё‘рфYЙзЎ№ЎЈЈ§23Ј§
Я@·NІ»”а·ЦБСөД»м‘р оӣrЈ¬ід·ЦұнГчБЛЦРҮшНРЕЙПИМмІ»ЧгәНьhЕЙЖ«ТҠөДӘM°ҜРФЈ¬®”И»Ј¬ҸДҙуөДӯhҫіҒнҝҙЈ¬ФЪ°ЧЙ«ҝЦІАПВЈ¬ЯҖДЬ№ІН¬РЕСцНРВеЛ№»щЦчБxЯ@ҳУТ»·NАнПлЈ¬ТІУРЦөөГҫҙЕеөДөШ·ҪЎЈХэИзНхОДФӘббҒн»Ш‘ӣ•rЛщҝНУ^ФuХ“өДДЗҳУЈә
¬FФЪ»Ш‘ӣЖр®”•rЕЙ„eйgөДЎёфY ҺЎ№ЗйРОЈ¬Ц»УXөГОе»Ё°ЛйTЈ¬һхҹҹХОҡвЈ»ө«ИфЧРјҡПлПлЈ¬Я@ТІХэКЗГҝТ»ӮҖХюЦОЛјПлФЪЯ„УіхЖЪөД№ІНЁ¬FПуЎЈӮҖИЛЕcЕЙ„eЖ«ТҠЈ¬әНёпГьЛјПлөДХжХІо®җҪ»ҝ—ФЪТ»ЖрЈ»•rіЈ•юұн¬FөГ·ЗіЈ№ЦХQЎЈізёЯөДЕcұ°БУөД„УҷCНщНщ•юУГН¬Т»·ҪКҪұнЯ_іцҒнЈ»¶шёчӮҖИЛЖ·ЩЈьЙПөДЩtЕcІ»РӨЈ¬®”КВЗйЯҖЦ»ПЮм¶ХfФ’»тОДЧЦЦ®•rЈ¬ТІҝӮКЗ»мПэІ»ЗеөДЎЈ№вҫНЮDПт·ҙҢҰЕЙөД„УҷCХfЈ¬ТСҪӣКЗоHІ»Т»ЦВБЛЎЈУРөДЈ¬һйБЛьhғИІ»ТЧөГЦҫЈ¬ЖуҲDөҪРВөД·ҪГжИҘХТіцВ·Ј»УРөДЈ¬ФЪ°ЧЙ«ҝЦІАөДі«ҝсЦРәҰЕВБЛёпГьЈ¬°С·ҙҢҰЕЙҝҙЧчБЛПтббНЛ…sөДТ»үKүЈьД_КҜЈ»УЦУРТ»Р©ИЛЈ¬Ц»ПлАыУГ·ҙҢҰЕЙөДёьЧуөДГыБxЈ¬ҪеТФСЪп—ЧФјәөДПыҳOЈ¬К№ЧФјәөДГ“ьhДЬРД°ІАнөГЈҝЈҝІ»Я^ғҚ№ЬУРЯ@ФS¶аұ°ұЙІ»јғөД„УҷCЈ¬ОТ…sЯҖ‘ӘФ“ХfЈ¬®”•rөДЧоҙу¶а”ө·ҙҢҰЕЙ·ЦЧУЈ¬¶јКЗУЙм¶ХжјғөДёпГь„УҷCЈ¬јҙУЙм¶ХжХПаРЕУҡВеЛ№»щкPм¶ЦРҮшёпГьөДЦчҸҲұИЦ®м¶К·ҙуБЦӮғЛщ¶ЁөДВ·ҫҖЈ¬ёь·ыәПЦРҮшёпГьөДАыТжЈ»ТтЦ®Ј¬І»оҷЛыӮғјИөГөДЎёАыТжЎ№»тТСУРөДөШО»Ј¬¶јоҠИ«РДИ«БҰөШһй·ҙҢҰЕЙфY ҺЎЈЈ§24Ј§
®”•rкҗӘҡРгЦчіЦНЁЯ^өДЎ¶ҪУКЬҮшлHОҜҶT•юҒнРЕЦ®№ІН¬ТвТҠЎӘЎӘҹo®aХЯЙзөДМб°ёЎ·Ј¬ҢҰҙЛ¬FПу„tҸДҝНУ^—lјюЙПЯMРРБЛ·ЦОцЈәЎёФЪХыӮҖ№І®aҮшлH·ЦұАлxОцөД оӣrПВЈ¬ЧуЕЙ·ҙҢҰЕЙФЪёчҮш¶јІ»ДЬТ»й_КјҫНЯ_өҪҪyТ»өДҪMҝ—Ј¬ФЪЦРҮшёьУцөҪМШ„eА§лyөДӯhҫіЎЈЦРҮш№І®aьhФЪҮшлHҷC•юЦчБxөДоIҢ§Ц®ПВЈ¬ІоІ»¶аЧФКјҫНОҙКЬөҪХжХэөДсRҝЛЛјЦчБxөДҪМУэЈ¬ЛьөДАнХ“»щөA·ЗіЈұЎИхЎЈЯ@ҙОК§”ЎЦ®ҮА…–өДҙт“фЈ¬УЦК№ьhөД»щөAНЯҪвҒKМҺФЪҳO¶ЛөД°ЧЙ«ҝЦІАЦ®ПВЈ¬ФЩјУЙПК·М«БЦЕЙ№ЩБЕЦЖ¶ИПИЖЪҢҰм¶·ҙҢҰЕЙЦ®ҳO¶ЛҹoАнөДүәЖИЈҝЈҝФЪЯ@·N·Nҙт“фЦ®ПВЈ¬ЦРҮшЧуЕЙ·ҙҢҰЕЙФЪй_КјөД•rәтҫНәЬлyҸДТ»ӮҖіЙКмөДХюЦОЕЙ„eРОіЙТ»ӮҖҪyТ»өДҪMҝ—ЎЈ¬FУРөДёчРЎҪMҝ—¶јКЗФЪ·ЦЙўөД оӣrЦРёчЧФіЙБўЖрҒнөДЎЈТтһйУРёчЧФіЙБўөДРЎҪMҝ—Ц®ҙжФЪЈ¬ҫНІ»ГвҫЯУРРЎҪMҝ—өДЕЕЛыРФЈ»ёчІ»ПаПВЈ¬ЙхЦБ»ҘПа№ҘјйЈ¬ХжХэХюЦОҶ–оЈэөДУ‘Х“¶јлyГв„eЙъЦҰ№қЎЈЎ№Ј§25Ј§
‘ӘФ“ХfЈ¬ФЪ®”•rЯ@Р©·ҙҢҰЕЙЦРЈ¬кҗӘҡРгКЗ„УҷCЧоХжХЎўЧојғқҚөДТ»ӮҖЎЈ
®җҮшУРЦӘТфЈ¬Ц§Ф®ҒнЧФНРЕЙҮшлH
ЦРҮшНРЕЙРЎҪMҝ—ФЪ»ҘПағAЬҲөДН¬•rЈ¬УЦ¶јПтНРВеЛ№»щҢ‘РЕЎўјДІДБПЈ¬ҳЛ°сЧФјәЈ¬№Ҙ“ф®җјәЎЈНРВеЛ№»щИзН¬К·М«БЦТ»ҳУЈ¬КјҪKкPЧўЧЕЦРҮшөДёпГьЯ„УЈ¬ҒK°СЖдТ•һйЧФјәАнХ“өДТ»үKЦШТӘЎёҢҚтһМпЎ№ЎЈЛыҢҰм¶ҒнЧФЦРҮшөДРЕјюәНІДБПЈ¬ҹoІ»ХJХжйҶЧxЈ¬ј°•r»ШёІЎЈЦ»КЗ®”•rаЈ§В·ВдббЈ¬ЙПәЈЦБЛыЧЎөДНБ¶ъЖдҫэКҝМ№¶ЎұӨөДРЕРиТӘЎё№ІЩMИэК®ОеМм№Ө·тЎ№ЎЈЛы»ШРЕөҪЙПәЈЈ¬ЎёЦБЙЩТІТӘЩMЯ@ФS¶аИХЧУЎ№ЎЈЈ§26Ј§ОТӮғҸДНРВеЛ№»щ1940Дкұ»МKВ“ҝЛёсІӘМШ„ХУГё«ЧУҝіЛАббёщ“юЖдЯzҮЪ40ДкббЈЁ1980Дк1ФВЈ©ІЕҶў·вөДНРВеЛ№»щЛҪИЛҷn°ёөДГЬ·вІҝ·ЦСYЈ¬°l¬FҸД1929Дк11ФВЦБ1940Дк8ФВЈ¬ЛыҪoЦРҮшНРЕЙј°кҗӘҡРгҢ‘өДРЕУР22·вЈ¬ЖдЦРЦұҪУХ„кҗӘҡРгҶ–оЈэөДҫНУР17·вЦ®¶аЎЈ
ЖрПИЈ¬НРВеЛ№»щВ РЕ„ўИКмoЖ¬ГжЦ®Ф~Ј¬ҢҰОьКХкҗӘҡРгјУИлНРЕЙҪMҝ—’сИЎБЛК®·ЦЦ”ЙчөД‘B¶ИЎЈ„ўИКмoТ»·ҪГж·ҙУікҗФЪ»щұҫБўҲцЙПТСҪӣғAПтНРЕЙЈ¬ЕъФuЎёОТӮғөДФ’ЕЙЎ№ҫЬҪ^кҗӘҡРгЕЙЈ»ө«ФЪёпГьРФЩЈьҶ–оЈэЙПИФУРұЈБфТвТҠЈәХJһйПВҙОёпГьҝӮУРТ»¶О•rйgЈЁјҙК№әЬ¶МЈ©ТӘНкіЙГсЦчёпГьЯzБфПВҒнөДИО„ХЈ¬І»Н¬ТвТ»й_КјҫНКЗЙз•юЦчБxёпГьЎЈкҗЦчҸҲөДЎёҹo®aлAјүЕcШҡЮrҢЈХюЎ№ҝЪМ–Ј¬ТІЕcЎёҹo®aлAјүҢЈХюЎ№І»Т»ҳУЎЈҢҰҙЛЈ¬НРКПФЪ1929Дк11ФВҪo„ўөДРЕЦРЈ¬ЕъФu„ўІ»‘ӘФ“ЕcЎёОТӮғөДФ’ЕЙЎ№·ЦБСЈә
ДгХfЛыӮғЈЁјҙЎёОТӮғөДФ’ЕЙЎ№ЎӘЎӘТэХЯЈ©·ҙҢҰкҗӘҡРгөҪЛыӮғөДк ОйЦРҒнЈ¬һйБЛЯ@Т»ьcЈ¬ҹoХ“ИзәОІ»ДЬК№ОТӮғЧФјә·ЦБСөДЎЈИз№ыМ«РФјұөШЕcкҗӘҡРгҪyТ»Ј¬И»ббУЦёъЛы·ЦБСЈ¬ДЗәҶЦұКЗЧпҗәЎЈОТӮғЕcЛыЦ®йgЈ¬ФЪЯ^ИҘөДЖзТҠЈЁТ»ҫЕ¶юЛДЁCТ»ҫЕ¶юЖЯДкЈ©КЗМ«ЙоБЛЈ¬ТФЦВПа»ҘйgӣЈ§УРКВПИөДаҚЦШҝјтһЈ¬І»ҝЙДЬҪyТ»ЖрҒнЎЈҹoХ“ИзәОЈ¬¬FФЪҫНёгЧуЕЙҪyТ»Ј¬ҒKЗТФЪЯ@ӮҖҶ–оЈэЙПЕcЛыӮғӣQБСЈ¬ДЗКЗф”Г§өДЈ»ЗЎәГДъЧФјәҫНХfкҗӘҡРгФЪЦРҮшёпГьРФЩЈьҶ–оЈэЙПКЗХҫФЪRБўҲцЙПөДЈ¬ҒKІ»ЕcОТӮғТ»ЦВЎЈҝЙКЗЯ@ӮҖҶ–оЈэ…sКЗ»щұҫөДЎЈ¬FФЪЕcҲФіЦЎёГсЦчҢЈХюЎ№өДИЛёгҪyТ»Ј¬ұгКЗІ»ҝЙрҲЛЎөДЭpВКЎЈЈ§27Ј§
Я@СYөДЎ°RЎұјҙАӯөТҝЛЈ¬ФшКЗВ“№ІНРЕЙ№ЗҺЦЈ¬ҙуёпГь•rЖЪФшИО№І®aҮшлHҲМОҜЎў•шУӣЎў–Јь·ҪІҝІҝйLЎўДӘЛ№ҝЖЦРЙҪҙуҢWРЈйLөИВҡЈ¬ЦРҮшБфҢWЙъ¶а”өКЗКЬЛыөДӰ푶шЮDПтНРЕЙөДЎЈө«ЛыФЪЦРҮшёпГьРФЩЈьҶ–оЈэЙПЕcНРВеЛ№»щУР·ЦЖзЎЈ1927Дкұ»В“№Ій_іэббЈ¬ұнКҫ»ЪЯ^Ј¬іРХJЎё№ӨЮrГсЦчҢЈХюЎ№өИУ^ьcЈ¬1930Дк»ЦҸНьhј®ЎЈТтҙЛЈ¬Лыұ»НРЕЙТ•һйЧғ№қХЯЎЈө«КЗЈ¬ббҒнЛыУЦұ»В“№Ій_іэЈ¬ҒKФЪ1937ДкөДЎёНРІјЈЁ№юБЦЈ©·ҙьhВ“ГЛ°ёЎ№ЦРұ»жӮүәЈ¬ЛАбб»ЦҸНГыЧuЎЈФЪЯ@СYЈ¬НРВеЛ№»щп@И»“ъРДкҗӘҡРгіЙһйАӯөТҝЛДЗҳУөДЎёЧғ№қХЯЎ№ЎЈм¶КЗЈ¬„ўИКмoКЬҙЛУ°н‘Ј¬ҸД1929Дк11ФВЦБ1930Дк3ФВЈ¬Ң‘БЛТФЙП¶аЖӘЕъЕРкҗӘҡРгөДОДХВЎЈ
ҝЁ –ЈҝІ®¶ч№ю¶аҫSЖжЈҝАӯөТҝЛ
ЎёОТӮғөДФ’ЕЙЎ№ТІФЪ1929Дк11ФВ15ИХЦВәҜНРВеЛ№»щЈ¬ҲуёжТтһйкҗӘҡРгІ»ҪУКЬЎёИэӮҖ—lјюЎ№Ј¬А^АmЧФјәөДӘҡБўБўҲцЈ¬ТтҙЛЎёОТӮғХJһйкҗӘҡРгІ»ФшГ“лxҷC•юЦчБxЈ¬ОТӮғӣQ¶ЁПс·ҙҢҰТ»ЗРҷC•юЦчБxХЯДЗҳУ·ҙҢҰЛыЎ№ЎЈЈ§28Ј§12ФВ22ИХНРВеЛ№»щёІРЕЈ¬ҢҰкҗЪ…ПтНРЕЙұнКҫЎёәЬҡgУӯЎ№Ј»Н¬•rЛыУЦХfЈәЎёОТәЬЦӘөАЛыЈЁкҗӘҡРгЎӘЎӘТэХЯЈ©ФЪёпГьДЗҺЧДкЦРөДІЯВФКЗК·ҙуБЦЎўІј№юБЦЎў¬” –¶ЎЦZ·төДХюІЯЎЈЎ№¶шҢҰЎёОТӮғөДФ’ЕЙЎ№ХfкҗЯҖӣЈ§УР·Е—үҷC•юЦчБxЈ¬„tұнКҫЎё¬FФЪОТЯҖӣЈ§УРЧxЯ^кҗӘҡРгИОәОҫVоIКҪөДВ•Гч•шЈ¬ЛщТФӣЈ§УРҝЙДЬФЪҙЛҶ–оЈэЙП°lұнТвТҠЎЈЎ№һйБЛҺНЦъЛыӮғ·ЦЗеҙуөДКЗ·ЗЈ¬НРФЪРЕД©МбіцБЛЛыЕcК·М«БЦ·ЦЖзөДК®ОеӮҖҶ–оЈэЈ¬ЧчһйәвБҝкҗӘҡРгәНЖдЛыИЛЎёЕcОТӮғКЗ·сФӯ„tЙПТ»ЦВЎ№Ј§29Ј§өДҳЛңКЎЈЯ@К®ОеӮҖҶ–оЈэЈ¬ҫНКЗТФЙПкҗӘҡРгұ»й_іэЗ°ббЛщ°lұнөДОДХВәНОДјюЦРҪӣіЈХ„өҪөДЕcЦР№ІЦРСлөД·ЦЖзЎЈ
1930Дк1ФВ25ИХЈ¬„ўИКмoН¬•rЕcкҗӘҡРгЕЙј°ЎёОТӮғөДФ’ЕЙЎ№ӣQБСТФббЈ¬УЦҢ‘РЕҪoНРВеЛ№»щҲуёжЗйӣrЎЈ2ФВ24ИХЈ¬НРВеЛ№»щ»ШРЕН¬ТвЕcкҗӘҡРгЕЙӣQБСЈ¬ө«І»Н¬ТвЕcЎёО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