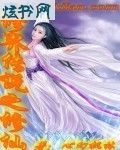іВ¶АРгИ«ҙ«-өЪ96ХВ
°ҙјьЕМЙП·ҪПтјь Ўы »т Ўъ ҝЙҝмЛЩЙППВ·ӯТіЈ¬°ҙјьЕМЙПөД Enter јьҝЙ»ШөҪұҫКйДҝВјТіЈ¬°ҙјьЕМЙП·ҪПтјь Ўь ҝЙ»ШөҪұҫТі¶ҘІҝЈЎ
ЎӘЎӘЎӘЎӘОҙФД¶БНкЈҝјУИлКйЗ©ТСұгПВҙОјМРшФД¶БЈЎ
ЎўаҚөИХэәГЮDПтНРЕЙЈ¬м¶КЗҫН°СЛыҺ§БЛЯ^ҒнЎЈЖдҢҚЈ¬ЛыІ»ЦӘөАНРВеЛ№»щЦчБxһйәООпЈ¬Ц»із°ЭкҗөДһйИЛЎЈЯ@ҙОЛыКЬУҡөҪОчұұ»IҝоЈ¬ёгөҪБЛТ»№PеXЎЈө«І»ҫГЈ¬ЖдНРЕЙөДЙн·Эұ©В¶Ј¬—о»ўіЗҫНҪРЛылxй_БЛЎЈббҒнЈ¬АоҝҙөҪНРЕЙӣЈ§УРЙхьN°lХ№З°НҫЈ¬ҫНИҘН¶ҝҝәъЧЪДПЈ¬ЧцБЛОч°І…ўЧh•юЧhйLЎЈ
Я@јюКВұнГчЈ¬ёпГькҮ IЈ¬Из№ыІ»КЗҝҝВ·ҫҖЎў·ҪбҳЎўХюІЯөДХэҙ_әНёпГьөДІ»”а„ЩАыЈ¬¶шҶОҝҝоIРдӮҖИЛөДчИБҰУ°н‘Ј¬КЗлyТФҫSіЦәН”UҙуөДЎЈкҗӘҡРгУЙм¶РЕСцНРВеЛ№»щЦчБxЯ@·NФЪҝӮуwЙПГ“лxЦРҮшҢҚлHәНИәұҠөДАнХ“Ј¬І»ФЩУРИзФЪРВОД»ҜЯ„У•rЖЪДЗҳУөДЎёҝӮЛҫБоЎ№өДУ°н‘БҰәНМ–ХЩБҰЎЈлmИ»ЯҖКЗТ»ӮҖьhЕЙөДоIРдЈ¬ЯҖФЪоIҢ§Т»ӮҖ·ҪГжөДёпГь№ӨЧчЈ¬ө«ҢҚлHЙПХэФЪПтЛјПлјТәНҢWХЯРНөДИЛОпЮD»ҜЈЁЯ@ҳУөДИЛОпУАЯhКЗЎё№ВӘҡХЯЎ№Ј©ЎЈІ»Я^ЧФјә…sІ»ЧФУXЈ¬ЯҖПл№МКШёпГьоIРдәН»о„УјТөДҪЗЙ«Ј¬үфПлҝӮУРТ»МмТ»әф°Щ‘ӘЈ¬ФЩ¶ИПЖЖр·ӯМмёІөШөДёпГьАЛіұЎЈЛыөДбб°лЙъЈ¬іэБЛЯҖУРТ»Р©у@КАс”ЛЧөДЛјПлйW№вәНҢWРgЙПИЎөГІ»ЛЧіЙҝғЦ®НвЈ¬ФЪёпГьКВҳIЙПЈ¬І»ҝЙДЬФЩИЎөГЦөөГХFТ«өДіЙҫНЎЈ
Из№ыТФТ»ӮҖИЛҙъұнТ»ӮҖ•rҙъөДФ’ЈәҸД1894ДкЕdЦР•юіЙБўөҪ1914Дк·ҙФ¬фY ҺК§”ЎЈ¬ҝЙТФ·QһйЎёҢOЦРЙҪ•rҙъЎ№Ј¬ТајҙЦРҮшГсЦчёпГьЗ°ЖЪЈЁТа·QЎёЕfГсЦчЦчБxёпГьЎ№Ј©ЎЈҸД1927ДкҪЁБўҫ®ҢщЙҪёщ“юөШөҪ1949ДкҠZИЎҙук‘ХюҷаЈ¬ҸД№І®aьh·ҪГжҝЙ·QЦ®һйЎёГ«қЙ–Јь•rҙъЎ№ЈЁЧФИ»Ј¬ХжХэөДЎёГ«қЙ–Јь•rҙъЎ№‘ӘФ“ҸД1935ДкЎёЧсБx•юЧhЎ№й_КјЈ©Ј¬јҙЦРҮшГсЦчёпГьббЖЪЈЁТа·QЎёРВГсЦчЦчБxёпГьЎ№Ј©ЎЈ¶шЯ@ғЙӮҖ•rҙъЦ®йgЈ¬јҙҸД1915ДкөҪ1927ДкЈ¬„tҝЙ·QһйЎёкҗӘҡРг•rҙъЎ№ЎЈТтһйЈ¬Я@ӮҖ•rҙъТФЎ¶РВЗаДкЎ·лsХIһйкҮөШ°lЖрөДРВОД»ҜЯ„УЎўОеЛДҗЫҮшЯ„УЎўсRҝЛЛјЦчБxФЪЦРҮшӮчІҘЎўЦРҮш№І®aьhіЙБўЎўҮш№ІәПЧчТФј°ұұ·Ҙ‘р ҺәНҮшГсёпГьЯ„УЈ¬ӣЈ§УРТ»ӮҖИЛөДУ°н‘і¬Я^кҗӘҡРгЎЈЯ@ӮҖ•rҙъөДМШьcЈ¬КЗҮшГсьhӣЈ§УРНкИ«ҶКК§оIҢ§ёпГьөДДЬБҰЈ¬¶ш№І®aьhЯҖӣЈ§УРИЎөГоIҢ§ёпГьөДДЬБҰЈ¬МҺм¶У–ҫҡ•rЖЪЎЈҪӣЯ^БЛЯ@ӮҖіЙйLЖЪЈ¬№І®aьhІЕЧЯЙПБЛӘҡБўоIҢ§ЦРҮшёпГьөДөАВ·ЎЈЯ@ӮҖ•rҙъТФкҗӘҡРг°l„УРВОД»ҜЯ„УәНЯBИОЦР№ІОеҢГЧоёЯоIҢ§ИЛһйЦчТӘҳЛХIЎЈ1927ДкТФббЈ¬кҗӘҡРгұШИ»ЦрқuөӯіцХюЦООиМЁЈ¬лxй_ёпГьөДЦчәҪөАЎЈ®…ҫ№Ј¬ҸДДЗТФбб№І®aьh·ҪГжКЗГ«қЙ–Јь•rҙъЈ¬ҮшГсьh·ҪГж„tКЗЎёКYҪйКҜ•rҙъЎ№БЛЎЈ
ЙнФЪҪӯәюЈ¬ЙнІ»УЙјәЎЈкҗӘҡРгјИИ»өЗЙПБЛНРЕЙЯ@МЛБРЬҮЈ¬Т»•rҫНлyТФГ“ЙнБЛЈ»әОӣrЈ¬Лыұ»РВЛјіұЎўРВөАВ·јӨЖрБЛҹбЗйЈ¬ТІІ»ПлГ“ЙнЎЈ1929Дк12ФВЈ¬кҗӘҡРгХТөҪБЛ„Ӯ„Ӯұ»ьhй_іэөДәОЩYЙо“ъИОЎёҹo®aХЯЙзЎ№өДГШ•шйLЈ¬ҢҰҪMҝ—ЯMРРБЛХыоDЎЈҙЛ•rЈ¬НРкҗЕЙіЙҶTТСҪӣ°lХ№өҪ120ИЛЈЁЖдЦРАПьhҶTЦӘЧR·ЭЧУҫУ춶а”өЈ©Ј¬ТІПсЦР№ІДЗҳУФOЦГБЛЙПәЈңы–ЈьЎўңыОчЎў·ЁДПЈЁ·ЁЧвҪзәНДПКРЈ©ИэӮҖ…^ОҜЈ¬ФЪјҶҸSәНҙaо^№ӨИЛЦРҪЁБўБЛЦ§ІҝЈ¬ФЪұұҫ©ТІҪЁБўБЛТ»ӮҖЦ§ІҝЈ¬”Ј§іцТ»ёұЕc№І®aьhИ«Гжҝ№әвЎўЖуҲDИЎҙъөДјЬ„ЭЎЈ
Я@ҳУ№ӨЧчБЛБщӮҖФВЈ¬№ыИ»іЙҝғІ»·ІЎЈФЪ1930Дк6ФВҹo®aХЯЙзҙъұн•юЧhЙПЈ¬кҗӘҡРгЧчЎ¶кPм¶ЦРҮш·ҙҢҰЕЙЯ^ИҘј°ДҝЗ°№ӨЧчЎ·өДҲуёжҒKё¶ЦTӣQЧhЈ¬Ры·QЈә°лДкТФҒнЈ¬ОТӮғЎёҝӮЛгІЭ„“БЛТ»—lРВөДөАВ·Ј¬ҒKҲFҪYБЛТ»Р©ЦШТӘІҝйTөДҺЦІҝ·ЦЧУЎ№ЎЈӣQЧhФЪ№Ҙ“фЦР№ІЦШТ•ЮrҙеОдСbфY ҺКЗЎёҷC•юЦчБxЎ№Ц®ббЈ¬ҸҠХЈыТӘЯMРРіЗКР№ӨИЛЯ„УЈ¬оIҢ§ИәұҠЧч·А¶RөДфY ҺЈ¬ХыоDғИІҝҪMҝ—Ј¬ЕарB№ӨИЛҺЦІҝЈ¬іэЙПәЈНвЈ¬ФЪҸV–ЈьЎўОдқhЎўМмҪтЎўЗаҚuј°–ЈьИэКЎёчӮҖ№ӨҳIЦРРД…^Ут°lХ№№ӨЧчЎЈЈ§4Ј§І»Я^Ј¬ббҒнУЙ춹І®aьhөДҙтүәәНГҰм¶ЕcЗаДкНРЕЙ ҺфYЈ¬Я@ӮҖУӢ„қВдҝХЈ¬Ц»ФЪПгёЫҪЁБўБЛТ»ӮҖЦ§ІҝЎЈ
п–КЬ»ШҮшНРЕЙҪMҝ—өДЕЕ”DәНҙт“ф
кҗӘҡРгөИИЛТвБПІ»өҪөДКЗЈ¬ұ»№І®aьhҙт“фй_іэЈ¬қMЗ»ҹбЗйЮDПтНРВеЛ№»щЦчБxЈ¬ТӘЗујУИл»тВ“әПҸДДӘЛ№ҝЖ»ШҮшөДЗаДкНРЕЙҪMҝ—•rЈ¬ҫ№И»п–КЬЕЕ”DәНҙт“фЎЈ
1929Дк4ФВЕeРРөДВ“№ІөЪК®БщҙОҙъұнҙу•юЧчіцФЪВ“№ІьhғИЗеьhөДӣQЧhЈ¬ДӘЛ№ҝЖЦРЙҪҙуҢWТІІ»АэНвЎЈ6ФВЈ¬ЦРЙҪҙуҢWХЩй_ьhҶTҙу•юЈ¬ФS¶аҢWЙъұ»ЦёУР…ўјУНРВеЛ№»щЕЙ»о„УөДПУТЙЎЈУЙм¶ЧC“юІ»ЧгЈ¬УРР©НРЕЙ·ЦЧУұ»ЛН»ШҮшғИЎЈө«КЗЈ¬ҸДЗпјҫҢWЖЪй_КјЈ¬В“№ІЦРСлұOІмОҜҶT•юЕЙіцЗеьhОҜҶTҒнөҪЦРЙҪҙуҢWЈ¬’сИЎұЖ№©РЕКЦ¶ОЈ¬ЦВК№Т»О»Ш“ШҹБфМKЦРҮшНРЕЙГШГЬҪMҝ—№ӨЧчөДҢWЙъЧФҡў•rҪ»іцБЛТ»·ЭБфМKНРЕЙҢWЙъГыҶОЎЈЈ§5Ј§НхОДФӘЈЁјҙНх·ІОчЎўлpЙҪЈ©ХfҙЛИЛКЗЪwСФЗдЈ¬ГыҶОУРИэ°ЩИЛЈ¬ЖдЦРИэК®ИЛТС»ШҮшЈЁКўФАХfЈ¬Ҫ»іц°ЛЎўҫЕК®ИЛГыҶОөДКЗАоЖјЈ©ЎЈУЙм¶ҪУКЬЙПҙОтҢЦр»ШҮшөДНРЕЙҢWЙъҙЯЙъБЛЦРҮшНРЕЙҪMҝ—ҒKУ°н‘өҪкҗӘҡРгөИТ»ҙуЕъьhғИоIҢ§ҺЦІҝЮDПтНРЕЙөДҪМУ–Ј¬МKВ“®”ҫЦЯ@ҙО°СЯ@Р©НРЕЙҢWЙъҺЧәхИ«Іҝ°lЕдөҪОчІ®АыҒҶ·юҝаТЫЎЈіэҳOЙЩ”өҪӣЯ^З§РБИfҝаМУ»ШЦРҮшНвЈ¬Ҫ^ҙу¶а”өФЪДЗСYұ»ХЫДҘ¶шЛАЎЈ
Нх·ІОчЈ¬ФӯГыЈ¬НхОДФӘЈ¬№PГылpЙҪЈ¬ЦРҮшАПТ»Э…НРВеҙД»щЦчБxХЯөДоIҢ§ИЛ
Н¬•rЈ¬В“№ІТІІ»·ЕЯ^ГыҶОЦРТСҪӣ»ШҮш¶шЧсХХНРВеЛ№»щөДЦјТвА^АmлЈ§ұОФЪЦР№ІьhғИөДИЛЈ¬Бўјҙ°СҙЛГыҶОНЁЦӘҪoЦР№ІЦРСлЎЈЦР№Іҝј‘Ј§өҪ°ЧЙ«ҝЦІАөДҢҚлHЗйӣrЈ¬¶шЗТЯ@Р©НРЕЙ·ЦЧУФЪ№ӨЧчЙПұн¬FБјәГЈ¬ТІКЗҮшГсьhІ¶ҡўөДҢҰПуЈ¬ТтҙЛ’сИЎБЛЦ”ЙчөДЮk·ЁЈәЎёПтЈЁДӘЛ№ҝЖҒнЈ©РЕғИЛщЦёіцөДН¬ЦҫЈ¬·Ц„eөД°lіцБЛНЁЦӘЈ¬ТӘЛыӮғШ“ШҹұнГчЧФјәөДХюЦО‘B¶ИЈ¬ҢҰНРВеЛ№»щ·ҙҢҰЕЙөДТвТҠЈ¬ТФј°КЗ·с…ўјУ·ҙҢҰЕЙ»о„УөДЗйРОЎ№ЎЈЈ§6Ј§
ҪУөҪНЁЦӘөДУРР©ИЛ»ШБЛРЕЈ¬ҸДЎ¶јtЖмЎ·ЙПХӘөЗөДЯ@Р©ИЛөДРЕҝҙЈ¬УРөДөДҙ_І»КЗНРЕЙ·ЦЧУЈ¬Ц»КЗУЙм¶ФЪДӘЛ№ҝЖ·ҙҢҰЯ^НхГчЈ¬ІЕұ»Х_һйНРЕЙЈ¬ИзҗБУкМДөИЎЈТтҙЛЈ¬ЛыӮғјҠјҠ°lұнВ•ГчЈ¬·сХJЧФјәКЗНРЕЙЎЈУРөДКЗНРЕЙЈ¬ө«КЗһйБЛА^АmлЈ§ұОФЪьhғИЈ¬ТІ·сХJЧФјәКЗНРЕЙЈ¬Изе§өВЦ®ЈЁУЦГые§ЗеИӘЈ©ЎўҸҲ·fРВ·тӢDЎЈУЙ춶јаҚЦШұнКҫ“нЧoЦРСлөДВ·ҫҖЈ¬·сХJЕc·ҙҢҰЕЙУРИОәОВ“АMЈ¬ҒKЕcЦ®ЧчЯ^фY ҺЈ¬ТтҙЛТ»•rөГТФІmМмЯ^әЈЈ¬ЦР№ІұнКҫЈәЎёҸДЯ@Щ•ГчЦРЈ¬ЦРСлХJһйЯ@Р©Н¬ЦҫӣЈ§УР·ҙҢҰЕЙПУТЙөДХжҙ_ЧC“юЎЈЎ№УРӮҖ„e„tұнКҫ»ЪёДЈ¬В•ГчГ“лxНРЕЙЈ¬ИзЪwРСГсФЪЎ¶јtЖмЎ·ЙП°lұнБЛЎ¶ОТҢҰм¶ХюЦОөДХJЧRәН‘B¶ИЎӘЎӘГ“лxНРВеЛ№»щ·ҙҢҰЕЙөДВ•ГчЎ·ЎЈЈ§7Ј§ө«¶а”өИЛҢҰНЁЦӘІ»УиАнІЗЈ¬ҒK·eҳOЯMРР·ҙҢҰЕЙөД»о„УЈ»УРөДФЪЧцБЛӮҖ„eХ„Ф’өД ҺИЎ№ӨЧчббЈ¬ЯҖҲФіЦНРЕЙБўҲцЎЈм¶КЗЈ¬ФЪЗеіэәһГым¶Ўё°ЛК®Т»ИЛВ•Гч•шЎ№өДНРкҗЕЙ·ЦЧУөДН¬•rЈ¬УЦіЙЕъөШй_іэЯ@Р©ДӘЛ№ҝЖ»ШҮшЯMИльhғИөДНРЕЙ·ЦЧУЈ¬іц¬FБЛГCНРөДУЦТ»ӮҖёЯіұЎЈ
УРР©НРЕЙ·ЦЧУИзНхОДФӘЈ¬»ШҮшбб·ЦЕдФЪЦР№ІЦРСлҪMҝ—Іҝ®”ҺЦКВЈ¬…ЗјҫҮАһйЦРСлРыӮчІҝҺЦКВЎЈһййLЖЪБфФЪьhғИЯMРР·ҙҢҰЕЙ»о„УЈ¬ҢҰ№ӨЧчұн¬FөГ¶јәЬ·eҳOЎЈУГНхОДФӘөДФ’ХfЈ¬ЎёОТөД‘B¶ИКЗЈәЖҙГь№ӨЧчЈ¬ұMЙЩХfФ’ЎЈЎ№ТтҙЛЙоөГҪMҝ—ЙПөДРЕИОәНЖчЦШЎЈЛщТФЈ¬®”ЦР№ІШ“ШҹИЛФЪДӘЛ№ҝЖҒнРЕЦРөГЦӘЖдХюЦОғAПт•rЈ¬К®·Цу@У әНЯzә¶Ј¬ёьјУДНРДјҡҝ@өШҪoЛыЧц ҺИЎ№ӨЧчЎЈНхОДФӘ»Ш‘ӣЈә
ЎёҙЛ•rОТХэІЎө№ФЪбtФәСYЎЈЦЬ¶чҒнЈЁ•rИОҪMҝ—ІҝйLЎӘЎӘТэХЯЈ©°lТҠГыҶОЙПУРОТөДГыЧЦЈ¬ХТОТХ„БЛТ»ҙОФ’ЎЈЛыөД‘B¶ИәЬУСЙЖЈ¬ҙуТвХfЈәЛықMТвОТҺЧӮҖФВҒнөД№ӨЧчЈ¬ЛщТФПЈНыОТһйЧФјәөДЎәёпГьЗ°НҫЎ»Ј¬ЧчТ»•шГжВ•ГчЈ¬·Е—үНРЕЙТвТҠЈ¬ФЪЎ¶јtЖмЎ·ЙПөЗЭdЈ»Я@ҳУЈ¬ЛыҝЙТФұЈЧCОТТАЕfБфФЪьhғИ№ӨЧчЎЈЎ№ЎёОТӣЈ§УРХfЙхьNФ’Ј¬Ц»ҙр‘ӘҢ‘В•ГчЎЈөЪ¶юМмЈ¬ІҝСYөДҪ»НЁҒнИЎЈ¬ҝҙБЛәЬКЗК§НыәНлyЯ^Ј¬ТтһйОТЛщҢ‘өДНкИ«І»КЗЛыӮғЛщПЈНыөДЎЈОТұнГчБЛЧФјәөДХюЦОТвТҠЈ¬В•ГчОТІ»Н¬ТвьhБщҙОҙу•юЛщЧчөДкPм¶ЦРҮшёпГьК§”ЎөДФӯТтЈ¬кPм¶ДҝЗ°ҫЦ„ЭТФј°З°Нҫ№АУӢөД·N·NӣQ¶ЁЈ»ө«ОТН¬•rЦёіцЈәЯ^ИҘТ»•rЖЪөД№ӨЧчТСҪӣЧCГчЈәОТҒKІ»ФшТтһйЧФјәөДІ»Н¬ТвТҠ¶шФЪ№ӨЧчЦРЯЎ®·ҙ¶а”өөДӣQ¶ЁЈ»ОТТӘұЈБфЧФјәөД®җТҠоҠТвА^АmФЪГсЦчјҜЦРЦЖөДҪMҝ—В·ҫҖПВһйёпГь·ю„ХЈ»ТтҙЛОТПЈНыьhТІ‘ӘФ“ЧсХХБРҢҺөДҪMҝ—Фӯ„tЈ¬ИЭФSОТИФЕf№ӨЧчЎЈЎ№Ј§8Ј§
ө«КЗЈ¬НхОДФӘәЬҝм°l¬FЧФјәКЗМ«МмХжБЛЎЈЦЬ¶чҒнЎўАоБўИэјҙК№ДЬУРЎёБРҢҺКҪөДҢ’ИЭҙу¶ИЎ№Ј¬ө«ФЪК·М«БЦөДГьБоПВТІӣQІ»ёТЧцЎЈЎёОТЦӘөАЈ¬ҪMҝ—І»•юФЩҒнХТОТЈҝЈҝҺЧМмЦ®ббЈ¬ОТұ»й_іэьhј®өДНЁёжөЗіцҒнБЛЎЈЎ№Ј§9Ј§Н¬ҳУЗйӣrөД№ІУРИэИЛЎЈ1930Дк5ФВ14ИХіц°жөДЎ¶јtЖмЎ·ЙПЈ¬ҝҜөЗБЛЯ@ҳУөДОДјюЈәЎ¶ЦРҮш№І®aьhЦРСлОҜҶT•юһйй_іэ…ЗјҫҮАЎўНхОДФӘЎўЦЬіз‘cьhј®КВНЁЦӘИ«ьhЎ·ЎЈ
ҸДДӘЛ№ҝЖ»ШҒнөД„ўИКмoКЗӮҖМШКвИЛОпЈ¬Т»ПтКЗЎё·ҙҢҰЕЙЦРөД·ҙҢҰЕЙЎ№ЎЈ»ШҮш•rЧФЦӘЧФјәөДЗйӣrІ»•юұ»ЦР№ІҪУјЈыЈ¬ҫНЯЎ®·ҙлЈ§ІШФЪьhғИөДФӯ„tЈ¬ПтЦРСлҙъұнҗБҙъУў№«й_ұнКҫІ»Н¬ТвьhөДВ·ҫҖЈ¬ҒKҢўМбіцЧФјәөД•шГжТвТҠЎЈлSббҫНлЈ§ҫУЖрҒнЈ¬І»ФЩ…ўјУьhөДИОәО№ӨЧчәН»о„УЎЈҪУЧЕЈ¬ФЪІЯ„қЎёОТӮғөДФ’Ў№ЕcкҗӘҡРгЎёҹo®aХЯЙзЎ№өДВ“әПК§”ЎббЈ¬җАРЯіЙЕӯЈ¬ФЪ1929Дк11ФВ5ИХУНУЎУЎ°lБЛТ»ЖӘоЈэһйЎ¶·ҙҢҰЕЙҪyТ»Я„УЦ®З°НҫЎ·өДРЎғФЧУЈ¬”ўКцБЛЛыНЖ„УғЙЕЙВ“әПј°К§”ЎөДҪӣЯ^Ј¬јӨБТ№Ҙ“фғЙЕЙҢҰНРЕЙөДЎёҪyТ»Я„УЎ№ӣЈ§УРХТвЈ¬К№Я„УТФЎёК§”ЎЎ№¶шЎёёжТ»¶ОВдЎ№Ј¬әБІ»СЪп—өШГпТ•ЗаДкНРЕЙЈ¬Н¬•rУЦ№Ҙ“фкҗӘҡРгЎЈ
ҢҰм¶ЗаДкНРЕЙјҙЎёОТӮғөДФ’ЕЙЎ№Ј¬„ўИКмoЕъФuЖдоIҢ§ҷCкPЎёҝӮҺЦКВ•юЎ№І»ОьКХкҗӘҡРгЕЙөДФӯТтКЗЎёНкИ«КЗһйБЛөШО»Ў№Ј¬Ўё‘ЦЕВДЗР©УРДЬБҰөДИЛЎ№ЎЈЈ§10Ј§¶шЗТҢҰЛыДГ»ШҒнөДНРВеЛ№»щЖрІЭөДЦРҮшНРЕЙХюҫVІ»јУУ‘Х“Ј¬ёьІ»ФЪ1929Дк9ФВЕeРРөДЎё¶юҙъ•юЎ№ЙПЧчіцӣQЧhЎЈФЪҢҰҙэЦР№ІөД‘B¶ИЙПЈ¬ЕъФuЎёҝӮҺЦЎ№Ҫ©ЛАҲМРРНРЕЙФЪьhғИ»о„УөДФӯ„tЈ¬ЦчҸҲЎёЧўЦШФЪьhғИЯMРР·ҙҢҰЕЙөД№ӨЧчЎ№Ј¬Н¬•rУЦ‘ӘФ“ӘҡБўҪMҝ—Ј¬ФЪьhНв·eҳOй_Х№»о„УЎЈЛыЯҖХJһйЈ¬ЎёОТӮғөДФ’Ў№ФЪЎё¶юҙъ•юЎ№ХюЦОӣQЧh°ёЦРкPм¶ёпГьРО„ЭЎёХэФЪҸНЕdЎ№өДМб·ЁЕcЦР№ІөДУ^ьcПаЛЖЈ¬ҲМРРөДКЗЎёН¶ҪөЕЙВ·ҫҖЎ№ЎЈЈ§11Ј§
ЦБм¶кҗӘҡРгЈ¬„ўИКмoҢҰЖдҢ‘өДЎ¶Х“ЦРҮшёпГьөДРФЩЈьЎ·ЈЁҢWНРОДјюРДөГЈ¬Ц»ФЪНРЕЙН¬ЦҫЦРӮчйҶЯ^Ј¬ӣЈ§УР№«й_°lұнЈ©Ўў1929Дк10ФВ10ИХҪoЦРСлөДРЕЎўЎ¶ёжИ«ьhН¬Цҫ•шЎ·ј°Ў¶ОТӮғФЪ¬FлA¶ОХюЦОфY ҺөДІЯВФҶ–оЈэЎ·өИОД„tЯMРРБЛёьһйГНБТөДЕъЕРЈә
Т»ЎўЎёІ»ҸШөЧіРХJЧФјәөДеeХЎ®Ў№Ј¬ҢҚлHЙПЖуҲDЎёГ“Р¶Я^ИҘёпГьК§”Ў‘ӘШ“өДШҹИОЎ№Ј¬ЎёұнГжЙПіРХJеeХЎ®Ј¬ҢҚлHЙП·ҙҲМЦ®УъҲФЎ№ЎЈЈ§12Ј§„ўИКмoәНЛщУРЗаДкНРЕЙХJһйЈ¬кҗӘҡРгКЗЎёЧФУXөШҲМРРЎ№№І®aҮшлHөДВ·ҫҖЈ¬¶шІ»КЗПсЛыЧФјәХfөДЎёЯЎ®РДөШҲМРРЎ№Ј»
¶юЎўІ»МбНРВеЛ№»щөДЎёҹo®aлAјүҢЈХюЎ№ҝЪМ–Ј¬¶ш„eіцРДІГөШМбЎёҹo®aлAјүЕcШҡЮrҢЈХюЎ№өДҝЪМ–Ј¬Я@ЎёҢўіЙһйГсЦчҢЈХюХЯЦ®Чобб¶ЭҪСЎ№Ј»Ј§13Ј§
ИэЎўӘҡБўіЙБўЧФјәөДҪMҝ—Ј¬Х„ЕРВ“әП•rЈ¬УЦІ»оҠТвҪвЙўЛьЎЈ
һйҙЛЈ¬„ўИКмoРыҒСЈ¬кҗӘҡРгЕЙКЗЎёјЩҪе·ҙҢҰЕЙөДХРЕЖЎ№Ј¬ЎёҢҚлHКЗЕfШӣЩNБЛРВЙМҳЛЎ№Ј¬ЧғіЙБЛЎёУТЕЙ·ҙҢҰЕЙЎ№Ј¬¶шІ»КЗЎёЧуЕЙ·ҙҢҰЕЙЎ№ЎЈЛыЙхЦБЯ@ҳУҮА…–өШ№Ҙ“фкҗӘҡРгЈәЎёОТӮғЧоіхҢҰм¶кҗӘҡРгФшІ»·Ұ»ГПлЎ№Ј¬Ўё¶МЖЪәПЧчЎ№ббЈ¬°l¬FЛыЎёлxй_ёпГьБўҲцЈ¬ҫ«ЙсЛҘ”ЎЎ№Ј¬ЎёүҷВдіЙһйТ»ӮҖК§ТвөДХюҝНЎ№ЎўЎёТ»ӮҖРЎЩY®aлAјүГсЦчЦчБxХЯЎ№Ј»ЎёјҜәПм¶ЛыЦЬҮъөДЈҝЈҝ¶јКЗР©ЖЫФpК§ТвөДХюҝНЎ№Ј¬ЎёОТӮғ‘Ә®”ҒGөфЛыЎ№ЎЈЈ§14Ј§ЛщТФЈ¬®”ЛыҺНЦъЖрІЭөДЧоббУЙкҗӘҡРгРЮёД¶ЁёеөДЎ¶ОТӮғөДХюЦОТвТҠ•шЎ·°lұн•rЈ¬„ўИКмo”аИ»ҫЬҪ^ФЪЙПГжәһГыЈ¬ҒKВ•ГчЯ@ӮҖТвТҠ•шұИЛыФӯҒнЖрІЭөДёеЧУЎё”UҙуБЛФS¶аЎ№Ј¬ЎёӣЈ§УРТ»ьcёпГьөДЧчУГЈ¬Ц»КЗМжкҗӘҡРгм–№МЛыЯ^ИҘөДеeХЎ®Ў№ЎЈЈ§15Ј§
„ўИКмoөДЎ¶·ҙҢҰЕЙҪyТ»Я„УЦ®З°НҫЎ·РЎғФЧУұ»ЦР№І°l¬FббЈ¬ХJһйКЗФЪҪMҝ—РВөДЎё·ҙьhВ“ГЛЎ№Ј¬Ј§16Ј§12ФВ29ИХ№«й_ЦВәҜ„ўЈәЎёПЮДгм¶йҶҲуЈЁјtЖмЈ©ббИэИХғИХэКҪУГ•шГжҙрёІЦРСлЎ№Ј¬ЧЕБо„ўФЪЦР№ІЦРСлЕcНРЕЙВ·ҫҖЦ®йgЧчіцҫс“сЎЈЈ§17Ј§„ўОҙУиАнІЗЈ¬лSјҙЧФ„УГ“ьhЎЈ®”•rІ»ЙЩНРЕЙ·ЦЧУ¶јКЗЯ@ҳУЧФ„УГ“ьhөДЎЈ
1930Дк1ФВЈ¬„ўИКмoЕcНхОДФӘЎўАи°ЧВьЎўЛО·кҙәөИҫЕИЛБнРРіЙБўТ»ӮҖНРЕЙРЎҪMҝ—Ј¬°lұнйLЯ_јsТ»ИfЖЯЗ§ЧЦөДЎ¶ёжН¬Цҫ•шЎ·ЈЁРЎғФЧУЈ©Ј¬ЖрГыЎ¶ЦРҮшЧуЕЙ№І®aЦчБxХЯН¬ГЛЎ·Ј¬ҒKФЪФ“ФВ30ИХіц°жҷCкPҲуЎ¶К®ФВЎ·Ј¬м¶КЗЛыӮғұ»ИЛ·QһйЎёК®ФВЙзЎ№ЎЈ
Ў¶ёжН¬Цҫ•шЎ·ғЙГжй_№ӯЈ¬Т»ГжҮА…–ЕъЕРкҗӘҡРгЈ¬ФЪЦШСЈэТФЙП„ўИКмoҺЧЖӘОДХВЦРөДУ^ьcЕъЕРкҗӘҡРгөДН¬•rЈ¬УЦФцјУғЙ—lЈә1ЎўЕъЕРкҗӘҡРгЕcЕнКцЦ®1929Дк10ФВ26ИХЦВЦР№ІЦРСлРЕЦРДіР©Хf·ЁЎёЕcІј№юБЦҢҰЦіГсөШҪӣқъ°lХ№өД№АБҝКЗНкИ«ПаЛЖЎ№Ј»2ЎўЕъЕРкҗӘҡРгГгҸҠҪУКЬҮшГс•юЧhҝЪМ–Ј¬ҢҚлHіЦУРөДУ^ьcКЗЎёХжХэөДҮшГс•юЧhЦ®ХЩјҜһйІ»ҝЙДЬЎ№әНЎёҢҰм¶ҮшГс•юЧhұҫЙнІ»ДЬУРТ»ьc»ГПлЎ№Ј»¶шІ»КЗНЁЯ^һйҮшГс•юЧhфY ҺҪТВ¶ЩY®aлAјүЈ¬ҲFҫЫёпГьИәұҠЈ¬Я^¶ЙөҪМKҫS°ЈЈ¬ҠZИЎИ«ҮшХюҷаЎЈТтҙЛРыҒСЈәЎёкҗӘҡРгЕЙКЗҙчЧЕЧуЕЙ·ҙҢҰЕЙөДјЩГжҫЯФЪДЗСYЦрқuРОіЙЛыӮғөДУТЕЙ·ҙҢҰЕЙЎЈЎ№
БнТ»·ҪГжЈ¬ПөҪyөШЕъЕРЎёОТӮғөДФ’ЕЙЎ№Ј¬ЦёЖд1929Дк9ФВөЪ¶юҙОҙъұнҙу•юНЁЯ^өДЎёХюЦОӣQЧh°ёЎ№ЯЎ®ұіНРВеЛ№»щөДЎёЦРҮш№І®aЦчБx·ҙҢҰЕЙХюҫVЎ№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