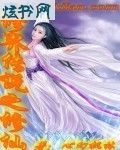іВ¶АРгИ«ҙ«-өЪ121ХВ
°ҙјьЕМЙП·ҪПтјь Ўы »т Ўъ ҝЙҝмЛЩЙППВ·ӯТіЈ¬°ҙјьЕМЙПөД Enter јьҝЙ»ШөҪұҫКйДҝВјТіЈ¬°ҙјьЕМЙП·ҪПтјь Ўь ҝЙ»ШөҪұҫТі¶ҘІҝЈЎ
ЎӘЎӘЎӘЎӘОҙФД¶БНкЈҝјУИлКйЗ©ТСұгПВҙОјМРшФД¶БЈЎ
ЎӘЎӘЯ@ЗЎЗЎКЗкҗӘҡРгФЪЕc„ўИКмoҳOЧуЕЙ ҺХ“•rөДУ^ьcЎЈНРКПБўҲцхrГчөШХҫөҪБЛкҗӘҡРгТ»Я…ЎЈ
кPм¶јtЬҠҶ–оЈэЈ¬НРКПЦ»ХfЈәЎёЛьөД°lХ№ЧCҢҚБЛ·ҙҢҰЕЙөДТ»°гөДоAСФЈәИзІ»өГ№ӨИЛлAјүЯ„УөДоIҢ§Ј¬„tЛьөДГьЯҫН•юТАЩҮм¶ЖдҙжФЪ…^УтЦРөДЙПҢУГсұҠЈЁЙМИЛЕcЦРЎўё»ЮrЈ©Ј¬јҙұ»ҮшГсьhј°өЫҮшЦчБxөДғһ„ЭұшБҰЛщүә·юЎЈЎ№ЎӘЎӘЯ@ӮҖУ^ьcТІКЗЕcкҗӘҡРгТ»ЦВөДЎЈ
кPм¶ҮшГс•юЧhҶ–оЈэЙПөД ҺХ“Ј¬ТББ_ЙъҪйҪBЈәЎё„ўИКмoХfИәұҠ°СҮшГс•юЧhәНҹo®aлAјүҢЈХюЎә®”іЙТ»ӮҖ–ЈьОчЎ»ЈЁјҙҮшГс•юЧhКЗҹo®aлAјүҢЈХюЦ®НЁЛЧ№«КҪЈ©Ј¬НРКПҫНҙт”аБЛОТөДФ’Ј¬ЛыХfЈәө№І»ИзЯ@ҳУХfёьҢҰР©Ј¬ҫНКЗ„ўИКмo°СЛыЧФјәРДСYөД–ЈьОчәНИәұҠРДСYөД–ЈьОчЎә®”іЙТ»ӮҖЎ»БЛЎЈЛыҪУЧЕХfЈ¬ФЪУў·ЁөИҮшөД°lХ№ЦРЈ¬ГсЦчЦчБxКЗЧЯПтЙз•юЦчБxөДТ»ӮҖйL•rЖЪЈ¬КЗСУйLБЛҺЧКАјoөД•rЖЪЈҝЈҝФЪЦРҮшЈ¬ЎәГсЦчЎ»•rЖЪҳO¶МЈ¬ТІФSНкИ«І»ҙжФЪЎЈЯ@¶јКЗНкИ«ҝЙДЬөДЈ¬ө«Я@І»КЗХfЈ¬ИәұҠ°СҮшГс•юЧh»тГсЦчөДёЕДоәНҹo®aлAјүҢЈХюЎә®”іЙһйТ»ӮҖ–ЈьОчЎ»ЎЈЎ№
ЎӘЎӘЯ@ӮҖУ^ьcТІКЗЕcкҗӘҡРгЕъЕР„ўИКмoөДУ^ьcТ»ЦВөДЎЈ
ЧоббЈ¬кPм¶ТтЯ@Р© ҺХ“Ј¬ЦРҮшНРЕЙРВЦРСлӣQ¶Ёй_іэкҗӘҡРгЈ¬НРКПхrГчөШұнКҫЈә
ОТ¬FФЪЯҖӣЈ§УРНкИ«ІtҪвЯ@Р© ҺХ“Ј¬ЛщТФЯҖІ»ДЬұнКҫТвТҠЎЈІ»Я^УРТ»ьcОТҝЙТФХfөДЎЈОТПлјҙұгкҗӘҡРгҫЯУРДіР©ҷC•юЦчБxөДіЙ·ЦЈ¬ө«Лы®…ҫ№¶а»оҺЧҡqЈ¬УРёь¶аөДҪӣтһЎЈЛы°СЯ@Т»ЗР¶јФЪЙъ»оЦРуwтһЯ^БЛЎЈЛыұИ„eИЛДЬФЪёьһйҫЯуwөДРОКҪПВИҘЦӘөАЯ@Р©ЎЈЛыДЬШ•«IОТӮғФS¶аәГөДТвТҠЎЈ¶ш„ўИКмoҝЙЕВөШ°СІ»Н¬ТвТҠХFҙуБЛЈҝЈҝОТПаРЕәНкҗӘҡРгөД·ЦБСКЗІ»ФКФSөДЎЈОТӮғҪ^ҢҰРиТӘБфЛыФЪөЪЛДҮшлHҝӮОҜҶT•юЦРЕcОТӮғәПЧчЎЈЈ§49Ј§
НРВеЛ№»щЙоЙоРЕИОәНТРЦШкҗӘҡРгЈ¬ҫНФЪЕcТББ_ЙъөЪИэҙОХ„Ф’ббЈ¬јҙ8ФВ10ИХЈ¬ЛыБўјҙҪoФЪЙПәЈөДАоёЈИКҢ‘БЛТ»·вРЕЈ¬ҲФӣQ·АЦ№ФЩіц¬FЎёй_іэЎ№кҗӘҡРгөДКВјюЎЈКЧПИІ»өГІ»Д¬ХJЦРҮшНРЕЙҪMҝ—өДЧғ»ҜЈ¬ЎёЦРҮшЦ§ІҝТІТСіЙБўЖдЧФјәөДЦРСлОҜҶT•юЈ¬ЕcкҗӘҡРгј°ЖдТ»ЕЙІ»ПаёЙБЛЎ№Ј¬ЎёДЗР©ЛјПл·ЦЖзЈ¬ОТ•ә•rІ»ұнКҫТвТҠЎ№ЎЈ¶шҢҰкҗӘҡРг‘B¶И…sК®·ЦхrГчЈ¬әБІ»СЪп—өШҪЯБҰНЖізкҗӘҡРгЎёКЗЦӘГыөДЈ¬¶шЗТҳIТСЧCГчһйҪ^ҢҰҝЙҝҝөДЎ№ЎЈЎёЛыКЗҮшлHөДИЛОпЈ¬Лы¬FФЪұ»ұOҪыФЪАОғИЎЈЛыІ»ғHИФЕfЦТҢҚм¶ёпГьЈ¬¶шЗТИФЕfЦТҢҚм¶ОТӮғөДғAПтЎЈЎ№
ЎӘЎӘЯ@СYЈ¬ЕcТББ_ЙъөДХ„Ф’Т»ҳУЈ¬ҢҚлHЙПТСҪӣГчҙ_ұнКҫБЛҢҰғЙЕЙ ҺХ“өДТвТҠЎЈНРКПТІІ»оҷЯ@·NЧФПаГ¬¶ЬөД¬FПуЈ¬ЧоббЙхЦБТФЎёДгӮғІ»ТӘОТТӘЎ№өД‘B¶ИХfЈә
ЧуЖрЈәК·ДӯМШИRЎўК’І®јЈыЎўЛО‘cэgЎўІМФӘЕаЎўТББ_ЙъЎўБЦХZМГЎўф”Сё
кҗӘҡРгҝЙТФ¶шЗТұШнҡУРЖдО»ЦГФЪөЪЛДҮшлHоIҢ§ҷCкPЦ®ЦРЈ»ОТӮғ¬FФЪХэФЪ„“БўөЪЛДҮшлHЈ¬ТФҝӮАнКВ•юһйоIҢ§ҮшлHөДАнХ“ҷCкPәНЦJФғҷCкPЈҝЈҝОТХJһйЈ¬ҹoТЙЈ¬кҗӘҡРгН¬ЦҫКЗ‘Ә®”јУИлҝӮАнКВ•юөДЈ¬І»№ЬЛыәНЦРҮшЦ§ІҝУРЙхьNЦШТӘ·ЦЖзЈ»ОТӮғИз№ы’Ғ—үБЛкҗӘҡРгөДәПЧчЈ¬ДЗҢҰм¶өЪЛДҮшлHөДНюҷаҢўКЗТ»ӮҖҮАЦШөДҙт“фЎЈЈ§50Ј§
Я@ұнГчЈ¬НРВеЛ№»щФЪкҗӘҡРгЧоА§лyәНКЬЗьИиөДЗйӣrПВЈ¬ҪoБЛЛыУЦТ»ҙОЧоҙуЦ§іЦәНЎёҳsЧuЎ№ЎЈ¶юИЛЦ®йgПа»ҘЧрЦШөДкPӮSЈ¬Т»ЦұА^АmөҪНРВеЛ№»щ1940ДкУцҙМЙнНцЎЈ
НРВеЛ№»щФЪЕІНюВ ИЎБЛТББ_ЙъөДУРғAПтРФЎӘЎӘЧ““P„ўИКмo¶шЕъЕРкҗӘҡРгЎӘЎӘөДҲуёжббЈ¬ЯҖДЬҢҰЯbЯhөДЦРҮш°lЙъөДЗйӣrЧчіцЯ@ҳУөД·ҙ‘ӘәНЕcкҗӘҡРгТ»ҳУөДЕР”аЈ¬ҝЙТҠЛыЕcкҗӘҡРгТ»ҳУЈ¬өДҙ_ҫЯУРН¬ҳУөДӮҘИЛЖ·ЩЈьЎЈ¶шЗТЈ¬Я@јюКВ°lЙъФЪЙПҙОНРКПЕcкҗӘҡРгөДНРЕЙЦРСлК§ИҘВ“АMҪьғЙДкТФббЈ¬п@өГёьјУлyөГЎЈ
лmИ»¶юИЛЯ@•rФЪЛјПлАнХ“өДҝӮуwЙПҒнХfЈ¬ТАИ»КЗЧуғAөДЈ¬јҙЦРҮшҪӣЯ^¶М•әөДГсЦчфY ҺЈ¬ҫН‘ӘҪЁБўҹo®aлAјүҢЈХюөДЙз•юЦчБxЙз•юЎЈҢҚлHЙПЦРҮшРиТӘөДКЗВюйLөДГсЦчЦчБxәНЩYұҫЦчБxөД°lХ№Ј¬ёщұҫХ„І»ЙПЙз•юЦчБxЎЈФЪЯ@Т»ьcЙПЈ¬кҗӘҡРгббҒнөДЛјПлЈ¬ҪK추Ј§Г“сRҝЛЛјБРҢҺЦчБxј°ЖдЧғПаөДНРВеЛ№»щЦчБxөДБbҪOЈ¬і¬Я^БЛНРВеЛ№»щЈ¬јҙі¬ФҪБЛҪМ—lЦчБx¶ш»ШҡwАнРФЈ¬ҸД¶шК№ЛыіЙһйІ»РаөДӮҘИЛЎЈ
НнДкЛјПлЮDЧғөДһEУx
кҗӘҡРгұ»НРЕЙй_іэЛщТФӣЈ§УРіЙһйКВҢҚЈ¬ЦчТӘФӯТтКЗТтһйНРЕЙЦРСлФЪ1935Дк3ФВУЦТ»ҙОұ»И«уwЖЖ«@ЎЈЦРҮшНРЕЙҸДкҗЖдІэ•rЖЪөД·ҖҪЎұЈКШЈЁҢҚлHЙПКЗҹoЛщЧчһйЈ©РНЈ¬ЮDЧғһйҳOЧуЕЙРВЦРСлөДјӨЯMРНЈ¬јұм¶ҒСЦГёчөШҪMҝ—Ј¬ФЪИХұҫРQКіИAұұөДҮАЦШРО„ЭПВй_Х№ёпГьРыӮчәН”UҙуҪMҝ—Ј¬Ры·QЈәЎёІ»‘ӘФ“ПсК·ҙуБЦЕЙДЗҳУХFҙуЈ¬ө«ТаІ»‘ӘФ“іЙһйОІ°НЦчБxЎЈЎ№ФЪБщӮҖФВ№ӨЧчУӢ„қЦРЈ¬ТҺ¶ЁЧц°Лн—№ӨЧчЈәЈЁТ»Ј©Ў¶»р»ЁЎ·ЦБЙЩіцБщЖЪЈ¬‘ӘЧчТ»ҙОДјҫиЯ„УЈ»ЈЁ¶юЈ©ЯMРРьhғИҪМУэөДЎ¶РЈғИЙъ»оЎ·ЦБЙЩіцЛДЖЪЈ¬ҒKҢ‘іцРВөДЎ¶ХюЦОҫVоIЎ·Ј¬ЦШТӘФӯ„tҶ–оЈэЈ¬ҢҰЯ^ИҘЧчТ»ӮҖіхІҪөДҪYКшЈ»ЈЁИэЈ©НЁЛЧРЎғФЧУЦБЙЩіцИэ·NЈЁ1ЎўҮшГс•юЧhЯ„УЈ»2ЎўЯ^ИҘёпГьҪМУ–Ј»3ЎўҮшлHЎёЧуЕЙ·ҙҢҰЕЙЎ№К®ДкфY ҺК·Ј©Ј»ЈЁЛДЈ©ЙПәЈьhҶTЦБЙЩ‘Ә°lХ№Т»ұ¶Ј»ЈЁОеЈ©ЙПәЈЦБЙЩ‘Ә°lХ№ИэӮҖИәұҠҲFуwЈ¬…ўјУИэӮҖИәұҠҲFуwЈ»ЈЁБщЈ©ЕЙИЛХыоDҸV–ЈьҪMҝ—Ј¬»ЦҸНұұЖҪЎўЗаҚuҪMҝ—кPӮSЈ¬ңКӮдИ«Үшҙъұнҙу•юЈ»ЈЁЖЯЈ©ҮшлHНЁУҚЦБЙЩУРғЙҙОЈ»ЈЁ°ЛЈ©іЙБўЗаДкҲFОҜҶT•юЎЈ
ИзҙЛҙуД‘РР„УЈ¬ЖдҪY№ыЧФИ»КЗҝЙПл¶шЦӘөДЎЈҢҚлHЙПЈ¬НРЕЙөД„УПтТСҪӣұ»МШ„ХЛщХЖОХЈ¬ХэИзТББ_ЙъПтНРВеЛ№»щҸЎҲуМбҫVЦРЛщХfЈәМШ„ХФшПт„ўИКмoұнКҫЈәЛыӮғЎёҺЧ•rТӘЛыҒнЎ№Ј¬ұгҺЧ•rҝЙТФЧҪЛыЎЈ„ўИКмoИзҙЛЈ¬ҢҚлHЙПХыӮҖНРЕЙөДМҺҫіТІИзҙЛЎЈТББ_ЙъФЪНРЕЙРВЦРСліЙБўббХJһй№ӨЧчЧЯЙПБЛХэЬүЈ¬м¶КЗғlУГ„ўИКмo®”·ӯЧgЈ¬Т»ЖрИҘұұЖҪЛСјҜЩYБПЈ¬ТФұгҢ‘Т»ІҝХжҢҚөДЎ¶ЦРҮшҙуёпГьК·Ў·ЎЈ„ўИКмo»ҜГыһйБшиbГчЈ¬ГҝМмөҪТББ_ЙъЧЎөД–ЈьіЗҙуСтТЛЩeәъН¬Т»М–КХјҜёч·NҲујҲЙПкPм¶ХюЦОЎўҪӣқъЎўЮrҙе№І®aьhәНҮшГсьhөИРВВ„Чgіц№©ТББ_ЙъК№УГЈ¬ЦШТӘөДЯҖЧціЙјфҲуЩYБПЎЈ1935Дк3ФВ22ИХФзіҝЈ¬„ўИКмo”yЖЮк‘ЙчЦ®ј°УЧғә¶юГы»Шәюұұ‘ӘіЗҝhФӯҪеКЎУHЎЈөҪЯ_З°йT»рЬҮХҫЈ¬ҫҜМҪТІлSЦ®¶шҒнЎЈЛСІйРРАо•rЈ¬ХэИзТББ_ЙъЛщХfЈә„ўИКмoЎёұнКҫіц»МҝЦҫoҸҲЎЈТтһй·ЗіЈҫoҸҲЈ¬ҫ№ЦВҢўТ»Р©ҝЙТФИлЧпөДОДјюҺ§ФЪЙнЯ…ЎЈЎ№Я@СYХfЎёҝЙТФИлЧпөДОДјюЎ№Ј¬ҫНКЗНРЕЙғИІҝкPм¶ЎёНЖ·ӯҮшГсьhХюё®Ў№өДҝҜОпЎўӮчҶОәНИзәОЎёНЖ·ӯЎ№өДУ‘Х“јҜЎЈҫҜМҪм¶КЗХJһйЧҘөҪБЛ№І®aьhЈ¬°С„ўИКмoТ»јТИЛҺ§өҪҫЦСYҢҸҶ–Ј¬И»ббТЖЛНөҪәУұұКЎёЯөИ·ЁФәөЪТ»·ЦФәҫРСәЎЈұұЖҪКРьh„ХХыАнОҜҶT•юөГУҚЈ¬БўіЦ№«әҜ°С„ўИКмoХЈыөҪФ“•юҢҸАн·QЈәЎёЩFФәјДСә№І·ёБшиbГчЎЈФЪӮЙІйЖЪйgҪӣұЦ•юМбіцФғҶ–ҫҖЛчкPӮSЈ¬ғA·оЦРСллҠБоһйБшиbГчјҙ№І®aьhНРЕЙоIРд„ўИКмoЈ¬°ёЗйЦШҙуЈ¬ЧЕұЦ•юШ“ШҹСәҪвЛНҫ©ЮkАнЎЈЎ№Ј§51Ј§„ў·тӢDПИЮDЛНұұЖҪКР№«°ІҫЦЈ¬5ФВ8ИХЦұҪвДПҫ©ЎЈьh„ХХыАнОҜҶT•юәҜ·QЈәЎёЩFҫЦЦ®№І·ё„ўИКмoЎўк‘ЙчЦ®Т»°ёЈ¬¬F·оЦРСллҠБоҪвҫ©УҚЮkЈ¬ЖқМШЕЙҶTё°ЩFҫЦҢўФ“„ўк‘ғЙ·ёМб»ШЎЈЎ№Ј§52Ј§
„ўИКмoФЪЕcкҗӘҡРг ҺХ“•rЈ¬ұҫҒнҫНХJһйЦ»УРҪӣқъҸНЕdббІЕУР—lјюёгёпГьЈ¬ббҒнКЬкҗ·ҙҸНЕъФuәНЧIЦSј°ЗаДкНРЕЙҳOЧуЕЙөДүәБҰЈ¬ІЕГгҸҠ·Е—үУ^ьcЎЈФЪХюУ–ИЛҶTөДй_Ң§ПВЈ¬ЦШ“мЦРҮш¬FФЪ‘ӘФ“°lХ№ЩYұҫЦчБxҪӣқъөДУ^ьcЎЈЮDИлДПҫ©·ҙКЎФәббЈ¬ТФЖдАнХ“ЦӘЧRЧц„eөД·ёИЛЎёй_Ң§Ў№№ӨЧчЎЈіцФәббН¶ұјФӯЎёОТӮғөДФ’Ў№НРЕЙ№ЗҺЦБәҺЦҶМЦчіЦөДУ–ҫҡ°аЈ¬Ф“°аКЗ°ьҮъСУ°ІөДәъЧЪДПЛщЮkЈ¬ҢЈйTҸДКВ·ҙ№ІРыӮчҒKҢҰН¶ұјСУ°ІөДЗаДкЯMРРЎёХюУ–Ў№ЎЈИ»ббФЩ°СӮҖ„eЎёХюУ–Ў№Я^ҒнөДИЛЕЙё°СУ°ІЎЈ“юҙЛЈ¬ФЪСУ°ІХыпLЯ„УЦРЈ¬ЦР№ІЎёдzјйІҝЎ№Ш“ШҹИЛҝөЙъФЪГ«қЙ–ЈьЦ§іЦПВЈ¬ҪиЎёЧҘМШ„ХЎ№Ц®ҷCҢҚК©ьhғИЗеПҙЈ¬ЖИәҰҙуБҝҸДҮшҪy…^Н¶ұјЎёёпГьИЫ tЎ№СУ°Іј°ёчөШёщҫЭөШөДЦӘЧR·ЭЧУЈ¬ФміЙҹo”өФ©°ёЎЈІ»ЙЩИЛЧФҡў»тұ»ҡўЈ¬ЯҖГАЖдГыФ»Ўё“ҢҫИЯ„УЎ№ЈЎ
„ўИКмoФЪұұЖҪұ»І¶ЛДӮҖРЗЖЪТФббЈ¬ФЪЙПәЈөДНРЕЙҪMҝ—УЙм¶Т»ӮҖ»мЯMЛ®лҠ№ӨИЛНРЕЙҪMҝ—өДҮшГсьhМШ„Хёж°lЈ¬К·іҜЙъөИЛДГыіЈОҜФЪТ»ҙОй_•ю•rУЦұ»Т»ҫWҙтұMЎЈЈ§53Ј§НРЕЙЦРУРИЛХfғЙӮҖНвҮшИЛАоёЈИКәНТББ_ЙъТІН¬•rұ»І¶Ј¬ТтһйЛыӮғөДЎёСуИЛЎ№Йн·ЭЈ¬ҙтБЛТ»оDбб·ЕБЛЎЈ№PХЯФш°СЯ@ӮҖЗйӣrҢ‘ЯMУЙМЁһі–ЈьҙуҲD•ш№«Лҫ1994Дкіц°жөДЎ¶ЦРҮшНРЕЙК·Ў·ЎЈ¬FФЪҝҙҒнУРХЎ®ЎЈРВ°l¬FөДТББ_ЙъПтНРЕЙҮшлHМбіцөДӮдНьдӣЦРХfЈәЎёGН¬ЦҫЈЁјҙАоёЈИКЈ©ЕcҫҜ·ҪЦ®йgТІ°lЙъБЛТ»ьcјmёрЈ¬ҫҜ·ҪФзЦӘөАЛыәНОТӮғҪMҝ—УРкPӮSЈ¬І»Я^ЦұЦБДҝЗ°ЈЁјҙ1935Дк8ФВЈ©һйЦ№Ј¬ЛыӮғІ»ФшҢҰЛы’сИЎИОәОРР„УЎЈЎ№
ТББ_ЙъФЪұұЖҪөД»о„УУЙ춄ўИКмoөДұ»І¶Ј¬ұұЖҪҶTҫҜ¶аҙОЙПйTұPІйЈ¬¬FФЪұұҫ©ҷn°ёр^СYЯҖУР¶ајюұPІйУӣдӣЈ¬ө«ӣЈ§УРҙюІ¶өДУӣдӣЎЈТ»КЗТББ_ЙъіЦУРГАҮшЧoХХЈ¬ЦРҮшІ»ёТЭpТЧГ°·ёЈ¬¶юКЗҝЙДЬВ РЕБЛ„ўИКмoөДҝЪ№©ЈәЎёТББ_Йъ®”ИХФшЭoЦъ№І®aьh№ӨЧчЈ¬іцҝҜЎ¶ЦРҮшХ“үҜЎ·Ј¬¬FФЪТСФзЕc№І®aьhГ“лxкPӮSЈҝЈҝ¬FФЪөДЛјПлј°ЖдХ“КцҢҰёч№І®aьhЦ®№ӨЧчЗйРОІ»®”Ц®ьcЈ¬ҫщУРЕъФuЈ¬№КЖд¬FФЪЦ»ҝЙФЖН¬Зй№І®aЦчБxҫ№І»қMТвм¶ҮшГсьhЈ¬ФЪҝНУ^өШЧчТ»ҢWЧRЙПЦ®МҪУ‘ЎЈЎ№Ј§54Ј§ЛыІ»ҫГлxИAЈ¬»ШҮшҢ‘БЛТ»ұҫЎ¶ЦРҮшёпГьөДұҜ„ЎЎ·ЎЈФЪҢ‘ЧчЯ^іМЦРөГөҪБЛНРВеЛ№»щК®·ЦҫЯуwөДҺНЦъЎўЦёҢ§ЎўҢҸйҶәНРЮёДЈ¬Я@КЗТ»ұҫұИЭ^ҝНУ^өДЎўШһҸШНРВеЛ№»щЛјПлөДЦРҮшҙуёпГьК·Ј¬ЕcМKВ“ј°ҮшлHҙъұнҪЯБҰСЪЙwәННбЗъХжПаөДЦРҮшҙуёпГьК·У^РОіЙхrГчҢҰХХЈ¬Т»•rіЙһйЮZ„УКАҪзөД•ідN•шЈ¬УИЖдһй·ҙМKөДОч·ҪҮшјТЛщҡgУӯЈ¬ТІКЗЦРҮшНРЕЙҪЯБҰНЖізөДТ»ІҝҪӣөдЦшЧчЎЈ
ЦРҮшНРЕЙФЩҙОКЬҙЛЦШҙуҙт“фЈ¬К№РВЦРСлЦШХсҪMҝ—өДТ»ПөБРУӢ„қәНЕ¬БҰУЦё¶Ц®–ЈьБчЎЈҪMҝ—УЦПЭм¶Т»Ж¬»мҒyЦ®ЦРЎЈАоёЈИКХТөҪкҗЖдІэЈ¬Ҷ–ЦБЙЩһйБЛ»ЦҸНТ»Р©ҢҚлH№ӨЧчЈЁіц°жЎ¶»р»ЁЎ·өИЈ©Ј¬КЗ·соҠТвәПЧчЎЈАоҢҰкҗөД‘B¶ИәЬЖж№ЦЈ¬ЎёҢҰЛыВ•ГчЈәЯ@КЗһйБЛ№ІН¬№ӨЧч°СҪMҝ—ёг»оЈ»ө«ФЪХюЦОҶ–оЈэЙПЈ¬ЛыЈЁкҗЖдІэЈ©өДұ»й_іэИФЕfУРР§Ў№ЎЈЈ§55Ј§Я@ДДКЗЙхьNәПЧчЈ¬әҶЦұКЗОкИиЎЈм¶КЗЧФИ»І»ҡg¶шЙўЎЈ
РТМқЯ@ДкПДМмЈ¬НхОДФӘФЪаlПВрBІЎббУЦ»ШөҪЙПәЈЎЈЛыҝҙөҪЈә
ҙЛ•r„ўИКмo„ўјТБјӮғәПСЭөДұҜПІ„ЎТСҪӣКХҲцЎЈТЧВеЙъЧЯБЛЎЈАоёЈИКЯҖФЪЎЈоIҢ§ҷCкPёщұҫӣЈ§УРЈ¬ДЗ•rИ«ЙПәЈҙујsЦ»УР¶юК®рNӮҖ·ҙҢҰЕЙН¬ЦҫЎЈҙујТУXөГ·ЗЦШРВҪMҝ—І»ҝЙЎЈЈ§56Ј§ӘzЦРөДӘҡРгҢҰҪMҝ—әЬкPРДЈ¬ЛыҢ‘РЕіцҒнЈ¬ЦчҸҲУЙкҗЖдІэЎўЪwқъәНОТЈ¬•ә•rіЙБўТ»ӮҖИэИЛОҜҶT•юЈ¬ЧЕКЦХыАн№ӨЧчЎЈ
АоёЈИКТІҸДЯ@ҙОКВ№КЦРјіИЎҪМУ–Ј¬ЛЖәхІtҪвөҪТ»Р©ЦРҮшҮшЗйәНфY ҺөДМШьcЈ¬Цч„УЗ°ҒнЕcкҗЖдІэј°ТьҢ’әНҪвЈ¬ҪӣіЈЕcЛыӮғТҠГжЈ¬ТІҳOЕОҪMҝ—ДЬүтғҚҝм»ЦҸНЈ¬ТФҸӣСaЯ^ИҘГ°К§ФміЙөД“pК§ЎЈө«КЗЈ¬й_Кј•rЈ¬кҗЖдІэТтКЬБЛМ«ЦШөДҙт“фЈ¬І»М«оҠТвіцЙҪЎЈУИЖдКЗкҗӘҡРгЈ¬“бГюЧЕЎёАПГ«ЧУЎ№К·ҙуБЦј°ЖдҒнИAҙъұнӮғҸҠјУөДӮыНҙЈ¬ҢҰЎёГ«ЧУЎ№НвҮшИЛАоёЈИКөДҗәБУЧчУГёьјУІ»ҝЙФӯХҸЈ¬ЙхЦБЎёИf·Ц…’җәЎ№Ј¬ЎёҪУЯBҢ‘іцРЕҒнЈ¬БҰЧиОТӮғФЩәНЎәГ«ЧУЎ»әПЧчЎЈЎ№НхОДФӘІtҪвЯ@·NЗйӣrббЈ¬ЕcАоёЈИКНЖРДЦГё№өШХ„БЛТ»ҙОФ’ЎЈҪY№ы°l¬FЈәЎёЯ@КЗТ»О»әЬЦТәсАПҢҚөДН¬ЦҫЈ¬Ҫ^·З№ЩБЕЈ¬Та·ЗГ°лUЦ®НҪЎЈЛыЦ»КЗТ»РДТӘПл…ўјУ№ӨЧчЈ¬ПЈНыіГЛыФЪИAЦ®ҷCЈ¬ДЬҪoҪMҝ—ТФ¶аЙЩҺНЦъЎЈҝЙП§өДКЗЈ¬Я^ИҘЛыөДҹбРД…sЧҢ„ўИКмoөДТ°РДҪoАыУГБЛЈ¬ТФЦВОҙДЬіЙКВЈ¬ТЦЗТ”ЎКВЎЈЎ№
НЁЯ^Я@ҙОХ„Ф’Ј¬ЦРҮшНРЕЙЯҖЕӘЗеБЛАоёЈИКөДХжҢҚЙн·ЭЈ¬јҙҒKІ»КЗ„ўИКмoөИТ»ПтЛщХfөДЎёҮшлHҙъұнЎ№Ј¬Ц»КЗТ»ӮҖҮшлHЕуУСЎЈАоПтНхаҚЦШВ•ГчЈ¬ЛыЦ»ТтВҡҳIкPӮSҒнЦРҮшЈ¬ТтһйКЗНРЕЙТ»·ЦЧУЈ¬ҫНТӘХТҪMҝ—…ўјУЈ¬ЛыҸДІ»ФшПтХlХfЯ^ЛыКЗЙхьNЎёҮшлHҙъұнЎ№ЎЈЛщТФЈ¬ЛыөГЦӘ„ўИКмoөИТ»Пт°СЛыХfіЙЎёҮшлHҙъұнЎ№Ј¬М§ФЪјзЙПЈ¬ФЪЦРҮшН¬ЦҫЦРХР“uЧІт_Ј¬Ўё·ЗіЈҡв‘ҚЎ№ЎЈ
ҪӣЯ^Я@ҙОңПНЁЈ¬ТФј°ТББ_ЙъЕcНРВеЛ№»щТҠГжббЈ¬НРКПЕcАоёЈИКј°ЦРҮшНРЕЙЦШРВҪЁБўБЛҫoГЬВ“АMЈ¬АоёЈИКЕcЦРҮшНРЕЙөДкPӮSөГөҪБЛёДЙЖЈ¬ҢҰҪсбб№ӨЧчөДЯMРРИЎөГБЛТ»ЦВөДТвТҠЎЈНхОДФӘҫНӣQРДНЖ„У»ЦҸНҪMҝ—өД№ӨЧчЎЈЛыХfЈәЎёІ»ҫГЈ¬ҸДТ»ҙОЙПәЈ¬FУРН¬ЦҫөДҙъұн•юЧhЙПЈ¬НЖіцБЛТ»ӮҖЕR•rЦРСлОҜҶT•юЈ¬ЖдЦР°ьАЁкҗЖдІэЎўТьҢ’ЎўКYХс–ЈьЎўАоёЈИКәНОТЎЈҙЛ•rӘҡРг·ҪГжЈ¬ТтөГЖдІэЎўЪwқъәНОТөДІ»”аҪвбҢЈ¬ҝӮЛгҢҰЎәГ«ЧУЎ»өДәПЧчТІХҸҪвБЛЎЈЎ№Ј§57Ј§
НхОДФӘТФЙПөД»Ш‘ӣЈ¬Еc1980ДкҪвГЬөДНРВеЛ№»щҷn°ёЦР°l¬FөДТ»·Э•юЧhУӣдӣУРьcіцИлЎЈЯ@·ЭГыһйЎёЦРҮш№І®aЦчБxН¬ГЛЈЁІј –КІҫSҝЛЎӘЎӘБРҢҺЕЙЈ©ЕR•rОҜҶT•ю•юЧhУӣдӣЎ№Ј§58Ј§өДҷn°ёұнГчЈәЯ@ҙО•юЧhХЩй_м¶1935Дк12ФВ3ИХНнЈ¬іцПҜХЯіэЙПКц®”ЯxөДЦРСлОҜҶTНвЈ¬ЯҖУРФӯЕRОҜіЙҶTЩRПЈЎўЙЫф”ЎЈ
Я@Дк8ФВТББ_ЙъПтНРЕЙЕR•rҮшлHәННРВеЛ№»щҸЎҲу•rЈ¬Фш°ҙХХНРЕЙЦРСлӣQ¶ЁЈ¬НЖЛЈ§БР –КҝЈЁ„ўИКмoЈ©ЎўК·іҜЙъ¶юИЛ…ўјУҢўТӘіЙБўөДөЪЛДҮшлHоIҢ§ҷCҳӢЎӘЎӘЎёҝӮАнКВ•юЎ№ЎЈУЙм¶НРКПҲФіЦкҗӘҡРг…ўјУЈ¬ЧғіЙБЛИэИЛЎЈ¬FФЪ„ўЎўК·¶юИЛТСҪӣұ»І¶Ј¬УЦӮчҒн„ўТСҪӣЧФКЧЈ¬ЯMИлЎё·ҙКЎФәЎ№өДПыПўЈ¬¶шК·іҜЙъУЦКЗҙујТНҙәЮөДИЛОпЎЈм¶КЗЈ¬•юЧhЧЕЦШУ‘Х“БЛкҗӘҡРг…ўјУҝӮАнКВ•юКЗ·сәПК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