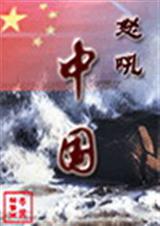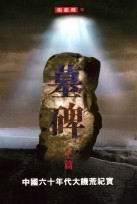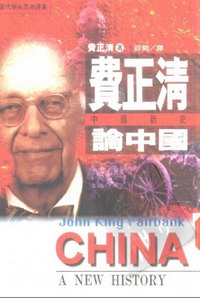Ĺ��-�й���ʮ����ļ�ʵ-��1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ӵ���Ա����ͥ����9����Ϊ12������ʡ�﹫��������ֱ��Ѻ�͵�������������������ù������������ӵ�¿Ȧ������������ﵱ��������Ա��
1958��7��15�գ�����Ժ������̷�����ں���ʡί�ɲ������ϵĽ�����һ��ʼ��ף�أ�������������ϵ�ͬ־��ϲ����ף�غ���ʡ�ļ�����գ�Ҳף�غ���սʤ�����˸���Ϊ������������壬�ε�����һ����죬Ҳף�����ǹ���������֥��ͬ־Ϊ����һ����졣��̷��������ף���ڻ᳡�ϵõ��˱������������������ı�����ǿ�������ζ����ı����ꡣ�������ض������ˡ�С�˸���������Щ��С�˸����������ܵĴݲб��˸������صöࡣ�ݹ��ƣ�ȫʡ������С��������ʮ�����ˣ��������ĸɲ�Ⱥ�ڲ���20���ˣ��ݲ�����һ�ٶ��ˡ�
���ģ�����ζ�����ס�����ǵ��죬Ϊ˵�ٻ�ɨ�����ϰ���˭Ҫ�Ը߲����ǡ������硢��������������ɣ�˭���Ǹ����������Ĩ�ڡ����ͻ��Ϊ�������ɡ����������ɡ��Ǻ͡��ˡ��������վ��һ��ս���ϵ��ˡ����ͻ��Ϊ���۶�����ʱ����ν�����ۡ������Dz��ò�ͬ�������˵�����ڳ��о��ǶԲ�ͬ����������У�˵�˼һ�����·�ߡ���Ծ���������磬������ñ�ӡ���ũ�壬�����ۡ����ǿ�ͷ�ϵ����磬���������ݲС�һ������ͬ�Ŀ������ͻ�����˵�����������������ͻᱻ�����Ų��������᳡���ģ�վ�ã���������ͷ��������ѵ�⡣
˭��˭�ǣ�Ⱥ�������������ũ��ͬ���˸�������������֥�ԣ�ʡ�������IJ��������֥�Ե����֣���ũ����ţʺ�������ˡ�
��������ʡ���ˡ���Ծ����������
��1957����Ͼ���7�������ɷ����Ժ�֪ʶ���Ѿ�����������1958���־������������������š����ڵ��ںɲ����γ������θ�ѹ���գ���û���˸ҽ��滰�ˡ��й�ȫ���˴���λ���ոս�����ʡί����ġ��������ۡ��Ͼͷ�������֥�Ե���Ϊ��Ծ������ѧ����ѧ��Ծ�����ij��ģ�ʹ����Ψ���۽�һ����չ�����ٻ����������쿪������ʡ�ݳ���һ�����־磬�����������ϰ�������˾�����ѣ�Ҳ��ȫ�����˺ܲ��õ�ʾ�����á�
�����˸�������֥�Ծͳ��˺���ʡ�ĵ�һ���֡����Ƿ����й������ٵģ���̨�Ժ�������ҡ��Լ�����̬�����С�������족�����ߡ�ʹ���ϳ���ȫ��עĿ�ĵط���
��ʳ�����Ÿ߲������ǡ��Ǻ������ȸ������ģ��������Ǻ������ȴ���ģ�������ѧ������ˮ���������ֲҲ���Ժ��ϡ����ϲ��ϵس����飬�������ձ����������ܺ��ϵľ��顣�ڵ�ʱ���ǵ����У�����ʡ�Ѿ���Ϊȫ������Ծ���������ġ�
1��ˮ�����費����ѧ�������˲�
ˮ����ҵ���ǵ������ܹ���ɵģ���Ҫ���и��������������Ȩ�ƶ�������������ơ���Ϊ��������ȫ������Դ�������Ե���ȫ����������������¡�ƽ�Ķ��ۣ���ë��������ʱ���й���ˮ����ҵ�����гɼ��ģ��е�ˮ�������ڵ�Сƽʱ�������ܻݡ����ǣ���ʱ������������ͷ�����ϰ������������Գ��ܵ��������ڸ�ˮ������ʱ��������ѧ��ֻ�����ɣ��Գֲ�ͬ������˼����Ⱥ���ʹ�ò���ˮ������ʵ�ʳ��˴�������ƺ�����Ͽˮ������������͵Ļ���������Ͽˮ������û�г�ֿ�����ɳ���⣬̧���˻ƺ����ε�ˮλ��ʹμ�ӳ�Ϊ�߳���������ӣ������2003����μ��ˮ�֡�
���ϵĴ�Ծ�����ȴ�ũҵ��ʼ�ģ���ũҵ��Ծ�������ȴ�ũ��ˮ���˶���ʼ�ġ�1957��10�£�����ʡ�ٿ�ˮ���������飬����᳹ȫ��ˮ�����龫�����֥���ٿ���̸�ᣬҪ������ӭ��ˮ�������Ծ�����й�������Ǵ���ǡ�������̷�������Ը��ὲ����11�µ�12�³���ʡ�������ٿ��ڶ��λ��飬��֥�Է������������ƣ�����ʡίָ��˼��ġ�����������������֯��ũҵ������Ծ��������ǰʵ��ȫ��ũҵ��չ��Ҫ���ﵽ���ý���ȫ���Ծ����̷�����ٴθ��ὲ����12��7�գ�����ת���˺���ʡί�ġ����������ȫʡ1500���˲μӿ������������Դ���ˮ���ʹ�����Ϊ���ĵĶ��������˶���Ͷ��������991���ˣ�ũ������˴�Ծ�����档���ǣ�1958��Ԫ���չ�������ʡ���ء��С����쵼��ũ��ˮ�������˿��ᣬ��֥����֯����1958��ũҵ��Ծ�������ȫʡ����ˮ��700��Ķ�����������ӵ�3��000��Ķ�ĸ�ָ�ꡣ1�µף���֥����ʡ��ί��������Ϲ᳹�й������������龫��������ʵ��ˮ����������ʵ���ޡ��ĺ���������ʵ��ũҵ��Ҫ����ʳ����Ŀ�꣬����������ä���ռ����С�Сѧ������
����֥��˵������ʡͶ��1958���սˮ��������1500��1957��10����1958��6�£������������ʯ��88����������ˮ����262�������������������ﵽ12546��Ķ������ɵ���ʯ���൱�ڡ�����48���������˺ӡ���ʵ���ϣ�1957��ȣ�1956��10����1957��9�£�ȫʡ������ˮ������ֻ�������ʯ��2909����������������Ծ����1960��ȣ�1959��10����1960��9�£���Ҳֻ�����ʯ��1��34��������80���ĩ�����ϵ���ˮ����ֻ��150����������80�����ȫʡ������Ҳֻ��5000��Ķ��ȫʡ�ط��ʽ����Ͷ��ˮ�����裬1958�����1��6��Ԫ��1959�����2��1��Ԫ�����Ⱥ��Ͷ���Ͷ����ʡ�����Ͷ����ʽ��������Ӽ����ˡ�
1958��ͬʱ��9������ˮ��ʩ������ƿ����ܺʹﵽ600�������ף�����7��ʡ�����ˮ����ݴ�46�������ף���������Ҫ�ں��Ͼ��ڵĵ�����ˮ�⣬Ͷ�������3���ˡ�1959�꣬ͬʱʩ���Ĵ���ˮ���Ѵ�11�������ϼ�ʮ������ˮ�⣬�ʽ������ԶԶ�������ϵ�ʱ�ij������������й��̾�����ơ���ʩ������ѧ̬�ȱ���������ڡ������档��ƽ̨��Ѽ�ӿڹ��̾�Ȼֻ��һ�깤�ڣ���Щˮ����Ϊ����β�����̣�һֱ�ϵ�60������ڻ�70����ŵ��Կ��������⣬���ϴ�Ծ���ڼ仹���˹�����������1957��11����1958��7�£��������ɹ��1000��Ķũ���ʵ��ֻ�ܹ��12��Ķ������ȫ�����ϡ�����������������կ����Ծ������1958��3����1958��8�£����ƻ����ûƺӹʵ���ˮ40�������ף�Ҳδ�ﵽĿ�ġ�1959��11�£�λ��֣�ݻƺ��ϵĻ�����Ŧ������13���������������1960�������������滮���ʧ���ò�ը����ӡ�������ϵ���̻��з����������������������δ�յ�Ӧ��Ч�档����ǿ��ͻ���ﵽ������ָ�꣬���ϴ������ƺ�ˮ�����������ش����μ��1961���μ�����519��88��Ķ�������ƻ�ũҵ��̬��19581959�꣬����ƽԭ���������������˹��˺ӣ���ͼ�Ѻ��ӡ����ӡ�������ƺӴ��������������ִ�㡰���ٽ�ϡ������ϵ������ƽ�ض�������ˮ�أ�����ν��һ��ض�һ���족��������Ϲָ�Ӻ���������֮�£�������ͼֽδ��������δ�ţ����ѻ��������������¡���������ˮ����û�н��ɵ������̵�����£��ͽ���Ӻ�������1960��5��17��ҹͻ������ʱ����ӳ�٣���2000�˱�������
��ˮ�������ϵ�ũ���¼��䷱�ص������Ͷ���ͷ�����»��ܳԱ�������1958��10���Ժ��Լ�1959���1960�꣬�����϶��Ŷ��Ӵ��·����Ͷ���ˮ�������ϵĸɲ����缫Ϊ���ӣ���ũ���������ʹݲУ���ˮ�������϶������������������������������1960��12��6���ں���ʡ������˵������ʼ���������ˮ�������ϾͶ���17000���ˡ��ϲ̣��²̣���ɽ����ƽ��ԥ��������������ˮ�������ϴ���������Ҳ�ܶࡣ
4����š����ǡ���ũ������
ë����1958��3��8����26�յijɶ������Ͽ϶��˺��ϣ�Ҳ�϶�����֥�ԣ��Ժ���ʡ�ĸ�ָ��ʹ�Ծ�������ؼ������á���֥�Դ������ϲμӳɶ����飬������ǰ��ָ���ʱ�䣬��Ԫ��ʱ��ʡί�����ٴ����ǰ������ë��ŵ������һ����ܹ�ʵ���Ļ�������ɱ伯��������Ϊȫ�������ơ�ë����3��20��˵�����������һ��ʵ���ġ��塢�ˣ��������߰����ƺ��Ա���ʳĶ���İٽ����Ķ����ٽ���ӳ������ϰ˰ٽ����ë����ũҵ��չ��Ҫ������ij�ԶĿ�꣬����˵һ�����ɣ���ˮ���������ĺ���������ä��������Щ���������������ú�������һ�ꡣ����������ˣ������ʡ����һ���˶�����Ծ�������á�����˵һ����ʵ���Ļ���������ȱ��ܴ������ǹ����ֲڣ�Ⱥ�ڹ��ݽ��š�����������У�ë�����������ϵ�ˮ����������·�ߵĶ������������ϵ�ˮ��ȫ����һ����4800��Ķ������ë�϶������֣�����1957��ʵ��ָ���2��4������Ȼ��ë��Ҳ�����ζԺ���ʡ�ĸ�ָ���ʾ���ǣ�������֥�Ի��ǹ�������������
4�£�����ʡί�ڰ˴�ȫ���ϣ���֥�Բ���ȫʡ��Ծ���������ʳ�ܲ��ﵽ275300�ڹ������ʵ��ˮ���������ǣ���ȫʡ��Χ�ںܿ������˸���硣1956����������һ������������ǣ����ԣ�1958�꣬�й�ũ��Ͱ�ũҵȡ�úܸߵIJ�����Ϊ���ˡ����ǡ����������ǡ����ǡ�����硱��ͻ���ı��֡�
������Ǵ�1958�����տ�ʼ�ġ���ƽ�؍��ɽ���磨����ȫ����һ�������磬��ʼ�����������磩��¥��Ӷӳ�����������Ů�ӳ�����������2Ķ9�ֵص������С��ȷʵ���ò����������ո��ʱ�����糤�ӵ������ˡ��ѳ������������Ƚе���Ӳ�������һ���������顣�ӵ���˵�����ϼ�������Ūһ�Ÿ߲����ǣ�����ȫ����һ�������磬������Ӱ�춼�ܴ������ǻ��У�ֻ�з��˸߲����ǣ�����˵�����������Խ�ԡ���������Ϊ�������⣬Ϊ�����⣬ҲΪ���ǹ������⡣�����ǵ��������ǵ�ʱ���ˣ�ϣ�����ͬ��ͬ�£�����Э��������顣���������ʣ���Ķ�����ٲ���������أ����ӵ���˵��������Ķ��3000�������������ִ��һ���ӳ�Ĭ�ˡ���ȥһĶ�Ŵ�100��һ���Ӵ���ô�࣬�Dz���̫�����ˡ��ӵ���˵�����ҿ�������������ﲻ����������ɣ��������˵���������ٶ�Ҳ����Ķ���߰˰ٽ���ӵ���˵������Ҷ�����취���ܲ��ܹ������������������������һ����������벻���취�����������˵����Ҫ���������ǣ����ǰ���10Ķ�ص����ӷŵ�һ����ӵ���˵������ѽ��Ū��һ��������𣡡������˵�����Dz��Ǻ����𣿡��ӵ���˵������û��ȫ�����ڵ����ƣ���������������˵����Ҳ��Ϊ���������⣬Ϊ��������£����Ǵ���Ҳ�Ǻ��ģ�Ҫ�������Ͽ��������������������ҹ������ʹ�����ӣ��ܹ�11178���2��9Ķ�㣬ƽ��Ķ��3854����۵������ѣ���3530���ϱ����ڶ��죨1958��6��12�գ����������ձ����������»�����߷�諵ı�����
���ǹ���ų��ڶ�������2Ķ9��С��Ķ��3530�
�̺�����ƽ������ũҵ��ڶ��������5ĶС��ƽ��Ķ��2105�����Ϣ����֮�������Ϣ���ڡ������ձ���6��8�յ�һ�棩��������С�������������10�յ�һ���2�ֶ�����2Ķ9�ֵ��ܲ����ﵽ10238��6�ƽ��Ķ��3530��75��ȴ�ӵ���߲���ÿĶ��1425���������ȥ��ÿĶ750���3�����ࡣ�������漣��2�ֶӶӳ������������ӳ������ʡ���֧ί����𡢼���Ա�¸��͡�����Ա�º��˵�6����С���������������������ġ�
���2Ķ9�ֵص�С���ر�ã�����ҳ����������������ܾ��ȣ�ÿĶƽ����120�����ꡣ������ǰ��ȫ�ظ�������Ⱥ�ں�ũҵ����Ա���������˲ι����ȡ�10�գ���2Ķ9�ֵص�С������ʱ���ڴ����ϼල���ﳡ���ӵ����й���ƽ��ίίԱ��ũ�����������±������������糤�����ᡢ�������糤�ӵ���������ӵĸɲ�������кü�ʮ����Ա�����������������κ��㡣���ؽ��й����������������ʵ��ȫ�ɿ���
����
����DZ������ߵ�ͬ�£���ǰ�����������ݶ��꣬�������������ε������У�����һλ�Ͱ����ĺ���̫̫������75���ʱ��������������������¡�̸�������ʷ�������겻�ѡ������Ƿ�������Ѱ�����ǵģ���ȥ����������쵼ͬ־˵��¥����һ��Ķ��3583������ǣ����Ž��ɡ������ֳ�һ�����濴���˺ô����ڣ����ǵ���������쵼���ijӣ�������Ȼ�е��ֹ���Ҳ����������ʣ�ֻ����ʵ������˭֪�Ǽٵģ������������µ����ߣ����µ�ֻ�Dz������ź������ǵģ���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