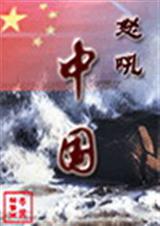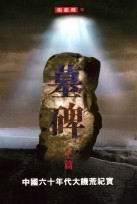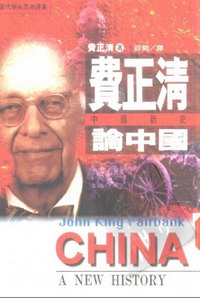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 2004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月26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现在增长50%。” 粮食部党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6283亿斤,比去年的3899亿斤增加2384亿斤,增长61.44%。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 于是,浮夸风越刮越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1958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10%-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7500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1957年的产量3700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8500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300-500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1959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4亿亩左右,比1958年减少了20%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10500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2000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9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 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200多亩。 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所不惜96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8年少17700万亩,即减少10%弱。 这大概是1959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月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亿斤,公布数为7500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亿斤,1980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4000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 1113。35亿斤比正常年景的850亿斤高出263。35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87万人。 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400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1。016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
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年10月4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亿斤,销售粮食211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亿斤,农村多销12亿斤。全国9月底,粮食库存41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斤。有17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从1959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年2月21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 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1959年1月27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