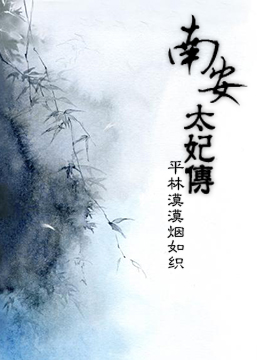望江南-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手上有钱,我就心痒起来,再次跟周顾提起“识字班”的创立。
早在前年我就想创识字班了,但周顾强烈反对。那时我手上的事情也多,忙昏了头,也就没有坚持。但是现在,我想应该是时候了。
“为什么?”周顾耐性的问我,眼中还是有种研究的味道。“四姑娘,妳到底想做什么?”
我真的没想做什么,只是不耐烦一遍遍的教人怎么种粗粮、如何堆肥,宣讲庄园制度和规矩
“…这些只要写成册,让庄头去照本宣科就行了,我实在不想那么累了。”我继续争取这个“说明书”,“而且如果识字,那么咱们的人就不会被读书人呼咙,自己也能看懂官府告示,最少能够自己看书信,不用别人代读…”
他的眼神奇怪起来,“…妳要让村里的孩子去考秀才?”
“不是。”我不耐烦了,“读书人有什么好做的?空谈误国。你瞧县令州牧都是亲民官呢,干些什么好事了?真真不如我…我只希望他们能自己读三国话本就好。能够自己写农业心得当然更好,种田也是很多学问的,这些学问流通范围太小,又容易失传,实在太可惜…”
我对这点有很深的感触。虽然来自二十一世纪,我读得又是农科。但除了知道粗粮抗荒的潜力,我还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许多知识,还是天天骑驴外出逛去逛出来的。
就算是农夫,也分三六九等。有那种非常聪明、经验非常老道的老农,真的值得人尊敬。对于天时的预测,恐怕比官方的钦天监厉害好几万倍。我现在都不敢小看农民历了。那是多少智慧的结晶啊!却不受人重视,多令人感伤。
我兴奋的哇啦哇啦半天,周顾的眼神却越来越奇怪。“四姑娘,农官能由民间培养吗?”
一下子我就泄气了。“…那官方就拿出办法来啊!”
周顾沉默的盯着我,我也瞪着他,满心愤怨。
“好,我知道了。”他终于开口,扯出半个笑脸,“妳要自己能看话本的农夫,而不是要教养出读书人。”
咦?虽说出入不大,但他似乎省略太多了…
不过他同意就好。说真话,我实在很欠缺自觉,总是不经意间就触犯这个时代的底限。
但我没想到他真的找了说书先生来当老师,并且将三国话本当课本,从中摘出生字。这让我大为惊吓。
这这这…这不就是中英对照读本的精神吗?周顾该不会也是穿过来的吧?
“穿?穿什么?”他大惑不解,又露出那种浓重研究的表情。
我赶紧闭嘴,若无其事的喝茶。反正他提不出任何证据,正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
见我不答言,他也就从善如流的转了话题。之所以办个识字班也这么小心翼翼,实在是十年前薄麓书院的学生串联拒考抗议科举不公,闹出有史以来“朝廷抄书院”这种有辱斯文的事情,许多官员都被牵连,现在连启蒙私塾都战战兢兢,唯恐被扫到台风尾。
时间过了这么久,创书院还是个禁忌的话题。
所以周顾巧妙的回避了“创学”的敏感性,直白的只注重“读”的能力。
讨论了一会儿,周顾冷不防的问,“四姑娘,妳叫什么名字?”
“殷…”说出我穿前的姓,我才悚然惊醒。这家伙真的太阴了,趁我最专注的时候攻其不备。“闺名不能随便告诉人的。”
周顾轻笑,“妳是四姑娘,却绝对不是曹四儿。”
我的手心,沁满了汗。
所谓攻击乃是最佳防御,我很快的反击,“那么周先生,你真的是周顾吗?”
他挑起左眉,“妳知道我的意思的。”
我也学他的表情,“你也知道我的意思的。”
对峙了一会儿,他先放松了表情。“顾是我的字。”
“半个字吧。”我顶回去,“哪有一个字的字。”
“没错。”他坦然承认,“我字子顾。”
“抱歉,我没有字。”我咳了一声,“识字班就这么定了吧?”
“嗯,就这样。”他眼光在我脸上转了一圈,含着笑,“四姑娘,妳说过我俩有半师之缘,我替妳起一个字,就叫薛荔,如何?被薛荔兮带女萝。”
就算再迟钝,我也知道这不是下对上的态度。虽然我也不喜欢那种主从礼节。虽然我书背得很惨,到底也知道这句是楚辞九歌的“山鬼”。
皱紧了眉,“…谢谢赐字。”
我算是侧面承认了他的猜测,但其它的也不会对他讲。我怎么讲?说我的魂魄来自五百年后?别说他多么超时代,要不他就去找大夫证明我发疯了,要不就叫道士来收妖。
他又看了我一会儿,似不经意,又似开玩笑,“青要之山霜雪如旧?”
“天下山川多了去,又不是只有青要之山。”我顶回去。
“妳是因为脾气的关系才被踢下来吗?”他笑了。
老大,你误会到哪去了?真把我当山妖?“我不知道。”我很诚实的说。
但实话总是没人相信的。
7
不管周顾怎么误会我,却在无影无形中,我肩上的担子悄悄的转移,转到他身上去了。说起来,比我厉害多了。到底我凭的是一时意气,经验和对这时代的了解非常浅薄。
而周顾滑溜的像条蛇。不管我的异想天开多么奇怪和犯忌,他总是能够迂回蜿蜒的达到目的。
于是,在我十八岁,正式成为别人眼中的“老姑娘”时,的确我眼前看得到的地方,再也不见愁云惨雾。
但所谓饱暖思淫欲,升米恩斗米仇。即使不求回报,难免还是会有人恩将仇报。
幸好我穿前就有过经验,不然铁定跟古人最爱生的病一样,来个忧愤成疾。
自从我开始接手唯二的庄子时,我就和村子里的老人拟定了一套“家规”。这个时代的司法系统人治的味道很重,非到不得已,没人想见官诉讼。
这时候家族和仕绅的力量就很大了。但没有土地的佃户,和地主的关系有些暧昧,属于半奴半雇佣的关系,反而凌驾于家族和仕绅的力量。所以地主的责任就更重了,可惜很少有地主仔细去正视这个部份。
大明律好大一本,我也背不全,也不可能让所有的部属了解。于是我和故老商量,定了一个简明的家规,大抵上是戒杀戮奸淫窃盗等,轻的跪祠堂或土地庙,重的送官。
但送官是很少的,没伤及人命的,干脆赶出去,只要是我管理的庄子都不收留。
坏就坏在这里。我不知道被赶出村子比去官府挨板子吃牢饭还严重,更招人怨恨。
我十八岁那年,出了一件大事。
一直以为非常纯朴的佃户,居然也有那种无耻的色狼。我才悚然发现,男人只要吃饱了肚子,邪恶的本性就会蔓延出来。
那天周顾去靠近陈州的庄子巡视,不在家里。天才刚亮,庄头就来拍门;,又急又羞又气,听到周顾不在,踌躇了一会儿,转身就走。
我硬把他喊住,问了又问。等他面红耳赤期期艾艾的透露了点口风,我的脸都变色了。
其实是很普通的强奸案。一个男人偷进了弟媳的房间,造成两个女人的上吊,和一个家庭的破碎
我觉得膝盖很软,心底发虚。历史真的会不断重演,不管是二十一世纪还是十五世纪。不过我的大嫂和二嫂没有上吊,她们离婚以后,看了很久的心理医生。
“…人呢?”我抓住门边,省得跌倒出丑,“人还活着吗?”
幸好救得快,两个女人都没死。但这个家就整个完了呢。
这是我第一次打佃户板子,如果可能,我真想干脆叫人打死。一面打我一面在旁边骂,骂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骂他伤害自己的家人,破坏自己的家庭。
若不是那人的老母不断哀求,打完我真的想直接送官算了。
最后我把他赶出庄子,严令不准有庄子收留他。他的老母和老婆跟着他走了,连他的弟弟都休了老婆一起走,那个倒霉的女人剪了头发当尼姑去了。
我生气,非常生气。或许是我错了,佃户就是佃户,是我的员工,不是我的家人。
我不该放入太多情感,为之痛心疾首,更不该觉得羞愧难当,觉得自己没教好。
也许就是我太生气了,所以很蛮横的加了条家规,若再出种事情,整家都赶出去。
好不容易,我把自己的心情整理好,但周顾一回来就说,“薛荔,妳错了。”
我跳起来,想破口大骂却噎着出不了声,只能颤着手指比着他。
“不说妳是女孩儿不该管这种事情,”他拨开我的手,皱紧了眉,“也不该把人赶出去。在妳手底还能捏着,看要怎么处理都好。赶出去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
我还以为我会气到少年中风呢,只觉得眼前不断发黑。终究还是强撑着,摔了帘子进屋生闷气,好几天不跟周顾讲话。
没错,他考虑得很周详。没错,我就是意气用事。但我是女人,倒霉的女人!我会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两世为人我就见过两次同样的破事,怎么可能压得住胸里那口恶气?不是力气太小,我就自己夺了板子打!
我才不管有什么后果!
结果恶果真的逼在眼前,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害怕。
隔没几个月,官府的捕快把我锁进大牢了。罪名是勾结山匪、逼良为娼、私设学院…洋洋洒洒几十条大罪,应该斩立决才对。
出首投告的,正是那个连名字我都记不住的强暴犯。看到捕快时,我冷笑两声,伸手让他们绑了,硬着心肠不去听奶娘哀哭的叫唤。
不知道是周顾打点得好,还是县令另有所求,我没受刑,就是关着。女牢也没那么不堪,就是气味难受些,食物不堪入口。就当作是减肥好了,又不是没饿过。
主要是我非常愤怒,心底腾腾腾的不断发火,连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
不管是十五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都是这样污秽不堪,不值得活。比起牢房的肮脏,我更不能忍受这种黏附在精神上的污秽,巴不得一死洗之。
“…还没气完?”
我猛然转头,一身黑衣的周顾在牢房外看着我。“你怎么来了?”我本以为他被允许来探监,但牢头娘子没陪他进来。
“我偷溜进来的。”他说得云淡风清,端详着我,伤疤嫣红,“看起来没吃什么苦。”
我真的很想骂他。私闯大牢,这条罪够他吃牢饭或流放个几千里。但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哭了。“…周顾,你代我照顾曹管家和奶娘就好,别再来了。”
他不回答我,“恩将仇报之徒,在所多有。”
我气馁了,“我不是气这个。”早八百年就知道了。所以施恩别望报,望报气死人。我是求心安,又不是希望人报答。
“那是气红颜多薄命了。”他无奈的说。
这话更触动我的心肠,我干脆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我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不在乎。但我受不了这种脏,真的完全受不了。更受不了被这种脏人抹黑,这是侮辱我!
他开了牢门进来,泪眼模糊中,只见向来淡定的周顾更无奈,抽了手绢给我,我只管呜咽,没一会儿帕子就半湿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杂七夹八的,我自己都不太懂。但周顾静静的听,一言不发。
等我觉得气出得差不多了,也哭得一点力气也没有。
他这才说,“别怕。妳只是代罪羔羊。有人在试水温呢…王六只是被拿来当枪使。
咱们这个胡涂县令,想借机趁火打劫。”他叹了口气,“这都不算大事…薛荔,妳觉得到县城避难好,还是自家修寨子好?”
我猛然抬头,有点吃不准。“为什么?又没要打仗…”我突然一窒,脸孔的血液褪得干干净净。
这几年关中旱得一塌糊涂。我们这地处南陲的小地方也只听到一点风声而已,但也听说了流民问题严重。流民就易生民变,我对官府又没什么信心。
“关中出事了?”我心头一紧,“那为什么是随州…”
“抢遍地饥荒的的乡里有什么用?”周顾笑了两声,声音冷冷的,“随州这几年还勉强能过,偏远又没官兵驻守…苏杭虽好,却是重镇。我要拉旗据啸,也会选随州。”
这下我明白了。这还真是个精巧的试金石。若是咱们县令是个能吏,那些流窜的匪徒就会改选别地,反正随州大得很。很可惜,这县令只会上穷黄泉下碧落,出了流匪只会抱头鼠窜。
随州就属安乐县最富,不巧大半都是我管理的庄园。
借着这个缘故,他们想看看官府的态度,和我有没有人撑腰…特别有没有官兵撑腰。如果没有的话,就刚好我为鱼肉,他们就正好成为快意的刀俎。
我握紧拳头,心底一阵阵发虚。
“寨子要修,但我们来不及。”我缓慢的说,“所以还是得做些准备,随时准备逃到县城。可能的话,还是跟流匪头子周旋一下。这家伙很缜密厉害,这种人是可以谈的。我猜他是会撑着等招安,说服他别弄到杀鸡取卵,他们应该是作长期地盘据的打算…”
周顾突然按住我的手,“薛荔。”
我茫茫然的抬头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