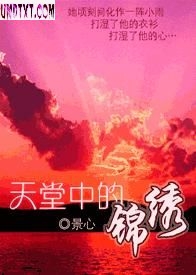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个故事遵循了一个沿用已久的公式,其中包含来自公司等级制度截然不同的两端的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在这一例子中,下层雇员涉世不深,丝毫没有意识到她与之对话的人的地位。叙述的动力源于它创造的关于故事结局的期望:老板将做出何种反应?秘书会受到惩戒、被解雇还是因忠于职守而得到褒奖?无论结局如何,故事都以强有力的方式向听者宣讲,提供有关得体的和不得体的组织实践的强烈意识,故事是重要的和意味深长的,这体现在组织成员把它确定为对典型的组织实践的例示。对于已社会化了的组织成员,它对“事情该怎样办”提供了肯定的答复;对于新成员,它起到了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的作用。
这样的故事是否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其实无关紧要:雷夫森与一个“初出茅庐”的秘书之间的冲突也许会像描述的那样,但即使故事是假的,这对其自身的推论力量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推论力部分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故事能够同时引出重要的主题和问题,尽管他们自身排斥效度测试的做法(Witten,1986)。
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可以说每个推论行动所包含的真理声言并不会在叙述中轻易得到改变。正如斯劳特在上面指出的,故事讲述者和故事本身依靠建立在讲者和听者之间的联系而形成了某种权威和合法性。故事的讲述要求不信任态度的终止;它要求作为听者我们被拉入其中并变得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都投入其中,正如我们看电影或读小说时发生的那样。在这样一个情境中,我们并不把自身远离出去以反映故事的真实性,而是使我们投入到故事的叙述结构和发展中去。我们最有可能对故事作出的评价是关于故事的叙述质量及其内在的连贯性。正如威腾(Witten,1986)所进一步指出的,故事叙述的规则与一般对话规则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存在话轮转换,因此几乎没有机会在声言与反声言之间进行正常的辩论。当有人讲述一个故事时,我们不大可能对某些具体方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即使我们发现这一切是假的。我们赋予故事讲述者作家的地位,这使他们被免除了通常的强调对话真实性的严格要求。用戈夫曼(Goffman,1959)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说讲述者和听者分别从事“防御的”和“保护的”行为。换言之,说者和听者都致力于维护讲述者所设计的自我表达的形式。把一个讲演者的自我表现方式揭露为虚假的(例如,暗示所讲述的故事不真实)就会引起所有参与相互作用者的尴尬。因此,我们假定故事是真实的,不仅因为我们不相信讲故事者会对我们撒谎,而是因为这正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要做的。毕竟,就叙述的性质而言,我们很有可能对其他人讲同样的故事,带有我们个人的色彩,而且我们期望在自己讲述故事时得到他人的保护,就像我们给予他人保护一样。
因此,尝试把组织叙述看做组织实践的反映——作为散布组织信息的方式——这样就过于简化了叙述与组织现实间的关系。组织的故事及其所描述的组织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能用纯粹的表述性术语作出归纳。叙述的作用不在于模仿、映射组织的行为,而在本质上是具转义性质的:
转义是所有现实的话语所极力躲避的阴影。但这一躲避是无用的;因为转义是所有话语构成客体的过程,它假装对客体作的只是现实的描述和客观的分析。……总之,话语是一种典型的中介事业。这样,它既具解释性,又具预先解释性;它既是与解释本身的性质有关的,又是与作为它对自己进行详尽阐述的明显场合的主题是有关的。(White,1978,
2-4页)
因此,组织成员并不直接经历组织现实,而是通过推论实践,尤其是叙述性的话语的表达来作为中介实现的。费希尔(Fisher,1984,1985)甚至提出,叙述不仅仅是话语的一种模式,它甚至提供了一种使传播过程概念化的范例;实际上,人类可以被看做是“叙述人”(homo
narrans)。人们的互相交往主要通过对事件和经历的叙述,无论叙述发生在组织、家庭或同龄小组的环境中。人们共享的意义大部分是通过叙述得以产生和再现的。
至于组织叙述,我主要关注的是对组织中讲述的故事在意识形态上对维护和再现现有统治关系的作用的方式进行审视。上面所引的怀特关于话语“假装只作现实的描述”的说法为把意识形态解释为推论的中介提供了一个起点。组织故事可以在意识形态上通过组织成员和他们对组织的知觉看法之间发挥现实的中介作用,构建一个仅服务于一小部分组织成员的利益的现实。因此,故事通过提出难以质疑的真理声言、并且自称代表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的声言来起作用。
因此,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叙述的解释必须阐明这一特定的推论实践作为一种“遏制策略”所起的作用(Jameson,1981)。即,我们必须考察叙述以一定形式把社会行为者置于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相关的方式。在组织文化中,这类遏制策略包括对规定的和禁止的组织实践的明确表述,及对组织成员的质询以使他们建立起一种“切合”于组织中现行的权力关系的组织意识。这些权力关系通过推论得以再现,因为叙述通过把事件从根本上描绘为道德剧(在这类道德剧中一组特定的价值观被赋予合法性和权威性)来达到封闭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故事体现了他们描绘的政治现实的理想。
在下一节,我将对某一具体的组织故事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的实现作出一个解释。这种分析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是全面彻底的,而是展示应用上述理论模型的一种可能的方法。
◆作为意识形态的组织叙述:一个具体应用的例子
在对一个话语——无论是书面的或口头的,是诗歌或散文——提供解释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可信度。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断定某一特定的解释比其他任何解释更“精确”、“正确”或“恰当”?我不想就此对解释理论做全面论述(那不是这一分析的目的),但是我的确想使自己远离可能对诠释的“客观”或“可证实的”过程进行辩论的观点。正如利科(Ricoeur,1976)等人向我们展示的,解释的过程包含了对话语所体现的“意义的过剩”的认识。没有任何一个解释能够完全包括一个文本可能产生的多重意义。无论是寻求作者意图还是探索文本产生的社会环境都无法给予我们对文本的“终极”意义的深刻洞察。归根结底,解释的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这当中解释者为文本建构并提出一种可能的意义。
从一个文本中有可能构建出的意义的多重性并不意味着解释的过程完全是相对的和主观的。对一个文本的解释并不完全是一种多元化的事业,其中每个解释无论是怎样的具有个性特征或肤浅,都被认为同样值得考虑。这种主张忽视了建立一个细致的、以理论为基础的意义分析的需要。正如我们不能轻易承认一个外行能对其他人的心理状态作出合理判断一样,我们同样应谨防在概念和理论上未具有扎实基础的对文本的分析。
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微妙,因为根据定义,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的表述并不是作为意识形态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就其本质来说,不仅能够通过支配者而且还包括被支配者来使支配的关系得以维护。但是如我们已看到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从不会是完全的。所有群体,无论怎样受压制,都能够以一定程度的推论渗入并继而批判他们所处的支配结构。据此,叙述并不一定仅仅再现它所处的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霍尔(1985,103页)指出,尽管在意识形态之外没有社会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实践,无论是推论或其他实践,都完全受制于它们所处的意识形态的意义结构。话语也许会受到重新解释:它由此而对所处的支配关系进行批判。
因此,对叙述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解释包含了对产生叙述的那些支配关系与叙述所表达的意义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不包括采纳意识形态以外的立场,而是使自身远离意义的结构以便使批判的视角得到采纳。这不意味人们表达了对叙述结构的非意识形态的解读,而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所表达的解释是具有解放的性质的,它允许对那些被受到分析的表义系统所质询的一方进行批评性的自我反思。当然,这样的分析困难重重。汤普森指出:
至于谈到由疏远而获得的客观化,它受到作为疏远关系对立面的归属关系的限制。对意识形态的评论可能是局部的、不连续的和不完全的。它永远不会在我们所属的历史和社会之外的立场上得到实施。在对社会历史遗产的更新和评价这一永无休止的解释过程中,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仅仅是瞬间的过程——尽管是很重要的一瞬间。(1984b,188页)
任何对话语的特许的解读(在作出真理声言这一意义上)都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然而,用话语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来分析话语起到了通过对话语与其帮助维持的统治关系之间的关系的解释而扩展了解释的过程。为服务于意识形态而对话语进行的批判必然牵涉到对统治的批判。
因此,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应采取何种方式呢?汤普森(1984b)指出,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社会分析,其中人们对产生统治形式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考察。这样的分析可以在以下层次上实施:(a)活动,其中对某种具体的相互作用环境进行考察;(b)公共机构,其中对形成和抑制行动的某些可限定的社会结构进行考察(ATT,IBM,等等);及(c)构成公共机构的结构要素;例如,在大多数美国公司中,正是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了具体制度得以维持和再现的环境。第二阶段要求达到推论分析的水平。汤普森(1984b,136页)主张,“表达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必须被视为……显示一个得到表达的结构的语言构成”。据此,对话语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它在表达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汤普森建议,对得到表达的话语的结构可以从叙述、辩论结构和句法结构等层次上进行检验。对意识形态的分析的第三阶段是解释。这一阶段允许“创造性的意义建构”(1984b,137页),并认识到无论分析方法可能是怎样的正规和系统化,最终应由研究者提出“一个总是充满风险和可以引起争论的可能的意义”
(1984b,137页)。人们正是从这一点来探究话语“就事论事”的潜力,把多重意义糅入单个的形象、短语或故事中。正因为话语的具有多重指称对象并将它们糅合到一个复杂的意义网中的能力才使得推论实践在意识形态上起到作用,从而得以维护统治关系。
汤普森建议,上述分析模式不应被看做包含了各不相同的方法论阶段,而是各个阶段应被看做在整体解释过程中不同的分析主题。在本章余下部分,我想对一个具体的组织故事进行考察,研究它在对统治关系的推论再现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在进行分析时,我将要使用吉登斯(1979)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功能理论和汤普森提出的分析阶段的理论。
马丁等(1983,439-440页)记录了一位IBM公司女管理员敢于对董事长小托马斯·沃森表示异议的故事。故事大致如下:
这位管理员是位22岁的新娘,体重90磅,她的丈夫被派驻海外工作,于是,她被给予一份工作,直到他回来为止。这位名叫露西·伯格的年轻妇女的任务是检查人们进入安全区时是否佩戴准确、清晰的身份证明。
和往常一样,沃森在身穿白衬衫的随从们的簇拥下朝她守卫的区域的大门走去,他佩带着允许在工厂其他地方出入的黄色标牌,但未戴允许进入她负责看守的大门的绿色标牌。“我身穿肥大的制服,浑身发抖”,她回忆道,“制服遮了我的颤栗,但却藏不住我发抖的声音。‘对不起,’我对他说。我知道他是谁。‘你不能进去。你的出入未得到许可。’这正是我们应该说的。”
沃森的陪同人员吃了一惊;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曾料到的。有人发出嘘声表示不满,“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沃森扬扬手制止了这声音,这时其中一位随行人员走回去拿来了一个正确的标识。
马丁等解释了这个故事背后所蕴涵的道德意义,他指出,对于组织的高层成员来说,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是“连沃森都要遵守规章,所以你当然应该遵守”,而对下层雇员们来说,故事传达的信息却是“无论谁违反了规章,你都应坚持原则,予以制止”(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