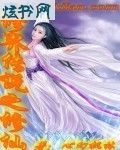曹禺传-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耳上的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女人长得很妖冶”。“一对明亮亮的黑眼睛里蓄满着魅惑和强悍”。“走起路来,顾盼自得,自来一种风流”。说得不好听,也多少有些淫荡。那个白傻子,也是人们平时在舞台上不多见的稀罕人物,还有一个性格怯弱的焦大星,他害怕老婆又畏惧母亲。他们的性格色彩、心理意识都迥然不同于曹禺笔下的其它人物。
他为这些人物所设计的活动环境、舞台气氛也是奇异而诡谲的,甚至说是恐怖而神秘的。暮秋的原野,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空,低沉沉压着大地。狰狞的云,泛着幽暗的赭红色,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堆中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这是象征性的,又是浪漫的奇异色调。大星的家里,也是阴沉可怖的气氛。焦阎王半身像透露着杀气,供奉的三头六臂的神像,也是狰狞可怖。“在这里,恐惧是一条不显形的花蛇,沿着幻想的边缘,蠕进人的血管,僵凝了里面的流质。”而最后一幕,黑林子里,黑幽幽潜伏着原始的残酷和神秘。粼粼的水光,犹如一个惨白女人的脸,突起的土堆,埋葬着白骨。“这里蟠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于是森林里到处蹲伏着恐惧,无数的矮而胖的灌树似乎在草里潜藏着,像多少无头的饿鬼,风来时,滚来滚去,如一堆一堆黑团团的肉球……”这的确是够人惊异而恐怖的了。奇异的人物就在这奇异的环境里活动着。如果按照《雷雨》、《日出》来衡量它,就觉得它不是原来那种写实的路子。
就是这样一些奇异的人物在这样奇异的环境里展开着种种冲突。人物之间纠葛的色彩也是奇异的。仇虎和焦母,一个要报仇,焦阎王死了,偏偏不杀焦母,而杀她的儿子;一个在那里警惕着恶狠狠地追寻扑打。焦母和金子,婆媳间犹如仇家。
仇虎和金子的关系也是奇异的,强烈的爱伴着强烈的恨:花金子立了秋快一个月了,快滚!滚到你那拜把子兄弟找窝去吧,省得冬天来了冻死你这强盗。
仇虎找窝?这儿就是我的窝(盯住花氏)。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窝。
花金子(低声地)我要走了呢?
仇虎(扔下帽子)跟着你走。
花金子(狠狠地)死了呢?
仇虎(抓着花氏的手)陪着你死!
花金子(故意呼痛)哟!(预备甩开手。)
仇虎你怎么啦?
花金子(意在言外)你抓得我好紧哪!
仇虎(手没有放松)你痛么?
花金子(闪出魅惑,低声)痛!
仇虎(微笑)痛?——你看,我更——(用力握住她的手)
花金子(痛得真大叫起来)你干什么,死鬼!
仇虎(从牙缝里迸出)叫你痛,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更重了些)!
花金子(痛得眼泪几乎流出)死鬼,你放开手。仇虎(反而更紧了些,咬着牙,一字一字地)我就这样抓紧了你,你一辈子也跑不了。你魂在哪儿,我也跟你哪儿。
花金子(脸都发了青)你放开我,我要死了,丑八怪。
(仇虎脸上冒着汗珠,苦痛地望着花氏脸上的筋肉痉挛地抽动,他慢慢地放开手。)
在这里,连爱的表现方式都是奇异的。等到仇虎松开手,问金子:“你现在疼我不疼我?”金子一边咬住嘴唇,点点头说,“疼!”一面突然狠狠打了仇虎一记耳光。这是富有诱惑力的。紧接着便是金子逼仇虎捡花的一场戏,她那种一反常态的泼野,就是常五来打门,也非要他捡不可。当仇虎说:“我要不起你”时,她那强烈的爱,就火一样燃烧起来。她一边捶击着仇虎的胸膛,一边骂着:“你不要我?可你为什么不要我?你这丑八怪,活妖精,一条腿,短命的猴崽子,骂不死的强盗。野地里找不出第二个shun鸟,外国鸡……”每一句狠狠的骂,都表现了她那强烈的泼野的爱。这是在一种爱的扭曲的变态心理支配下,演出的一场令人奇异而目眩的戏,你说它真实也罢,不真实也罢,但却抓牢了观众的心灵。作家就是这样波谲云诡地展开他那奇异的想象力,写出一场场奇异变幻的戏。
有人说《原野》在心理描写方面是受了弗洛依德学说的影响,写出了所谓性的本能和欲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能量——性力,说仇虎就有“性力”影响。焦母同焦大星、金子三人的关系,就有着所谓“恋母情结”的因素。但是,曹禺总是否认他受过弗洛依德影响,他说他几乎没有读过弗洛依德的论著。不过,《原野》的确写了人性的东西,自然也包括着性心理在内。在他看来,无论是仇虎、金子,还是焦母、大星的人性,都是一种扭曲变态的人性。特别是仇虎,在复仇之前所经历的精神折磨,以及复仇之后灵魂的痛苦,都深刻地反映出一种强大的统治精神——伦理道德观念、封建迷信观念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精神吞噬的残酷性,仇虎心灵痛苦的悲剧性和真实性被作家天才地揭示出来。他把人物的情绪、心理都戏剧化了。最后一幕,也是最能显示《原野》奇异色彩的一幕。写仇虎杀人之后,所出现的种种幻想,他所安排的黑林子是带有象征性的,同时也是现实的。他突出的是仇虎的恐惧、惊慌、悔恨。“恐怖抓牢他的心灵,他忽而也如他的祖先——那原始的猿人,对夜半的森林震颤着,他的神色显出极端的不安。希望、追忆、恐怖、仇恨连绵不断地袭击他的想象,使他的幻觉突然异乎常态地活动起来。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在序幕中那种狡恶、讥诈的性质逐渐消失,正如花氏在这半夜的折磨里由对仇虎肉体的爱恋而升华为灵性的”。这可以看出是作家构思第三幕的企图,也是他所作出的人物的阐述。为什么作家要采取这样一种写法呢?他在《原野·附记》中是这样说的:写第三幕比较麻烦,其中有两个手法,一个是鼓声,一个是有两景用放枪收尾。我采取了奥尼尔氏在《琼斯皇帝》所用的,原来我不觉得,写完了,读两遍,我忽然发现无意中受了他的影响。这两个手法确实是奥尼尔的。我应该在此地声明,如若用得适当,这是奥尼尔的天才,不是我的创造。至于那些人形,我再三申诉,并不是鬼,为着表明这是仇虎的幻想,我利用了第二个人。花氏在他的身旁。除了她在森林里的恐惧,她是一点也未觉出那些幻想的存在的。①
这里,最早透露了《原野》所受奥尼尔的戏剧,特别是《琼斯皇帝》一剧的影响。不过,他也特别提到他同奥尼尔的不同。的确,《原野》较之《琼斯皇帝》写得更深刻,也富于独创性。他后来对我说:
《原野》也不是模仿奥尼尔的《琼斯皇帝》。那时,我的确没看过奥尼尔的这个剧本。张彭春看了《原野》的演出后,建议说:“奥尼尔的《琼斯皇帝》中的鼓声很有力量,此戏了不起,震动人心。”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加入了鼓声。我看了一些奥尼尔的作品:《悲悼》、《天边外》、《榆树下的欲》、《安娜·克利斯蒂》,还有《毛猿》。奥尼尔前期的剧本戏剧性很强,刻画人物内心非常紧张。刘绍铭说我是偷《琼斯皇帝》的东西,不合事实。《琼斯皇帝》的故事,我是知道的,写一个黑人玩弄手段压迫土著人。此剧在美国上演时,是由黑人来扮演,这个黑人从来没演过戏,但演出效果很好,很逼真。①
曹禺这样的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会承受着传统的以及外来文学的影响。模仿和借鉴的不同,在于能否有所新的创造,借鉴是通向创造的必由之路。当《雷雨》发表之后,有人称他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说他承袭了欧里庇德斯等希腊悲剧的灵魂时,他就说过:“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仿谁。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奴仆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织好了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褪了色(因为到了我的手里)的金丝也还是主人家的。”“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我是追念哪些作品而写下《雷雨》”。②《原野》恐怕也是这样。他看过不少奥尼尔作品,像奥尼尔那种把人与环境的矛盾,渗透在人物性格的自身矛盾,特别是自身心灵矛盾之中的写法;那种通过人物的心灵冲突展现人物的命运的写法,的确是别开生面的。他把人物的心灵、情绪都戏剧化了,从而写出现代人的复杂而深刻的精神矛盾,写出人的内心世界的隐秘。这些,是会对曹禺产生影响的,而这些影响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他融化了奥尼尔的东西,但他更倾心的,还在于写他眼里所看到的中国的现实和人生。他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揭示农民的沉重的精神负担,深刻显现着农民从反抗到觉醒的曲折和复杂的心灵历程。在这样一个特定视角,他对生活的开掘,确有他的独创性和深刻性,单是这一点,就足够了。
《原野》于1937年4月在广州出版的《文丛》第1卷第2期开始连载,至8月第1卷第5期续完。同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准备把它搬上舞台,由应云卫导演。他们请曹禺到上海来,向全体演职员谈了《原野》的创作情况,以及演出中应注意的问题。那时,他就指出,对一个普通的专业剧团来说,演《雷雨》会获得成功,演《日出》会轰动,演《原野》会失败,因为它太难演了。一是因为角色很难物色,几个角色的戏都很重,尤以焦氏最不易,而每个角色的心理上的展开,每人的长处,是很费思索的。二是灯火、布景也都十分繁重。外景多,又需要很快更换,特别是第三幕,连续五个景。他对应云卫导演这出戏,满怀期望。1937年8月7日到14日,《原野》在上海长尔登大戏院举行首次公演,演员阵容相当不错,赵曙、魏鹤龄饰仇虎,范莱、吕复饰焦大星,舒绣文、吴茵饰花金子,王萍、章曼萍饰焦母,钱千里、王为一饰白傻子,黄田、顾而已饰常五。当《原野》公演时,曹禺已不在南京,此刻已是“七七”事变爆发,那时,人们已顾不得对它的评论了。所以说,《原野》未免有些“生不逢时”。在当时也未能引起什么反响,就淹没在抗日热潮之中了。
对《原野》的评论是不多的,但是,只是这些不多的评论,却多否定之词,甚至把它看作是一部失败之作。也可以说,《原野》的厄运是与生俱来的。最早的也是较重要的一篇是李南卓的《评曹禺的〈原野〉》。他认为“作者有一个一贯的优点,就是技巧的卓越。他的人物性格、对话,都同剧情一起一点一点地向前推移,进行,开展,直到它的大团圆”。“但同时也就是因为作者太爱好技巧了,使得他的作品太像一篇戏剧”。同时,他指出:“作者有一个癖好,就是模仿前人的成作。《原野》很明显同奥尼尔的《琼斯皇帝》(TheEmperorJones)非常相像”。他说,如果说奥尼尔和曹禺都受希腊悲剧影响,都有一种“对庄严的氛围的爱好,——不过这一点在《琼斯皇帝》如果成功了,在《原野》却是失败了”。他还指出,仇虎去谋害焦大星一段,是脱胎于莎士比亚的《马克白斯》,仇虎用故事的形式来暗示他同焦大星的关系,是模仿《八大锤》里的《断臂说书》。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而《原野》的人物性格“因为过份分析,完全是理智的活动,以致人物却有点机械,成了表解式的东西,没有活跃的个性”。他说,《原野》的思想也“不大清晰”,“有点杂乱”;既有“虚无主义的倾向”,又有“集团的意识”;“好像是相信命运,又好像是喜欢一种氛围”。总之,他认为这是作者的“一个严重的失败”。①南卓强调了《原野》因模仿而失败是不公允的。《原野》和《琼斯皇帝》不同,不但在主题、题材不同,即使在写法上,他只是借鉴了奥尼尔。曹禺把心理刻画和外部动作结合起来。后来唐埃赋霾茇木缱饕驳昧τ诖车奈难Ш拖非窬┚绾凸诺涫琛L瓢|说:“《原野》用过类似的手法,仇虎凝视阎王照片时,阴沉沉地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仇恨的申诉,焦母摸着本人的轮廓时喃喃念叨着恶毒的诅咒,都是独白,都是直接描写心理活动的自我剖析。”他说,这种以独白抒写思想感情的传统,不仅在古典戏曲里,在古典诗词中也有,如屈原的《离骚》就是一篇伟大的独白。“不过,《原野》借以塑造人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