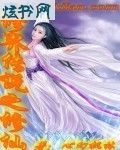曹禺传-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石蕴华是1937年初离开剧校的。有一次,他回到南京,把曹禺、马彦祥和叶子找到一起谈心。石蕴华非常爽快地问曹禺:“家宝,你是不是觉得很痛苦?”这似乎真的触到了他的痛处,他不吭一声,默默地坐在那里不愿回答。曹禺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能用沉默,久久的沉默来对待生活中的挑战,很少把内心的苦痛和辩解倾诉出来,而把它封锁在自己内心的深处。
曹禺在剧校的生活是愉快的。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剧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话剧的爱好者,他们都曾或多或少地参加过演剧活动,是有事业心的。另外,这些学生也是一些有勇气的青年,那时的社会风气把演员看成是“戏子”,把演戏看成是没出息的职业,加之话剧还是个新兴的剧种,职业话剧团很少,毕业后连谋生的出路也没有保证。特别是女同学,不是大胆冲破封建传统的舆论束缚,那是不会报考剧校的。像现在影剧界一些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如凌子风、石联星、项堃、叶子等,都是当时剧校的学员。正因为这些学生热爱新剧,对曹禺来剧校执教抱着深切的期望。曹禺的教学没有使学生失望,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渊博的戏剧知识和绝妙的教学艺术,博得学生的厚爱。
他在事业上是一个从来不敷衍的人,他的热情不但贯注在创作上,同样,也渗透在教学里。他教世界戏剧名著选读,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剧目也经过精心挑选。他从不做抽象的说教,而是采取边朗诵、边表演、边分析的方法,绘声绘色地把同学带入戏剧情境之中,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使剧本上的一句台词、一个停顿,他都能讲出它内在的底蕴。他把渊博的知识、舞台的实践和具体入微的艺术感受融合在一起,这就把学生迷住了。每一堂课,对他们来说都是美不胜收。许多同学回忆说,万老师上课,可谓绝妙,他有学问,会表演,又有创作经验,因此,讲起课来就驾轻就熟,挥洒自如,加上他那口才,所以,每次上课,课堂里都挤得满满的,连外班的学生也来听他的课。他还有一套辅导方法,为了提高学生的欣赏和理解剧本的水平,除重点讲授一些剧目,还组织学生阅读世界名著。他不是一般地布置一下,任其自流,而是按照点名册,具体规定某某读哪本名著,并让每个人都要写出读书报告,或分析主题和人物,或分析戏剧结构和冲突。过一段时间,再根据每个同学的具体情况,更换新的阅读剧目。这样一种指导阅读的方法,使学生获益匪浅,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鉴赏能力。因为他所读中外戏剧名著较多,才能这样指导学生;同时,也因为他具有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才能这样不怕麻烦,因材施教。
他指导学生排戏,更是煞费苦心。对于初学表演的同学来说,并不是任何一个剧本都可以拿来作为排练教材的。为了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他特意把法国剧作家腊比希的二幕剧《迷眼的砂子》翻译出来,并改编为独幕剧供学生排练。他所以挑选这个剧本,是因为他觉得法国19世纪的喜剧家腊比希(EugeneLabiche),同萨都一样,都多少承袭了结构剧的传统。在他看来,由斯克利布所开创的佳构剧,它的舞台和编剧技巧对易卜生这些大师都有影响,对初学编剧和表演的人是会有帮助的。他后来回忆说:“然而,我还是认为有必要认识一下这个腊比希,我才动心把他这个剧本改编成为《镀金》。原剧是两幕,现在是独幕了。我尽量使《镀金》成为当时(1936年)如小仲马说的‘有用的剧本’。因为我认为《镀金》容易有舞台效果,可以使初学表演的人尝尝初次面对观众是什么滋味。在这个戏演出时,舞台效果很好,证明了这个戏可以训练学生有舞台感,但应注意学生片面追求舞台效果。其次,我认为这个戏的演出风格的高低,会因演员的修养水平的高低而大不一样。一个成熟的好演员,可以把它演成有风度、有幽默、有趣味的好戏,决不会轻薄鄙俗。但遇到格调低的演员,完全可能把这个戏降低为‘文明戏’。这个独幕剧很能考验演员与导师的修养水平。”①由此,可看出他的教学是十分用心的;同时,也看出他的戏剧见地。
指导学生排戏,他基本上是运用他的实践经验,也可以说是从张彭春老师那里学来的导演方法。他首先发动学生讨论剧本,从主题、人物到台词,让学生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务求理解透彻。具体排练时,又指导得十分细致。每句台词,为什么这样写,它的含义是什么,该怎么念,又该怎样动作,几乎等于他把每个角色都演一遍。学生们说:“万老师是编剧、导演、演员三位一体的老师。他写的剧本处处体现出他的艺术匠心,写得那么细致,连动作都写出来了。他指导学生排戏,也是这样,独具一格,犹如中国的工笔画。”他的教学和他的日常生活风度迥然不同。他为人比较谨慎,沉默寡言,但又很马虎、不拘小节,不会料理生活。他给学生的印象是很随便的,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但是,在排演场上,却挺叫真,连一个动作都不准错。一旦进入创作领域,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南京的进步戏剧运动正在兴起。1935年初田汉被捕入狱,押在南京,由徐悲鸿、宗白华出面保释。这位响当当的共产党人出狱后,就又为进步的戏剧事业而奔波了。这年11月,由他主持的“中国舞台协会”宣告成立。洪深、马彦祥、张曙、白杨、舒秀文等都来与会,不久便公演了《械斗》和《回春之曲》。曹禺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戏剧界的朋友。中学时代就知道田汉的大名,如今相识了,原来是这样一位充满豪气而爽朗的人物。田汉每次请客,都请曹禺来。马彦祥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他既是一位戏剧理论家,也是位表演家,他刚刚从苏联归来,他是听说苏联举行戏剧节,自费前往观摩的。戴涯也来南京了。曹禺来南京不久,便同马彦祥、戴涯等一起组织起“中国戏剧学会”,他们“为适应新兴演剧艺术职业化的要求”,组织了这个学会,强调通过演剧来研究话剧艺术。他们第一次便筹备了《雷雨》的演出,由曹禺扮演周朴园,马彦祥扮演鲁贵,戴涯扮演周萍,郑挹梅扮演蘩漪,李虹扮演四凤。这是曹禺第一次扮演自己剧本中的角色,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入这次演出之中。当《雷雨》在南京世界大戏院公演时,一下子便打响了,可以说轰动了南京城。特别是剧校的同学看到老师们的示范演出,真使他们大开眼界。马彦祥后来回忆说:我看过不下十几个周朴园,但曹禺演得最好。这可能因为他懂得自己的人物,他是个好演员,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我觉得演周朴园没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①与此同时,他还把米尔恩的《戏》翻译出来,由马彦祥导演,于1936年10月29日起,在南京香铺营中正堂演出三场。11月6日,在镇江大舞台也演出过两场。由他亲自导演的《镀金》,也曾在中正堂演出四场。
来南京只有半年,除了教学,他改编、翻译剧本两部,导演一出戏,还参加演出一出戏,还有那么多的社交活动,可以想见他那种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工作热忱了。
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只有一年的时间,而这一年也可以说是他享受创作的愉悦和欢欣的一年。《雷雨》仍在继续上演,一篇又一篇的评论发表出来,赞美之声淹没了对弱点的批评。继日译本《雷雨》问世,英译本《雷雨》也由姚莘农(姚克)翻译出来,刊登在1936年10月出版的《天下》(英文)月刊上。姚莘农在英译本序言中,称赞曹禺是中国剧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1937年初,美国著名戏剧家、耶鲁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迪安来华考察中国戏剧,他来南京访问田汉、曹禺,由曹禺亲自担任翻译。曹禺把英译本《雷雨》赠给迪安教授,受到迪安的热情赞许。
更值得称道的,是《日出》的发表,它所引起的反响较之《雷雨》更为热烈也更为迅速。这里,不能不提到萧乾,这个独具艺术卓识的文艺编辑,以很大的气魄和无私的精神,在他负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栏内,组织国内著名的作家笔谈《日出》,他选择了最好的时间,正是1937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笔谈文章。
萧乾说:“关于《日出》的讨论,这个剧本问世后,我想通过它把评论搞得‘立体化’一些。我长时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专业书评家来评论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但应不应该也让读者发表一下意见?要不要请文艺界同行来议论它一下?我用三个整版做了一次试验。头两次是‘集体批评’,也即是请文艺界新老作家对它各抒己见,最后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当时除了为加深读者对剧本的理解之外,我还有一个意图,想用这种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謏,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批评。讨论是热烈的,评者与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①参加这次讨论的有:茅盾、叶圣陶、巴金、朱光潜(朱孟实)、沈从文、黎烈文、靳以、李广田、荒煤、李蕤、杨刚以及燕京大学外文系美籍教授谢迪克等。
这些批评既有中肯而热情的赞扬,也有同作者探讨的不同意见。茅盾认为“《日出》所包含的问题,也许不及《雷雨》那么多”,指出它“围绕于一个中心轴——就是金钱的势力”,“是半殖民地金融资本的缩影”。“将这样的社会题材搬上舞台,以我所见,《日出》是第一回”。他“渴望早早排演”。叶圣陶说,《日出》“采集了丰富的材料,出之以严肃的态度,刻意经营地写成文章的。前几年有茅盾的《子夜》,今年有曹禺的《日出》,它们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兴作品,而是一刀一凿都不肯马虎雕刻成功的群像”。他更指出:“它的体裁虽是戏剧,而其实也是诗。”沈从文从中国话剧创作的发展来评《日出》,说:“就全部剧本的组织,与人物各如其份的刻画,尤其是剧本所孕育的观念看来,仍然是今年来一宗伟大的收获。”他还指出:“作者似从《大饭店》电影得到一点启示,尤其是热闹场面的交替,具有大饭店风味。这一点,用在中国话剧上来试验,还可以说是新的。”巴金说:“《雷雨》在《文学季刊》发表后的一年间,似乎没有一个批评家注意过它或为它说过几句话,《雷雨》是靠着它本身的力量把读者和观众征服了的。”但认为《雷雨》“所强调的‘命运的残酷’”是它的缺点,而“这缺陷却由《日出》来弥补了。《日出》不是命运的悲剧,这只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他觉得《日出》的“结局太不悲观,而且在那末尾是明明有一条伸向光明去的路”。“看,这是一个多么雄壮的景象!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结局”。他说,《日出》“是一本杰作,而且我想,它和《阿Q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黎烈文说:
说到《雷雨》,我应当告白,亏了它,我才相信中国确乎有了“近代剧”,可以放在巴黎最漂亮的舞台上演出的“近代剧”。在这以前,我虽然看过两位最优秀的剧作家的剧本的上演,但我总觉得不能和外国看过的戏剧相比,看了一半就想退出。只有《雷雨》确使我衷心叹服,当看到自己身旁的观众,被紧张的剧情感动到流下眼泪或起了啜泣时,我们不相信中国现在有着这样天才的剧作家!能够这样紧紧抓住观众的心的天才的剧作家。他还认为,“把三等妓院搬上舞台,更是颇为大胆的手法。如果不是对于自己的艺术有着绝对信心的人,大概不会这样做的。”美籍教授谢迪克的意见尤为引人注目,他对《日出》的评价很高:
《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惭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李广田“觉得《日出》不及《雷雨》”,在《日出》中没有一个可爱的人物”,他更喜欢《雷雨》,而不喜欢《日出》。荒煤也有这种看法,认为“《日出》是不及《雷雨》的”,“作者给我们只画出了那些罪恶的表面,而没有给我们把那些罪恶的根据找出来——换句话说,那就是作者仅仅突击了一些‘现象’,而他应该突击的却是‘现实’!”还有对第三幕的批评。谢迪克认为《日出》的“主要缺憾是结构的欠统一。第三幕本身是一段极美妙的写实,作者可以不必担心观众会视为浮荡。但这幕仅仅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