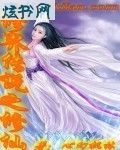曹禺传-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②他的确想学着契诃夫的剧本,以虔诚的拜师心情,做一个契诃夫的学徒。他那样写了,但他觉得失败了,他把这些底稿烧掉了。他心中在想着,这样写也可学得契诃夫的“半分神味”,但观众是否肯看,确是个问题。他觉得中国的观众,“他们要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①这是他多年来在演剧实践中对观众心理、观众的欣赏趣味和习惯,进行观察和体验所得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写剧本,总是想着观众,把观众的需求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没有观众,也就没有戏剧。戏,总是演给人看的。他已经体会到一个剧作家的苦闷和兴味:“写戏的人最感觉苦闷又最容易逗起兴味的,就是一个戏由写作到演出中的各种各样的限制,而最可怕的限制便是普通观众的趣味。怎样一面会真实不歪曲,一面又能叫观众感到愉快,愿意下次再来买票看戏,常是一个从事戏剧的人最头痛的问题。”那时,中国话剧经得起上演的剧本并不多,话剧的观众更是寥寥无几。在他的戏剧创作中首先想到观众的需要和口味,注意培养观众对话剧的爱好,这是他创作成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他要博得观众的欢心,同时却不以低级趣味投合群众,“怎样拥有广大的观众而揭示出来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这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应当说,《雷雨》和《日出》都做到了。在《雷雨》中已经显示着他的诗的兴奋,诗的激情,在《日出》中就有了更深入的发展。他把诗意的发现和现实的揭示有机地熔铸起来。他不仅仅是把那个“漆黑的世界”的图画描绘出来,就他对那个社会的揭露来看,它的污秽、混乱,使人感到那发散着腐尸的恶浊气息的社会,确是一座人间的地狱;但是,《日出》的迷人之处,却在“漆黑的世界”里又透出满天大红的天色;在冷酷中,蕴蓄着温热;在地狱里,有着金子的闪光;在腐尸臭气下,潜藏着牵动人心的诗意力量。《日出》的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血液,融入作家理想的温暖和浪漫的诗情。他曾谈过他写《日出》时的一种美学的愿望: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出来!我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①这是他写作《日出》的一种更真挚更内在的动因和企图。有了这种创作心境,他的笔墨就不同了。诗意的潜流在主题、结构、背景和人物身上流淌着:“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他写了那些“丢弃了太阳的人们”,更写了渴望阳光的人们。虽然,它还不能明确指出太阳是什么,但他的确“写出了希望,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属于太阳的正是那些在夯声中前进着的小工,方达生正是在高亢而洪亮的夯歌声中,迎着太阳走去。这点,当然是激动人心的。
诗意的灵魂,渗透在戏剧结构的血躯之中,处处是充满诗意的对比。激扬着愤慨的深刻揭露和喜剧的嘲讽,同犹如发现新大陆那样对美的心灵的揭示和美的毁灭的悲剧,是那样交织着激荡着。作家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在他的剧里,汇成对旧世界强烈的控诉。听听翠喜的心声吧!
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的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是啊!“都是人”,谁愿意堕入非人的生活境地?在这真实的心灵自白中,是对罪恶社会制度的控诉。对人的价值、人的精神遭到摧残和蹂躏的无比愤慨,使他为恢复人和发现人的价值而进行斗争。他以为,像翠喜这些“可怜的动物”,她们的心灵像金子一样,不能不使人想:究竟是什么毁灭着她们的美。
再听听陈白露的痛苦的答辩吧!
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这是作了交际花的陈白露对他少年时代朋友方达生质问的答辩。这个辩词貌似倔强,又是何等软弱,又包含着多少屈辱和痛苦!在这里深刻地反映着陈白露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也反映着她的精神危机。一个曾经有着美妙青春,漂亮、能干而纯洁的少女,一旦堕入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里,是既不得自已又不能自拔。她明知太阳出来,但又清醒地看到太阳不属于她。她为强大的黑暗势力吞噬了,精神崩溃了,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在《日出》中,既没有色情的露骨描写,更没有投合市民的庸俗心理。他听到过,看到过像艾霞、阮玲玉的悲剧,以及像翠喜那样妓女的悲剧。他不是写陈白露、翠喜堕落的悲剧,而是写她们这样一些纯洁善良的女人是怎样走进悲剧深渊的,他穷追猛打的正是那个社会制度。作家的心像洁白的玉石,他的神圣而崇高的道德感情,使他对自己的人物永远是同情,是悲悯,是怜惜。有人说左拉在《娜娜》中把浪漫幻想和色情描写结合在一起;而曹禺要写的是诗意的真实,翠喜、陈白露都是严峻而残酷的真实的诗。陈白露,是继蘩漪之后,作家贡献给新文学的第二个杰出的典型形象,她是属于曹禺自己画廊中的人物。
最费曹禺思索的是《日出》的结构。他决心舍弃《雷雨》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物上。用他的话说:“我想用片断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如若中间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结构’,那‘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即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谓‘结构的统一’也就藏在这一句话里。《日出》希望献给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们心里的,也应是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因为挑选的题材比较庞大,用几件故事做线索,一两个人物为中心也自然比较烦难。无数的沙砾积成一座山丘,每粒沙都有同等造山的功绩。在《日出》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当的轻重,合起来他们造成了印象的一致。”①这种所谓片断的方法,正是同《日出》的内容相适应的。结构的方法总是对象的适应性的产物,从来没有固定的格式。它的构架特点,即以陈白露的休息厅为活动地点,展开上层腐败混乱的社会相,同以翠喜所在的宝和下处为活动地点,展开下层的地狱般的生活对照起来,交织起来。他的第一、二、四幕,或可能受到根据美籍奥地利作家维姬·巴姆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饭店》的启发。曹禺说,他看过这部电影。《大饭店》写一家豪华饭店,住着来自四方的种种人物,实业家、红舞女、落魄的男爵、职员、速记员等,展开的是这些人物的生活片断。其实,高尔基的《在底层里》也是在一家旅馆里展开场面,没有贯穿的交织的故事情节。但是,曹禺的结构却来自它的艺术独创的构思,即他说的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基本观念”。他加上一个第三幕,即宝和下处的妓女的生活片断,这就加强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力量,加深了对社会人生相的深刻概括。这是曹禺的艺术独创之处。正是在这里,显示着他那富于艺术胆识和打破陈规、超越自我的创新力。他说,他是在“试探一次新路”,这试探,并非只是结构上的,而是探索对现实生活作更深刻更广泛的概括。因之,他把自己的创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也许有人以为他在《日出》前面,安排了老子《道德经》和《圣经》中的语录,便认为他信奉老子哲学,那是不确实的。这是他的苦心。他已经经验了《雷雨》禁演的事实,他不愿一个“无辜”剧本,为一些“无辜”的人们来演而引起一些风波。他知道处处有枭鸟的眼睛窥探着,而《道德经》、《圣经》中的这些语录,便使审查官老爷抓不住把柄。他提醒读者注意那些语录排列的次序,为此,他是煞费苦心的。曹禺曾这样回忆说: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也是很糊涂的,我对老子可以说毫无研究。“损不足以奉有余”大体可概括主题思想,但不能全部概括,因为后面还引了一大堆《圣经》里的话。这些,合在一起可以说代替序的作用。那时我不想写序。那时,有一个想法,对那个社会非起来造反、非把它推倒了才算数,要推倒了重新来过。也不知道怎么来,但是要有人,这批人就是劳动人民,说不清楚是无产阶级。那时,我看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没有读下去。我这个人对理论的东西总感到难懂,看了一些也极不准确。但怎么才叫无产阶级,也不确切知道。劳动者好,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思想是有的。我那一串语录就是要表达那么一些意思。①
他觉得这个意思还没有说清楚,便又补充说:《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天之道具犹张弓欤!高者仰之,下者举之。”这里说的“云之道”,我那时的理解,就是应该有的道理,是应该如此的道理。就好像张弓射物,举得高了就放低些,低了就举高些。“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这就提出个贫富之分,贫富之别了。“人之道则不然”了,那是相反的,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但是,我整个的想法还不在这里,我的想法是要毁掉它,当时不敢说出来写出来,就用了一大串《圣经》的话。开始就是要提醒人们警觉,你看那些人就是那么贪婪恶毒荒淫无耻。然后,就说那天也无光,地是空虚混沌,非要惩罚这个社会不可了。跟着,我说我就是光明,跟着我就能得救。再就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最后,便预示着光明,“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因为那时十分苦闷,可以说苦恼极了,有许多话不敢讲得那么清楚,但有些也是我的确讲不清楚的道理,就采取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了。①如果说,在《雷雨》中,他还对充满斗争的残酷和血腥的现实,有一种困惑,他以为那社会的真实相太大太复杂,“没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实相”,未免带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那么,在《日出》中,他比较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哲学”,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宇宙里的斗争”,而是对人吃人的社会真实相的粗略的概括。他说:“目前的社会固然是黑暗,人心却未必今不若古,堕落到若何田地,症结还归在整个制度的窳败。”他还说,“若果读完了《日出》,有人肯愤然地疑问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还要过这种‘鬼’似的生活呢?难道这世界必须这样维持下去么?甚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这样问两次,那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作者的奢望了”。①这些,大体上代表着曹禺创作《日出》时的思想情状。
曹禺传第十五章 执教剧校
第十五章 执教剧校
1936年1月,《雷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是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曹禺戏剧集》第一种出版的。
1936年2月,《雷雨》日译本,由日本汽笛社出版。日译本出版的经过令曹禺格外感动。他特别感谢秋田雨雀、影山三郎和邢振铎三位的支持和热情。
影山三郎于1981年8月在《悲剧喜剧》(370—373)发表连载文章《〈雷雨〉翻译始末》,回忆《雷雨》日译本产生的过程。《雷雨》在东京演出后,影山三郎在《东大新闻》发表一篇介绍《雷雨》的文章,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传开,这消息由一位推着售货车卖肉食的大婶告诉了影山三郎,由她搭桥结识了邢振铎,两人出于对翻译的共同爱好,决定把《雷雨》翻译成日文。影山三郎回忆说:“秋田雨雀先生从我写的介绍《雷雨》的文章中,得知中国留学生公演新剧的消息,便说‘以后有再演的机会,务必通知我’。这话传到我耳中,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拜访秋田雨雀先生,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