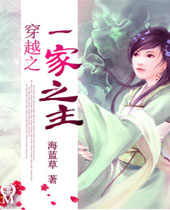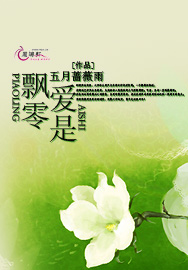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谔逯疲谕砟甑南衷诨叵耄肥翟斐闪四承┎凰忱枪怨缘厣涎В丝际远潦椋恋煤煤玫模残砘嵊胁灰谎那俺贪桑康挥惺迪值氖戮陀貌蛔哦嘞耄痪驮纳亩裕凰慷裁挥泻蠡凇�
不用排队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放学后再也不可以自己逛回去,而要改成排路队。所有的小朋友到大操场集合降旗,然后依每个人的路线排成好几路路队。绝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住在和平东路,长长的队伍随着护导老师带领着,就那么样地一个个进入了巷弄门户,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排路队的时候,回到家的时间一定比较晚,路上可看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常常跟在牛车的后面,一有机会,就偷偷地把自己吊在车后,让牛拖着我们走。孩子们看着拉车的水牛或是黄牛,边走边拉,牛屎好大,一坨怕不有十来斤吧?过年放鞭炮,可以插个大龙炮在牛屎上,用一小截有火头的香,做成定时炸弹,几个顽童赶紧躲到别处偷看,砰然一响,牛屎四射到两旁的墙上门上,小孩子开心得不得了。要是牛屎炸到了路人,听他们一路大骂,我们却最有成就感,偷笑得要命。牛要是撒尿,我们便一直专心地跟着盯着,看看它尿得有多久。牛尿起来很了不得,一路走一路尿,眼看尿痕在地面上弯弯曲曲没完没了,到它老人家终于尿得越来越细终至于滴滴答答最后不见,我们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一路还可以见识得更多,冰店都是当场制冰的,一条好长的轮带就从店里沿着墙一直延伸到门前,马达一转,好大的一格格各式各样的冰就在里面逐渐形成。枝仔冰、雪糕、冰淇淋等等,从他们开始灌汁水到成为冰品,一步步交代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可以用上大半小时,近距离地看着铁匠跟他的徒弟,裸着上身,突出他们烈火也似的筋肉,如何的从一块生铁,你一锤我一锤的,配合得比交响乐还要紧密,在鼓风炉上呼啦呼啦、叮叮咚咚,最后打出一把犁头。
弹棉花的店面就是一张大床,谁家的棉被用旧了,就送去重弹。戴着口罩的师傅背着好长的一把弓,用了许多年,呈现出暗暗的枣红,用一个纺锤似的东西,“”地敲着轻吻着棉胎的弓弦,那床原先已经用得紧紧薄薄灰扑扑的棉胎,就随着那一根弦,渐渐松开,发得比白面馒头还要高,然后他们用一枝比钓竿还要长的细竹棍,“咝咝咝”地把一根根线压上了崭新雪白的棉胎,新棉被就这样变出来啦。是不是这样子一床被子就可以用好几代呢?要是现在流行这样的翻新,就再环保不过了。
还有裱褙铺,师傅调出不同稠度的糨糊,用在不同步骤的纸上。看他们如何地把一张画先反过来,覆盖在那张大大的、光可鉴人的红漆桌上,桌子几乎占了整间店面,看他们再覆上薄薄的一张棉纸,然后温温柔柔地只用那软软的雪白的羊毛刷子,轻轻蘸一点点糨糊,就把这一幅字画给粘稳了,然后眼几乎贴着纸,细细地打出气泡,接着轻轻拈起已黏着在棉纸上的字画,往墙上轻轻两头拇指一压,再刷几刷,这一张字画就等着干了再加轴子了。
我当然还要看看那些画,古今名人作品时时可见,并不非常稀罕,现在的裱画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日后对于传统字画兴趣有增无减,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做榻榻米的总是蹲着干活儿,一把宽宽切刀,在厚厚的稻草上只一下子,稻草便齐齐的露出切口,空气里立刻弥漫着草香。师傅手心上绑了个用了许多年的小圆垫子,一把长针吃他一顶,直直穿过草垫,一针一针绕啊绕紧啊紧的,一张榻榻米就出来了。师大旁边的一家榻榻米店老板,工作之余爱喝上两杯,三两个徒弟跟老友们围着桌子吃吃喝喝,他一人就是要把凳子搬上桌,君临天下地喝。
还有卖歌本的,骑楼下一张大白布上堆得满满的歌本,那个男人拉着胡琴,跟他搭档的年轻女人就一首首地歌唱着,大白布上堆积着歌本,旁边围着许多人,捡起一本翻啊翻的,跟着轻轻地和声。
要是口袋里有个三毛五毛,就可以让一只绿色小鸟儿从笼子里跳出来,为我啄一枝签,打开来就可以见凶吉。小鸟重回笼中,主人不忘赏它一粒米。
吹糖人的、捏面人的、做画糖的、当场烧热了红糖汁滚糖串的、在骑楼下租小人书的、补破碗破盘的、现在还见得着的烤红薯的、家家都可以拿碗米来让他们做爆米花的,还有抓到了野兔、穿山甲、野猴等等,就拴在脚跟前等买主的……有了这样的世界,至少有的小孩子就不想再进入校园了,而大部分的小孩子回家太迟,更属理所当然。
只是,在开始排路队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参观或是参与这些形形色色的享受了。想来这么多路边的小手艺人,因为再也没有许多高矮胖瘦的小孩子围着傻看,一定大失光彩。
另类成长
渐渐长大,活动的范围也渐渐扩张。水源地是台北人饮水之源,净水厂就在“国防医学院”过去不过两三百公尺的水边,从乌来奔流而下的山泉,会合到碧潭,然后流入新店溪,河水平缓清澈,河边遍布鹅卵石,白花花直到见不着的远处天际。岸上有几处提供竹编躺椅的人家,供应一点简单的零食,买一小包红泥花生,书包也有地方寄存了,躺个半日,闲望白云苍狗,肚子饿了,书包里还有便当,冷了也好吃,吃饱了就逛到台大傅园。那个年头傅园外墙一大排店铺遮挡,十分清幽,在大理石亭子里,陪着傅校长睡个午觉,醒来读读从租书店里租来卧龙生写的《惊鸿一剑震江湖》,神驰幻境,逍遥自在,想想同学们还在教室里和差、鸡兔、大小、公约、公倍地算来算去,觉得人生之于我还是蛮好的。
还可以上六张犁的坟山,路很好走,茅草长得比人还要高,可以扑到巴掌大的绿色大蝗虫,还有亮如黑瓷的夏蝉。有一种蜥蜴,长长的尾巴,背上一条美极了的发得出光的宝蓝,从头到尾。它们静如雕塑、动如闪电,一恍神就在眼前消失。读古书写到村落里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便会联想到从六张犁山上下望的景致,但在今天已是热闹的吴兴街了。
一方方墓碑,新旧杂陈,虽然上面的字数不多,也能读出时代与情感。许多还有白瓷照片,无名有名,一律平等,却都耐玩味。记得见到了白崇禧将军的墓,覆盖在小亭之下,墓碑高大,上面是于右任写的寸草,记下这位民国以来最出色的将军生平,字字写得神完气足,便是在一个初中学生眼中,也十分了得,刚刚见过有的人在拓碑,很想依样拓下。但是多年后再去寻访,却找不着了。
动物园也是个去处,逃学如果有伴,善莫大焉。天地间不是只有我一人忍受不了学校,初中同班一位德姓蒙古子弟,此时此地的体制,锁不住他那该在草原上奔驰飞扬的骨血,我们常常彼此激励,更加逃学。曾经在无人防范的时候,溜到老虎笼后面,把正在休息不想理会我们的老虎惹得发怒,它从铁笼里伸出虎爪,抓碎了我的童军领巾,那方领巾是我非常得意的收藏,保存了好久。
我们爱去碧潭,为了省钱,常搭霸王车,就是在今天的汀州路上,当年是从新店通万华的运煤小火车。木制的直角坐椅,烧煤块喷着白气的火车头,呼呼哧哧地带着没几个人的车厢,直奔新店碧潭。小船三五元便可以租大半天,一人一船,或相撞或并行,或兀自寻幽。碧水数丈回光熠熠,潭面清寂如幻,扁舟一叶任西东,船桨划过,水声清澈如铃。我爱把船轻轻划进刻有“和美”两个大字的石缝,躺下身来静听一波波水打石壁,石壁上波影层层,是船是人是水都在水光里飘动,“春水船如天上过”,我仿佛身悬天际。天地间只有我一人,真想永远不回家,永远不去学校。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下了课,就曾经跟着另一班的同学杨敦和去对面的天主教圣家堂玩,那时的圣家堂只是竹篱瓦舍,外带一个小小的院子。杨敦和带着我去见一位魏神父,他是外国人,那时我们见到白人一律称外国人。魏神父总要我们背要理问答,我背不了,只得去玩。院子里有现成的高跷足球,玩得很开心。这是跟圣家堂结缘之始,后来他们搬到新生南路,我还是常常去,很喜欢圣家堂里彩色玻璃的长窗,窗外阳光射入,映照着雪白的圣母圣子,我点了圣水,一人独自坐在木椅上,诚心地希望得救,但背不出要理问答,至今也没有成为教友。圣家堂有座小小的图书馆,许多印刷精美的画册,本本都翻过。圣经故事也大多是从画册上先读了的。长大之后,失去了初恋的情人,痛不欲生,只得去找了已经年老了的魏神父,他颠颠倒倒地说了一些话,无非多读经而已,我从此便再也不求神助了。但姑妈等等许多堂客后来信了天主教,却大多是透过我这个人的缘分,陆续到天主堂去听经领洗的。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植物园是个好去处。时间有的是,走走就到了,读建中的时候更方便。一弯小运河,水面上有大王莲,听说莲叶上可以载得起一个小孩。边上有间欧式小屋,鱼鳞似斜斜的屋顶,门前一片草坪,躺在那样的草地上,比家里的床可惬意多了。放亮了眼睛,立刻就会发现树上有许多松鼠,到了秋天的时候,只只都圆圆肥肥,拖着一蓬尾巴,在树枝树叶间飞蹿如烟。园里大池荷叶亭亭,间杂着粉红的荷花、翠绿的莲蓬,一股风仿佛有意地忽地里在荷池间任情窜游,蓦然间荷池里枝枝片片朵朵个个此起彼落地活了起来。无处不在的参天巨树遮蔽了烈日,玻璃房里有许多奇花异卉,琳琅夺目,以致中年以后,我还一度想要改行去钻研自然科学,却因无从拿到入学许可而作罢。
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去抢图书馆的座位,却不去借书读,而是要占位子温习学校教科书里的功课?这种习惯,在我读书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后来发展到有人经营读书园,唤作K书中心,不必供应什么书,只要有座位便可,人人K他们自己的教科书,想着早点有个出头天。我从来没有在图书馆里读过教科书,大家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我却躲在新公园希腊式建筑或是植物园的中式图书馆里,读借来的书,除了胡适《留学日记》,另外如司汤达尔的《红与黑》、杰克伦敦的《海狼跟白牙》、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等书,篇幅都不算小,却都是在空空旷旷的图书馆里读完的。偶尔也在图书馆做一点学校的作业,大多都是为了补交,再不交就麻烦了。图书馆其实也是个发呆的好地方,常常在那两三处呆坐一下午,不会有冷气,天然的凉风习习而来,令人昏昏欲睡,睡与不睡间的那样的午后,此生似乎再也没有遇见过。要是问我天堂何在?我会说,就在人间,只看是如何的一副心肠。
第八章 异样人间
引子
圣家堂,我的童年与少年最熟悉的地方,不去学校,又无处可去,就去教堂。至今依然是个处处都很漂亮的地方。
八○年代,在纽约读研究所时,时间跟金钱都有限,却把一部日本电影看了又看,至少有五遍。这部电影居然以黑白摄制,是导演小栗康平的处女作,其实他一生也没有导过几部片子。这部片子的片名是《泥河》,描述一个穷苦小男孩童年的故事,他交了一两个小朋友,也有三四个大朋友,看来平平淡淡,却非常感人。那样神秘的友情,成为小男孩深藏一生的至宝。回台湾之后,我又去找来了录影带,再看了许多遍。
许多情节都忘不了,尤其是其中一位欧巴桑跟小男孩的妈妈说的一段话:
“小孩子会自己长大的。”
她比着节节高的手势说:
“他们咚咚咚地就长大了,整个世界都在帮他们长大,孩子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
这位欧巴桑讲话时鼓着腮帮子,正正经经却蛮滑稽的。
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我是受到了天地人群有意无意间的帮助长大的。我也有过一些永远忘不了的长辈跟朋友,无论来往的状况如何。他们彼此不见得相识,学养、年龄、职业背景,更是天差地别,然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回回几临绝境,总得到帮助,暗里明里,知或不知,让我重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些人当然是好人,然而人间的好人绝对不仅只有他们,个人的因缘有限,却由此而让我相信,人生真很值得走上一遭,再苦再痛再穷再无奈再冤再倒楣,信念依然未改。绝望?没有的事。
人生有限,便是满心的感激,也只能挑选几个写写。
1981年赴美留学,晓清带着两个孩子,姐姐也带着两个女儿,在我就读的所在地纽约会合,同游世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