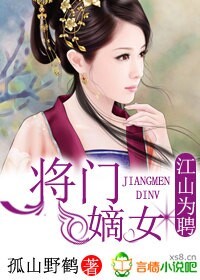江山不夜-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赶上了吗?”
“没有。”他淡淡道,“还是晚了一步,车刚到宫门,就听见里面已是哭声震天。”
江选侍固然是个好人,偏偏毫无根基势力。先帝病危时,她已预见到将来徐太后决计不会善待她。冒险接杨楝面圣,大约是想孤注一掷,弄出先帝临终传位皇孙这一结果。可惜人算终不如天算。
看见她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正在暗中瞪着自己,他叹了一声,没有说出先帝驾崩之后,江选侍被太后杖死的结局。
她的手从被底伸了过来,小心握住了他的手指,像是想要安慰他。过了一会儿,又听她问:“殿下的母亲呢?”
“母亲的棺椁一直停在朝天宫后面,没有下葬,因为……墓志一直拟不好。”他轻声道,“将来若有机会,我一定要将她同父亲合葬了。”
“墓志拟不好?”
太子妃的父亲崔树正以谋逆之罪而遭满门抄斩,才是墓志铭无法拟定的原因,也是太子妃被迫出宫修行乃至抑郁而终的原因。总有一天,他要将这个冤案翻过来。
既没有等到他的回答,琴太微心知不便再问,任他将自己揽到怀中彼此偎依一回,又说了几句闲话,各自安寝。
琴太微心事如灼,自是无法入梦,数着夜空里远远的钟声,连翻身都不敢翻一下。她记得杨楝易失眠,睡觉绝不能被人打扰,但见他背对自己一动不动,不知是否已入睡,暗夜中看去形廓有如画中一段小山。
朦胧中忽听见四声更鼓响,她立刻摸下了床。杨楝亦揉着眼睛醒来,默默地由她服侍着洗脸穿衣。
收拾停当,提灯出门,此时夜色深浓,新月早已沉落,唯见一天碎散星子。山中寒气侵肌,露重苔滑,她拽着他的袖子穿过层层廊道,不知走了多远,终于来到一处灯火通明的大殿,钟鼓木鱼,香烟缭绕,僧侣们通夜诵祷不绝,此时声音有些疲弱虚渺。明灯下一具大木如樯,正是熙宁大长公主的棺椁。
僧众们见徵王带着一名内侍过来,亦不甚在意,只道他是过来巡视的。杨楝上了一支香便踱到一旁,琴太微旋即跟上,对着棺椁认认真真磕了三个头,忽听见杨楝道:“我去后面看看,你在这里守一会儿,别乱走。”
她原指望他陪陪自己,却见他一侧身从后门出去了。她呆立了一会儿,见火盆在侧,又取了一挂纸钱,边扯边烧,忍着哭声暗暗抹泪。这番举止落在旁人眼中,自是极为怪异,便有人上前劝道:“小公公如此厚意,不知……”
她手中一震,整挂纸钱落入火盆中,骤然腾起三尺赤焰。灵堂乍然明亮,隔着猎猎的星火尘烟相看那人,一时如入阿鼻地狱。
穿过光明殿东边的一处院落,杨楝寻到一间禅房,径自推门进去,房中空空如也。正在踌躇间,忽听见背后有人轻声一笑,回头一看,轻袍缓带的郑半山立在门口含笑望着他,白发有如夜半飞霜,身后一个小内侍还提着一桶新鲜泉水。
“这永宁寺有何玄妙好处,”郑半山道,“竟值得殿下秉烛夜游?”
杨楝摇头道:“郑先生别取笑我了。先生的玄妙我尚且百思不得其解,哪有心情夜游?”
自中秋节以来,杨楝每每使人与郑半山暗通款曲,想要探知那个扮演《洛水悲》的戏班背后有什么机关,郑半山那边却是含糊其词。连冯觉非也只是说,郑公公使他找几个稳妥戏子进宫唱戏,他便叫和秀姿寻了一个相熟的戏班,内中情由一概不知,如今戏班子被一股脑儿拘住了,连他也懊恼得紧。
“殿下不都猜出来了吗?何须再来求证。”郑半山笑道。他催着小内侍煮茶待客,一边快速察看周围情形,旋即掩上房门。
杨楝道:“写那出《洛水悲》的汪道昆,他有一个同宗兄弟汪太雷,是福王的授业师父之一。戏班子的人在东厂招供了,说演洛神的那个戏子上台之前,有一个宫人曾跑到后台去看她,想来那把假扇子是被那内官换下的——现已指认出那宫人在太后名下,一向与贤妃交好。至于福王念出的那两句应景诗,是他的伴读暗中教给他的,连同之前应诏诗,也是伴读代笔。这个伴读内官名叫何足道,内书堂出来的人。我猜,先生您大概也认得他。”
郑半山微微颔首,算是默认了,却道:“司礼监问出的这些结果,可是周公公告诉殿下的?”
杨楝不置可否,道:“汪道昆其实是凑巧吧?伴读的小内官是早就安排下的。只是连太后身边的宫人亦能买通,倒真令我意外。郑先生布得好局,环环相扣,每一条罪证都指向福王,只是……皇上凭一时激愤或者会处置福王,稍一冷静下来,他还会相信吗?”
“纵然他只信到五分,也要当十分来信。”郑半山道,“贤妃母子讨好徐氏,皇上一向就不满。何况他一心想立三皇子为储,却因福王这个庶长子横在前面。如今送上门来的机会,他岂能放过?”
“然则他们毕竟是亲父子……”杨楝道,“而且,太后必定是不信的。”
郑半山不可觉察地笑了笑,道:“殿下不必担心。再说,皇上自会和太后去较力。”
杨楝想了想,道:“贤妃为了求娶徐三小姐,曾设计谋害过我……只是于我也算正中下怀。我原想着让杨檀娶了徐三小姐,再远远地离京,也就是了。”
“福王一旦与徐氏结盟,便还有翻盘的余地。徐氏手里捏着这个庶长子,底气也就更加充足。”郑半山不以为然道,“殿下支使冯觉非他们掀起朝议,在立储一事上大搅浑水,是为的什么?难道只是想让福王暂时离京就了事?”
杨楝笑着摇头。
“臣没有提前知会殿下,还请殿下恕罪。”郑半山道,“只是这桩事情殿下宜置身事外。目下看来还好,皇上教殿下出来办理大长公主丧事,便是对您还算放心。”
“这个我明白。”杨楝笑道,又客气了一句,“却是让先生费心了。”
“原是臣分内之事。”郑半山闭了一会儿眼睛,忽道:“别的倒也罢了,只是何足道这孩子从小就稳妥内秀,甚是可惜。”
“何足道。”杨楝笑道,“既然早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学名,此时就不用再说可惜了……”
“说的也是。”郑半山道,“这回替太后出来送灵,遇见从前带过的另一个孩子跑出来给臣磕头。这也是个聪明有肝胆的,年初为一桩小事将他贬到皇陵。臣看他熬了大半年,性情收敛许多,大有长进了,便有心再带他回来。臣想将他送给殿下,若他将来能为殿下助力一二,就算没有白费臣一番栽培了。”
杨楝不觉一讶,竟本能地想要推辞。郑半山击掌两下,小内侍立刻端着新煮的清茶进来,叩首问安、倒茶捧巾,举止如行云流水。杨楝尝了尝茶水,连声称赞,又见那小内侍眉目恭顺,便问其姓名。小内侍答曰:“姓徐行七。”
郑半山意味深长地笑道:“他从前伺候过琴小姐,颇为勤谨。”
那小内侍眼神极快,已跪在地上谢恩了,又恳请他赐个学名下来。
“就叫徐未迟。”他勉强道,“有错则改不为迟。”
听见这句话,郑半山不觉联想往事,望向杨楝的目光中闪过一线淡如晨雾的哀凉。
回到光明殿上,琴太微竟不知去向,棺木前空无一人,火盆余烟冉冉不绝。杨楝大惊,忙问左右,守灵僧人指向殿外。他追出去看,只见她站在殿外古碑下张望,晨风鼓起贴里的衣摆,飘飘如白蝶。此时天色将明,殿前香烟如雾,隔着烟气似可见一个披麻戴孝的人影穿过柏林,匆匆出了院门。
“那是谁?”
“晓霜。”她被他吓了一跳,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人背影纤细袅娜,看来是女子。然而他心中的狐疑却并没有一丝减轻。她愁眉不展,目光闪烁,似乎颇为后悔刚才说了那个名字。
“晓霜是谁?”他淡然问道。
她心中一沉,只得道:“从前服侍我的丫鬟。”
他没有再问下去,扣住她的手腕,穿廊过院一径拖回了自己房中。
这日早上还有最后一番祭仪。时辰已是不早,程宁捧着祭服急得团团转,见他二人回来,忙请杨楝换装,又催琴娘子赶快为殿下梳髻加冠。
杨楝见她仍是拙手拙脚的,皱眉道:“你不会梳头吧?”
琴太微道:“会的呀。”
他顿时黑了脸。
琴太微心中一惊,忙道:“从前躲在皇史宬,我都作内官装束,那时就学会了梳男子发髻——你瞧我今日给自己梳得如何?”
他瞥了一眼,见她头顶单髻额束网巾,果然十分整齐。“还不错,”他淡然道,“那便为我梳上吧。”
她握住乌黑光亮的长发,用角梳轻轻一绺一绺梳通了,一股脑儿拢在头顶挽成一只单髻,用头须绑好,罩上网巾,又从程宁手中捧过燕弁冠为他戴正,插上长簪,两绺朱缨仔细缕在胸前打上一个结子。燕弁冠上的五色玉珠泛着清润宝光,衬得他面如冰雪,只是眼下一抹淡淡青痕,似乎是没睡好。
“还成吗?”她小心问道。
他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祭仪结束于日出之前。除谢家人留在永宁寺继续守灵,其余人等皆随着徵王离开天寿山回城去。
折腾了一天一夜,众人皆感疲惫,只顾催着人马匆匆赶路,也不讲究仪仗了。杨楝坐在车中一言不发,皱着眉头将这两日的诸般事务一一回想起来,检点有无错漏。忽见琴太微抱臂缩在车角,两只眼睛圆溜溜地瞪着自己,他顿时想起早上的官司来。想必她也备了一套说辞专等着自己问话,一时间他倒不知如何下手了。
“那个丫鬟,”他忽然道,“我想讨她过来服侍你,故着人跟谢家问了一下,可惜她已做了谢翰林的小星,来不及了。”
早间那片刻工夫,她已看出晓霜开过了脸梳上了头,只是未敢往深处猜测,更没来得及问个端底。听杨楝这般夹枪带棒地说出,心中顿似踩了一空,险些在他面前露出怨色来。
“多谢殿下费心。”她强作淡然道,“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没想到最后竟成了一样的人。”
杨楝大怒,冷笑道:“既是一样的人,我拿你去和谢翰林换她,你意下如何?你能重回谢家定然心满意足,我这里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
她愤然道:“你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竟说出这种话!”
他亦有些后悔自己言语孟浪,嘴上却仍然道:“圣贤书是给你表哥这种人读了换乌纱帽的,我读它作甚?”
此言令她讶然无语,半晌才回过神来,缓缓道:“不过是偶遇故人,便遭殿下如此疑忌。长此以往,我亦不知该如何自处。或打或杀或贬黜,请殿下及时明断。”
敢如此说话,不过是仗着自己下不了狠手——他一时恨得想捏碎她的手腕,偏生“断”不出一个字来,只觉得不管说什么难受的都是自己。
可她也不是不害怕的,见他久久沉吟,索性壮着胆子主动说了一句:“晓霜只是问问我在宫中过得可好。”
“那你如何说?”他索然道。
“自然是照实说。”
“照实说?说我打你?”
琴太微又是一怔,不觉切齿道:“我岂有颜面说这个,自然是说殿下宅心仁厚,因此一向待我极好。”
他断然道:“我哪是什么宅心仁厚……”
忽又收了声,他顿觉自己失言了。她亦悟了过来,心中骤然一软。他的眼中似有微微一点火光在闪动,看得她竟不知再接哪一句话才好。
“我知道,”她含糊其词道,“不过是看在我爹爹的面子上……”
他忽然叫停车牵坐骑来,旋即翻上马背,远远地跑开了。
望着他绝尘而去,她怔了半天,忽想起他既然着人问过晓霜的来历,那么晨间殿上发生的事情又怎可能瞒过他?那么多人看见了。她又羞又急,到底还是惹他生气了。
晨间她隔火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晓霜,而是谢迁。他隔着火光看清她是谁,苍白的脸孔上立刻浮出了熟悉的温柔笑容。
他小声和她说话,声音低沉而急切,说他猜想她也许会跟着徵王出来送葬,所以一直守在祖母的灵前,果然等到了她,他们已有许久没见面。
可她像是被火烫了一下,哑然不能言语,最后竟连连退步径直逃出了灵堂,险些被门槛绊倒。
晓霜是随后追上来的,这一晚大约是晓霜一直伴着他守灵。他亦体谅她不敢面见外男,遂叫晓霜过来问她安好,问她有没有什么话要转告家里,有没有未尽之事需要他帮忙操办。晓霜与她分别逾年,激动得词不成句,连声说小姐长高了更好看了。可她心中万鼓齐敲,一个字也没听入耳中,只想着杨楝看见了怎么办,寥寥数语便催着晓霜赶快离去,到头来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她一遍又一遍地回味晨间那一幕,因为过于慌乱,她连谢迁的脸都没看清,只能靠模糊的印象一点点缀补,如捕风捉影不可捉摸。早知杨楝终归会计较,倒不如当时奓着胆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