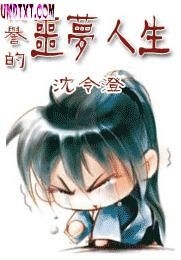十一种孤独-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译/ 陈新宇
文/ '美' 理查德·耶茨
理查德·耶茨(Richards Yates ;19261992)是“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伟大作家”,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对美国当代作家如安德鲁·杜伯斯(Andre Dubus)、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等产生过深刻影响,有“作家中的作家”之称。
他的处女作《革命之路》(1961)与《第22条军规》、《爱看电影的人》一同获得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随后他陆续发表的作品有《扰乱和平》(1975)、《复活节游行》(1976)、《好学校》(1978)、《年轻的心在哭泣》(1984)、《春寒料峭的港口》(1986)等。
《十一种孤独》以冷峻的笔触描绘了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纽约人的生活,写的是人的脆弱、对生活无可奈何地忍受。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该书里十一种孤独的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生活不太如意的人:曼哈顿办公楼里被炒的白领、有着不朽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屡屡遭挫、一心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即将结婚十分迷茫的男女、古怪的老教师、新转学的小学生,肺结核病人、老病号的妻子、爵士钢琴手、郁郁不得志的军官、退役军人。
以下四篇小说译自2002年Picador出版的《理查德·耶茨短篇小说集》(The Collection Stories of Richard Yates)
建筑工人
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专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把他叫做“克拉格”,但也可以保证他不幸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感性的人,但我们要跟他长期相处,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雇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从事撰稿工作。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好差事,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好像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注:一种帽顶相当低并有纵长折痕且侧面帽沿可卷起或不卷起的软毡帽。)(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多少知道诚实地谴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在我紧张时无数次神经兮兮地捏拢、整理它的形状,整来整去;其实帽子根本没有破)。我喜欢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感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日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得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浪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问题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
“今天,国内公司债券异常高涨,交易略显活跃……”这就是我每天为合众国际社电报写的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嘎吱嘎吱,卡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讨论棒球;我则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谢天谢地,总算到下班时间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妻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上一间大大的,有三个窗的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注:Left Bank,法语 Rivedroite。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构成的,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在琼洗碗时,房间里是一片令人尊敬、甚至是虔诚的静谧。这是我在角落那三折屏风后的休息时间,那里摆了张桌子、上面放着学生台灯,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性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根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注:这三篇小说都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小说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总是、总归还是很糟糕的东西。
许多个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风后发呆——读纸板火柴里印的每一个字,又或者,读《星期六文学评论》封底的广告——这年秋天,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无意中读到下面几行:
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丰富想象力。
伯纳德·西维尔。
——下面还有电话号码,看上去是布朗克斯(注:Bronx,纽约五大区之一,纽约市最北端的黑人区。)的区号。
那天晚上,我从屏风后走出来,琼从洗碗池边转过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摊开的杂志上。我不想用我和琼之间简单、诙谐的海明威式的对话来骚扰你们。我也会跳过我与伯纳德·西维尔之间礼貌的而无实质内容的电话交谈。我要跳过几天到后来的某个晚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最终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吗?”他问道。“你叫什么?鲍勃?好的,鲍勃,我是伯尼(注:伯纳德的昵称。)。进来吧,随便点。”
我觉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在此仔细描述。他大约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比我矮得多,也壮实得多,穿着件看上去挺贵的灰蓝色运动衫,下摆没有塞到裤子里去。他的头大我一半,稀疏的黑发齐刷刷地梳到后脑勺上,好像他刚刚站着仰面洗了个淋浴;他的脸是我见过最坦率最自信的脸。
公寓整洁、宽敞,奶白色调,整个地面全铺着地毯,到处是拱门。在靠近衣柜附近的狭窄壁龛处(“脱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挂在这个钩子上,我们就安顿好了;好。”),我看见一堆相框,全是一战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墙上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只有几只精美的铁制灯架,还有几面镜子。走进房间,你不会再去注意有没有相片,因为你所有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唯一的一件令人惊异的家具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它——壁橱?——不管它叫什么,它似乎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有些地方齐胸高,有些地方又只到腰部,至少用了三种不同深浅的褐色装饰面板。有个地方用来放电视机,有一部分是无线电留声机;有个地方薄薄的,做得像个架子,放着盆栽或小雕像;有个地方全是镀铬把手和花里胡哨的滑动板,像个酒吧。
“喝姜汁汽水吗?”他问。“我妻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给你倒杯姜汁汽水。”
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试他的写作应聘者时,他妻子一定经常出去看电影;我后来倒是见过她,以后会说到的。不管怎样,那第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俩,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着姜汁汽水,谈的可完全是正事。
“首先,”他说,“告诉我,鲍勃。你知道《载客中》(注:My Flag Is Down,纽约出租车司机James V Maresca的日记。)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说的是什么,他已从壁橱的某个凹陷处抽出这本书,递过来——这是本纸面本的书,你可在药房(注:照药方配药,出售药品和其它杂货的商店,实际是一种杂货店。)这种地方买到,是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回忆录。接着他开始跟我说这本书的内容,而我则看着这本书,点着头,只希望自己没离开过家。
伯纳德·西维尔也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干这行已经二十二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大,最近两三年,他开始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这小说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我想你看看这个,”他说。这次,壁橱里生出了一个干净的小盒子,三寸宽五寸长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诉我里面记录了几百条不同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他向我保证,至少每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真的。我能想象真正优秀的捉刀人会如何对待这样丰富的素材吗?或者说我能想象这样的作家将能从杂志销量、作品版税和随之而来的电影版权中赚取多么丰厚的回报吗?
“嗯,我不知道,西维尔先生。这事我得考虑考虑。我想我得先读读这本书,再看看有什么——”
“不,等等。你抢在我前面了,鲍勃。首先,我并没有要你读那本书,因为你从中学不到什么。那人写的全是黑帮、女人、性、酒这类东西。我完全不同。”我坐在那里,大口喝着姜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实只希望他快点讲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离开。伯尼·西维尔是个热情的人,他跟我说;他是个普通、平凡的家伙,有颗博爱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观;我明白他的意思吗?
我有个小花招,可以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很容易;你只要做到:双眼直盯着说话者的嘴巴,观察他说话的节奏,嘴唇、舌头无穷变幻的形状,你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正要这样做时,他又说道:
“别误会我,鲍勃。我还从没要哪个作家为我写过一个字而不付钱的。你为我写作,你会得到你应得的报酬。当然,这场游戏目前这个阶段,还不会有大笔的钱,但你还是会得到报酬。够公平吧?来,我给你再添满。”
这是他的建议:他从这些卡片里给我思路;我把它变成伯尼·西维尔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长度大概一两千字,他保证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欢我写的东西,将会给我更多东西写——如果我能应付得过来,就一周一篇——除了每篇故事付的钱之外,当然,这些故事还会带来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获得相当大比例的分成。他神秘兮兮地看着我,提到他推广这些短篇小说的计划,虽然他极力暗示《读者文摘》可能对此感兴趣,但他还是坦白承认目前还没有与哪家出版商联系过最终将这些短篇小说汇集成书的事宜,但他说他可以向我提几个名字,保管我听后眼珠子都会掉出来。比如说,我有没有听说过曼尼·威德曼?
“哦,也许,”他说,大笑起来,“也许说威德·曼莱你会更知道些。”这是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兰开斯特这样出名。威德·曼莱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区的小学同学。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到现在关系一直还很密切,有件事也让他们友谊常青,那便是曼莱再三说过想要将纽约出租车司机,这个粗鲁可爱的伯尼·西维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荧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由他来演伯尼·西维尔。“现在,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个名字,”他说。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
幸运的是,我还不是一脸茫然。准确地说,这名字虽不是如雷贯耳,但还不至于藉藉无名。这是《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的名字,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依稀有点印象,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名字被体面地提及。噢,这名字可能没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注:(Lionel Trilling,1905-1975),犹太美国人,文学批评家、作家、教师。)”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注:(Reinhold Niebuhr,1892—1971)是本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那样的影响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你可能将它与“亨丁顿·哈特福(注:(Huntington Hartford,美国金融家,也是艺术赞助商。)”或“莱斯里?R?格罗夫斯(注:莱斯里?R?格罗夫斯(Leslie R。Groves。):美国陆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美国向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