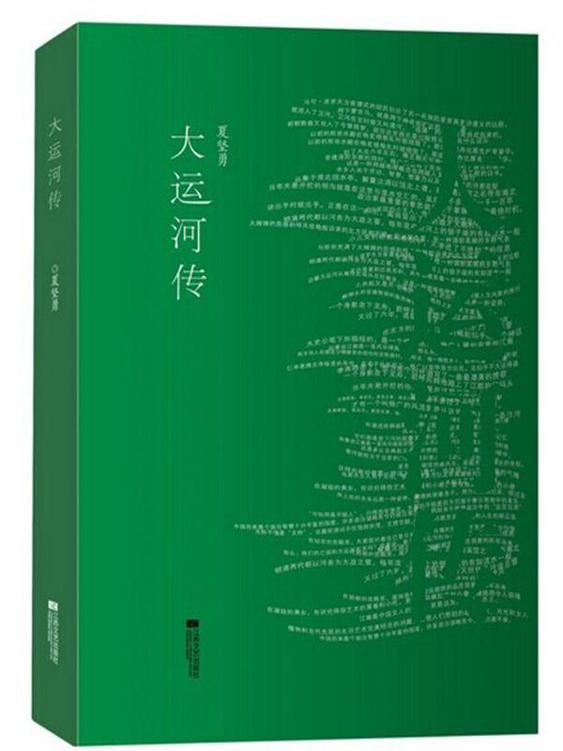大运河传-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运河北段的漕运也整个儿瘫痪了,黄河以北的漕粮也只能改折征收。改折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朝廷现在要的只是银子,至于京师军民的日用衣食,尽可以交给那些无孔不入的商人去操办。有了银子什么不能买呢,何苦总要自己揽在手里,成天为饭碗操心?这个简单不过的道理,他们想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想通。无论是鼓励商船海运漕粮,还是将漕粮改折征银,虽然都是清王朝为摆脱困境而实行的权宜之计,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赋税的货币化进程,有助于加强农民同市场的联系。漕粮的商运或鼓励民间商人运销粮食,更直接有利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分解。有意思的是,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却是在太平军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下,迫使清王朝在无可奈何中最终完成的。
大运河现在被冷落了,这种冷落中透出一股历史的悲凉感和势利味,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庞大的王朝须臾不可缺却的生命之河,京师里的衮衮诸公也不再会因为它的决口或堵塞而忧心如焚,以至奏牍如云、申斥如雨了。但冷落有时只是为了促成某种角色的转换,它虽然不再是一条神圣的河,却仍然不失为一条有神采的河。失去了权势的青睐,也还是有热情的目光注视着它,那是来自民间的。民间的热情不像权势的热情那样云蒸霞蔚一般辉煌,它是家常式的、温润平和的。接连几年汛期过后,有些地方的河道开始淤塞了,但各级官府已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因为到时候自会有商人凑份子拿出钱来,请附近的民工来捞浅。捞浅不是疏浚,那是得过且过的意思,但通航总是不成问题的。商业的法则悄悄地取代了权势的法则,大运河最先感觉到了。在河北山东一带的运河两岸,传统的田园色调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异化,铺天盖地的青纱帐中间,摇曳着棉花和烟草娇嫩的叶片。到了秋后,小镇的运河码头上,收获的棉花和烟草被打成包,装上高桅深舱的航船。而以前,这些船舱里装载的却是漕米、青砖和各类奇货可居的手工艺品。
航船开走了,码头上空寂下来,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提着一个小小的布兜,那里面是一捧鸡零狗碎的残花。秋风过了,棉叶落了,那遗留在棉秸秆上一瓣两枣的残花人家不要了,女孩子用心细细地剥下来,积在一起,想卖掉扯一块花布褂子哩。航船远去了,女孩子仍然站在深秋的晚风中,目送着大鸟似的白帆和航船后面“人”字形的波浪。
在那个季节里,河埠头上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女孩子,在她的身后,秋色在遍野的霜叶中冷寞地老去。
27最后的绝唱
咸丰六年秋天,六十三岁的魏源离开兴化,沿古运河前往杭州。这是在一个苍老的季节里,一个老人向另一个老人的告别之旅。
是的,魏源老了,大运河也老了。三十年前他在陶澍幕中鼓吹海运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气是何等豪迈。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里,他又行进在这条因漕运终止而显得冷冷清清的旧航道上。孤舟寒水,天低云暗,芦花萧萧,满目凄凉,这景况正暗合了他的心境。尽管一本《海国图志》使他名满天下,但名气有时是不能当饭吃的,特别是在势利的科场和官场,名气更是一文不值。“惠抱兰怀只可怜,美人遥在碧云边。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这是何绍基为他鸣不平的诗,他就这样在屡败屡试中误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岁时,才中了个三甲九十三名,这样的名次,对于一个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我查了一下道光二十五年的登科录,那年的状元是一个叫萧锦忠的湖南人,此公是个平庸无为的孝子,夺魁后,在翰林院当了两年修撰,便回家奉养老母去了,直到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因喝醉了酒不慎被炉火烧死。但就是这个怎么看也不起眼的萧锦忠,当年在科场上的排名却要让魏源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其实,就是把清代所有的状元加在一起,也肯定比不上一本《海国图志》的,仅从这一点看,科举的游戏规则也应该改一改了。
魏源在苏北的小县衙里坐了几年冷板凳,就辞官避居兴化,把佛经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凡皈依宗教的智者都是有大痛苦的,魏源的痛苦或许在于他已经看出了清王朝不可救药的大趋势,既然无力回天,便索性横出三界,寄望虚无。于是,他把人生的最后一座驿站选在灵隐寺下的杭州。
小船从内河绕过战火中的瓜洲和镇江,在谏壁附近进入江南运河。北风吹送着孤帆,省却了一路上纤夫的辛苦。漕运的终止加上连年战乱,古运河上一片萧索,原先狭窄的航道也显得宽敞多了。船到苏州,魏源登岸小憩。苏州是人见人爱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来,这里仍然一如往常,小桥流水,幽静如梦,老圃秋香,金桂出墙。阊门的市肆仍然繁喧,山塘的仕女仍然靓丽,桃花坞的年画也仍然充满了俚俗和喜庆。但魏源已经感觉到,这座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正在走向衰落,随着漕粮改行海运,它的地位正在被邻近的上海所取代。从此以后,苏州只能作为上海的后院而存在了,这里精致的园林可以让冒险家们纵横四海的雄心得到休憩,这里的深巷小楼里为他们调教出一茬又一茬色艺可人的姨太太,而这里温丽的山水间则为他们准备了一方死后的墓地。一座曾在中国城市史上勃发出经济和文化原创力的苏州正在消失,它正在变成供人们休闲把玩的一把团扇或一曲评弹。秋风惆怅,美人迟暮,魏源叹息一声,重又登舟解缆。艄公扳动橹桨,搅碎了姑苏城苍老的倒影,旧日的繁华有如流水一般悄然逝去……
几个月以后,魏源病殁于杭州。
就在这之前不久,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海国图志》修缮贴锦进呈,但对于咸丰和他的清王朝来说,一切已经太迟了。
魏源的感觉没有错,不光是苏州,中国东部那些比较纯粹的运河城市都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所谓纯粹的运河城市,是就它们对运河的依赖程度而言的,它们当初的繁荣就是运河滋润的结果,它们和运河是瓜儿离不开藤的关系,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把这些运河城市和衰落联系在一起是很让人伤感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繁荣曾展示了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城市发展的骄傲,而且因为它们在历次战乱后所体现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再生能力。例如扬州,铁血之剑曾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犁为废墟,著名词赋家鲍照的《芜城赋》就是在这里写的,那种“饥鹰砺吻”和“崩榛塞路”之类阴森森的描写让无数后人不寒而栗,芜城也因此成为扬州的代称。可战乱一过,扬州从血泊和瓦砾中站起来,轻描淡写地理一理衣衫,将息好身上的创伤,照样平头整脸的,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段时间以后,便又出落得丰容盛鬋,仪态万方了。扬州的故事属于大运河的历史范畴而不属于权力争逐的历史范畴,决定他命运的是大运河而不是任何一位帝王,即便是最残暴的将领和最平庸的帝王,也不能阻止扬州那凤凰涅槃般的再生,就如同饥寒交迫和风尘垢面不能阻止贫家少女出落得饱满鲜活一样。这些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它依傍着大运河,有艨艟连翩的漕运大观作为它生命的背景,从那里,它获得了生命中所有的色彩、思想和文明的声音。但现在不行了,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被冷落在一边,它生命中一个漫长的冬季降临了。
同治初年,随着太平军和捻军的相继失败,清廷内又发出了恢复漕运旧制的呼声。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当初改制只是在太平军兵锋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同治初年已经不是咸丰初年,更不是道光初年,虽然当皇帝的还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但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的各方诸侯已纷纷坐大,并分享了地方财政收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正项漕粮以外的浮收部分,称之为漕折。这是一笔很大的财源。恢复漕运旧制的呼声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各方诸侯的反对,这中间以曾国藩风头最劲。清王朝到了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的权威已大打折扣,现在他们不得不看地方军阀的脸色了,既然各方老总们的脸色不好,那就只能不了了之。
北京的舞台开始式微,上海那边的好戏却迫不及待地开场了。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上海轮船招商局建立,这在当时并算不上一件大事。但如果联系到这一年发生的其他事情,你就会隐隐感觉到这至少不是一件小事。同治十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终结性和开创性的大事。年初,曾国藩病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位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中兴名臣的死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仿佛为了印证这种论断,这期间,由恭亲王奕䜣领衔修撰的《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二卷和《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相继告成,那一幕让清王朝不堪回首的历史将从此被封存在厚厚的典籍之中,但愿不要被重新提起。不久,容闳率领三十名留学生踏上了开往美利坚的海轮,这是中国政府向西方世界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三十名拖着长辫子的青年才俊中,有一个叫詹天佑的,后来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再接着,就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招商局起初只有三艘轮船,后来又陆续收买了几艘外国洋行的旧船。尽管貌不惊人,也不那么张扬了,但黄浦江上喧闹的汽笛声中,毕竟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这开天辟地的大声音立即改变了航运界的竞争格局,过去一直是美国的旗昌;英国的太古、怡和几家公司之间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全都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地要挤垮招商局。招商局倒也不怎么怯场,凭借着清政府给予的漕运专利及回空免税的优惠政策,在竞争中反倒渐渐地显山显水,羽翼丰满起来。而且,从这里还陆续走出了一批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子,其中包括那位后来名满天下亦谤满天下的盛宣怀。在早期中国的洋务实业中,轮船招商局无疑是办得较有成效的,而在它那巨大的轰鸣声背后,则是大运河日甚一日的冷落。
大运河在冷落中流过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它目睹了那几十年中一个古老民族的屈辱和痛苦,也见识了一些崭新事物在它的身边次第崛起。如果说招商局海运的汽笛声离它还相当遥远,那么,另一个更大的声音却离它越来越近了——那是火车的轰鸣。
光绪二十七年,是中国传统的辛丑年,也是公元二十世纪的第一年。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从西安回来了,他们是去年夏天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城的,走的时候蓬头垢面,仓皇辞庙,一路经河北、山西再到关中,惶惶如丧家之犬,丢尽了皇家的脸面。去年经过的那些伤心之地老太婆这次不想再走了,回銮走的是南路,浩大的皇家车队沿着黄河南岸的古驿道进入中州大地,然后再折向北行。銮驾到达保定时,刚刚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给了太后一个意外的惊喜,他特地为老佛爷安排了一段火车上的行旅——让太后和皇上乘坐豪华的“龙车”回京。虽然铁路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有了好几年,但这个守旧而又虚荣的老太婆却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从来不肯赏光。现在看来,她似乎有意是为了等待逃亡返京的这一时刻,来完成这个历史性的盛大典礼。火车开动了,车站上跪满了花花绿绿的顶戴花翎,西洋乐队呜里呜拉地奏起了进行曲。这一对母子君臣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都想了些什么,我们无法揣测;我们只知道,銮驾回京不久,清廷就发出了一道谕旨:裁撤东河总督,自本年始,各省河运一律改征折色。至此,延续了二千四百五十余年,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漕运制度,终于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久,朝廷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废除科举。于是,大运河上最后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消失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一个书生背着行囊全程考察了大运河。在很多时候,我就这样站在古运河边,而且大致总是在黄昏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眼前的衰飒气象和古运河有某种相通之处吧。是的,我得承认,这当儿看大运河最能看出情调,因为目下的运河(主要是北段)已不再属于诗人笔下的艳词丽句,很有些没落的了。
大运河是衰落了,又恰逢枯水季节,便愈见出衰飒中的戚容。所谓浩荡和明丽自然都说不上,那浅浅窄窄的一脉,自然也失去了往日流畅的叙事风格。水边结着薄冰,是脆弱的苍白,有的地方呈现出类似于石砚上“眼”的那种花纹。水很小,又不时被沙渚割据开来,便有些袅娜的意味。但两岸的河堤却很雄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