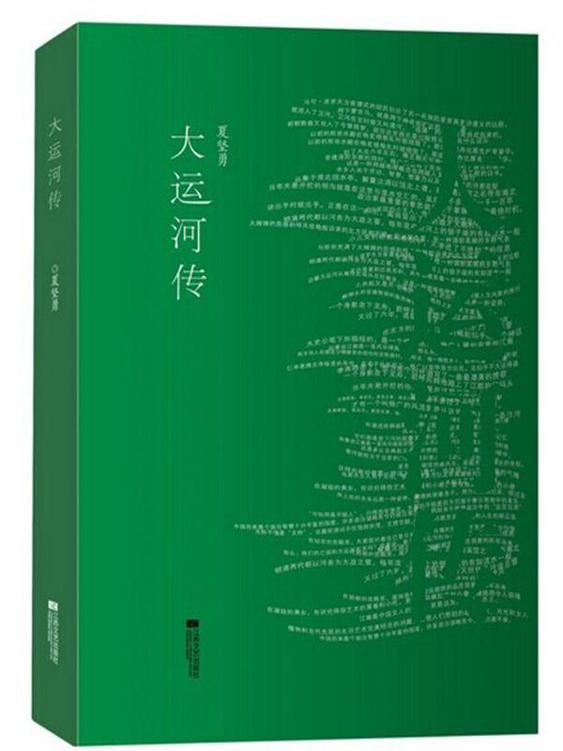大运河传-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昨天,有个传教士告诉我,一艘英国战舰能击溃十艘水师战船。我认为他说得不对,因为一艘英国战舰可以击溃全部中国水师。
电影中的处理是真实的,英国人一点也不是狂妄自大,他们有理由趾高气扬。
还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大清国的灾星到了……”
说这话的是那个名声不大好的琦善,但他说得并不错。
是啊,大清国的灾星到了。蓝色的海洋文明呼啸而来,用坚船利炮打败了黄色的大陆文明,海风中带着一股野蛮的血腥气。在亚洲东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黄河、长江——当然还有大运河——滋润了发达的农耕经济,这里是大陆文明天造地设的舞台,在它的北面和西面是连绵的高山和广袤的荒原,而东面和南面则是浩瀚无边的大海,一切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一切的哲学和生活方式也是孤芳自赏、固步自封的,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由汉唐至明清,这种自给自足的大陆文明走过了它温润的青春和衰飒的中年,现在,它终于走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入了枯槁僵化的生命形态。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由殖民地财富所产生的资本积累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以及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使得大英帝国的海洋文明正处于向外开拓的进取阶段。他们的三桅战舰带着先进的望远镜和滑膛炮,也带着开辟海外市场的扩张欲望和勃勃野心,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划出了一道又一道尖锐的弧线。现在,他们终于进入了太平洋。当东方的大陆文明遭遇到这股生气勃勃的异质文明时,就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美丽的锦帛一样,在新鲜的阳光和空气下顷刻间就破碎了,成为几缕令人惆怅的古典怀想。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孤独地离开镇海,踏上了万里谪戍的征程。
这次走的是水路,小船先沿浙东运河迤逦西行。太平洋的呼唤越来越远了,只有运河里水声喋喋,绵绵忧思化作老人的几滴英雄泪:
不信玉门成畏途,
欲倾珠海洗边愁。
临歧极目仍南望,
蜃气连云正结楼。
“边愁”在东南,而自己却要往西北去了,那回首南望的目光中该有多少壮志难酬的无奈!
过了钱塘江再沿大运河北上,小船在溽暑骄阳下兼程前行。江南的风是纯朴而迷丽的,吹送着六月乡村燥热的泥土味,也吹送着一路细致的风暴。杭州过去了,嘉兴过去了,吴江过去了,大运河脉脉无言,它实在有太多的悲愁无以言说。真正的大悲愁总是不屑于诉说的,每年进入京师的漕粮,有一多半出自江浙,千船万斛,千辛万苦,都压在它苍老的双肩上。可是这种殷勤的供养却没有让王朝鲜活起来。林则徐突然觉得大清国就像运河两岸那田间的稻草人一般,远望时摇曳生姿,张牙舞爪,其实那都是吓唬人的;走近一看,只是一副风雨飘摇的空架子。想起来真是羞愧,自己当了大半辈子封疆大吏,也自视勤于王事,所谓日理万机无非是河务、赈灾、钱粮、刑狱,何曾想到外面的世界竟如此大变。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对于他个人来说,这种羞愧是迟了点,但对于一个民族,知耻而勇,奋起直追还不算太晚。
林则徐的这种羞愧并不是官场失意之后浅薄的自嘲,也不是在万里遣戍的百无聊赖中偶有所感,而是一个富于使命感的封建士大夫带有根本意义的觉醒,这种羞愧将他生命中所有的智慧、才华、良知和勇气都凝聚成一种欲望。他觉得自己老了,大清国也老了,而站在对面的夷人却很年轻,连同他们年轻的舰船和大炮,甚至他们那些神奇机巧的小玩意——比如来复枪、龙尾车、量天尺、千里镜等等——都是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世道大变,天外有天,不睁开眼晴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行了,尽管这样会很痛苦。但既然你选择了责任,你就不能逃避痛苦。敢于面对痛苦也显示了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质量,痛苦的过程就是涅槃的过程,不经过痛苦,你便永远只能在痛苦中沉沦,因此,拒绝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体味痛苦。当然,以林则徐的性格,看世界也只能站着看,决不会跪着看。站着看是一种比试,既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又不失去炎黄子孙的尊严。那是一颗不甘屈辱的灵魂在和对手较劲,“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他抖擞身姿,把意气和激情埋沉在心底——如同夕阳满面羞愧地埋沉于西方的山海,为的是第二天更加辉煌地升起来——即使退却也不失丈夫气。而跪着看则是奴才对主子的仰视,懦夫对恶棍的乞求。跪着看的结果是永远看不懂,只会越看越觉得自己卑微,精神会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只恨自己这辈子选错了爹娘。他们当然不会有痛苦,至少不会有大痛苦,因为大痛苦只属于坚挺的脊梁——当它被强行按下去时,那挣扎的愤怒和忧伤便酿成痛苦。没有脊梁的人,既不配体味痛苦,也无缘体味痛苦。
那是一个在痛苦中思考和在思考中痛苦的时代,从道光十九年三月踏上广州天字码头,到二十一年六月离开战云密布的镇海,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林则徐的思考和痛苦超过了以往五十年的总和。现在他遭遇了遣戍,又在遣戍途中遭遇了大运河。大运河是柔性和诗意的,月色下的吴歌把夜晚拉得很长,几星雨点就打湿了所有的河埠头和石板桥,乡村的迎神赛会充满了浪漫情调,整个江南都飘散着新麦饼和土烧酒的香气。十八年前,林则徐曾担任过江苏按察使,后来又擢升江苏巡抚,江南的山水风情对他是有着肌肤之亲的。命运对他是如此苛酷却又如此多情,在他最需要宁静的时候,又把他从喧闹的官场解脱出来,并赐给他一段古运河上的孤旅,为的是让他将痛苦和思考沉淀为一种思想,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思想如果仅仅是思想者个人的财富,那也就仅仅是“思”和“想”,而不是思想。只有像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的思想,才有资格最终被称为思想。六月的江南运河如同一阕性灵派的诗词,在它的两岸,平原古典地铺展又古典地向后退去,苏州过去了,无锡过去了,常州过去了,这些江南名城都是倥偬消逝的风景。小船兼程前行,风也匆匆水也匆匆,急切得有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去赶一次盛妆舞会,那里的一切都是心仪已久的,她期盼着一次开天辟地般的牵手和托付。
到了镇江,终于泊船,起岸。
林则徐要在这里盘桓几日,无论对于自己还是自己的民族,现在都处于一个大生死和大抉择的紧要关头,这时候,他更加渴望与魏源和龚自珍的相会。什么叫挚友?除了心灵之间的倾诉和倾听,理解和慰藉,相濡以沫和相映生辉而外,他们在人格和精神上也大体是同一档次的,这样,他们的交往才能不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和创造的快乐。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彼此都是情感和意志的延伸,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排除临难受命拍案而起甚至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他与魏、龚就是这样的挚友,这两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奇男子,许身家国,快意恩仇,举世皆昏,唯我独醒。他们随口甩出的几句牢骚也远远胜过朝堂上衮衮诸公们的竟日高谈。现在,魏源在扬州赋闲,龚自珍在丹阳教书,林则徐选择了镇江——在扬州和丹阳中间,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来完成自己庄严的托付。
镇江以它吞天吐地的胸怀迎接林则徐的到来。吞天吐地是镇江的位置决定的,运河在它臂间浩荡,长江在它脚下雄浑,一个力重千钧的“镇”字写出了它的壮夫本色。“地雄吴楚东南会,水接荆扬上下游。”这里襟带江海,提挈吴越,永远总是艨艟连翩的浩大景观。但吞天吐地不一定就表现为喧嚣浮躁,相反,只有浅薄的小溪才喜欢神气活现地大声呼喊。镇江恰恰是一座不事张扬的城市,它甚至有点灰头土脸的,全不似苏州和扬州那般招摇,因为名分都被它们占尽了,出头露面作人来疯的是它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也是它们。镇江只有劳碌的份儿,而劳碌者总是沉默的。但沉默的精神不在于享受沉默而在于积聚力量,如果把沉默惯性化恰恰是背叛了沉默的精神。于是便有了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和辛弃疾“何处望神州”那样的大声音。镇江要么沉默,要么就发出振聋发聩的大声音,因为有了这大声音,它平日里灰头土脸的沉默才不是一种无奈;而显出了比喧嚣更有力量的大气。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当主战派和主和派在金銮殿上沸沸扬扬地争论时;当清朝水师在沿海要塞收集妇女的尿盆和月经带,置放在木筏上用于御敌时;当道光皇帝和满朝文武都相信夷人没有膝盖,一打就倒,一倒就爬不起来时;当大英帝国的舰队连破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一路势如破竹时,几个忧国忧民而又肝胆相照的挚友相会在镇江。直到若干年以后,人们在翻阅近代史时才会注意到,在那个多事之秋,决定中国命运的巨擘其实既不在京师,也不在广州,而在镇江的一处不起眼的庭院内,几个朋友一次不事张扬的晤谈之中。风清尘不到,潮带海声来,那座小小的庭院,连蝉噪和茶香也是令后人怀想的。
这次聚会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是:由魏源执笔,编写一本介绍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
北固山下,没有响起梁红玉那样驱策千军的战鼓,也没有发出辛弃疾那样壮怀激烈的豪语,只有几个朋友晤谈之后的执手一握,但中国的近代史却感到了那一握中的热情和力量,在蒙昧和苦难的中国,那热情和力量足以托起一颗新世纪的太阳。林则徐给魏源带来了他收集的大量关于西方、关于世界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在广州作钦差大臣时组织人翻译的西方地理书、地图册,以及澳门出版的英人报刊,还有关于鸦片战争的重要文件。在看到自己的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时,能意识到需要知识和思想,而后才能言及战略和策略,这是那一代思想家了不起的觉醒。
长夜沉沉,大野寂寂,一派朦胧的天光射向镇江,一部划时代的煌煌巨著就要诞生了。
《海国图志》。
哦,海——国——图——志!
我们对大海本来是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身边就依傍着世界上最浩翰的大海,历代的帝王也无不宣称自己“富有四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诗人的笔下,大海从来就是激情的渊薮,充满了浪漫的诱惑力。可是我们走向大海的云帆却很少升起,可怜的几次远航,一次是徐福,目的是为帝王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一次是郑和,那只是炫耀国威的政治游行,顺带着为主子寻找一个流亡在海外的政治上的对手。除去自己手中的权杖和那一副贪得无厌的臭皮囊,他们还能关心什么呢?大海是帝国的屏障,幸甚,幸甚!至于大海另一边的世界,他们从来懒得去想。一个依傍着大海的民族,关于大海的激情和想象力却日益枯竭,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我们对海外诸国同样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曾失去了多少次与人家交往的机会。作为“天朝上国”,我们从来总是把自己以外的国家称作“蛮夷”,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本来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要和人家交往什么呢?远的且不说,最近的一次,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率船队远涉重洋访问中国,带来了包括毛瑟枪和榴弹炮在内的六百箱礼品,要求与大清帝国签订贸易协定。但傲慢的乾隆不仅拒绝了人家的要求,还在敕书中老实不客气地把人家教训了一顿,说“中华万物皆备”,无需这些左道旁门的玩意。结果,才过了不到五十年,人家就带着当年作为礼品而不被主人笑纳的枪炮打上门来,把“天朝上国”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
那么,我们难道应该对一张展示外部世界的地图陌生吗?历史上的张骞西行、鉴真东渡、甘英出使古罗马帝国(据说此行曾一直抵达巴勒斯坦),都曾是我们走向外部世界的大举动。但那些只是汉唐遗事,随着汉唐大帝国从历史舞台上的消失,中华民族那种雄视四方的气魄也逐渐衰退,连同当年留下的那些地理图册亦散佚殆尽。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闭关自守,不再需要对外进取和交往,还留下这些劳什子何用?最后一批地图是被烧毁的,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档案付之一炬,其中就包括航海图,目的很简单:为了防止后人仿效。我们当然也拥有不少勉强可以与地图沾边的东西,有些甚至被作为国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