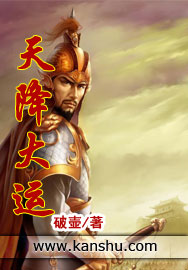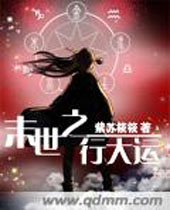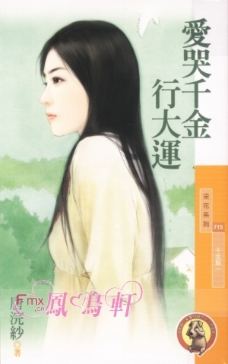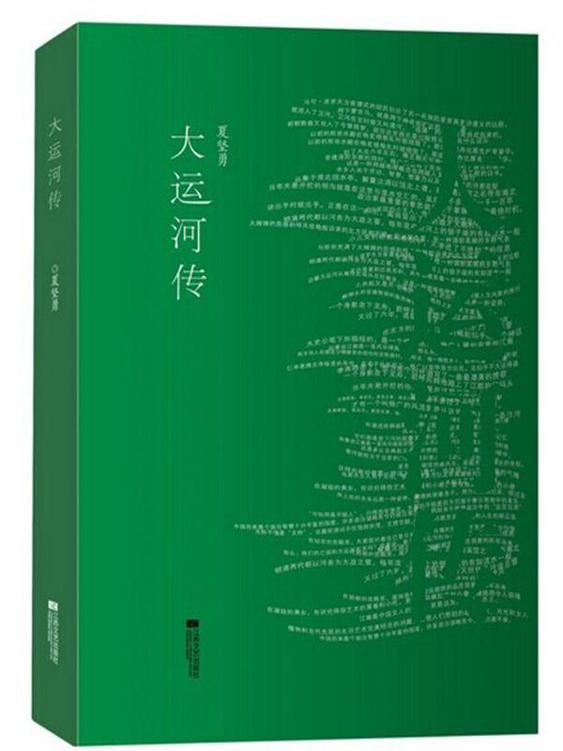大运河传-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就想些别的吧,例如,这些园林连同京师宫城里的那些大殿子大多是南方香山匠人的手艺。香山是多好的名字啊!香草美人,钟灵毓秀,词义和语感里天生就蕴含着某种艺术气质。正因为名字好,中国叫香山的地方太多了。这里所说的香山匠人来自苏州,他们中间包括:木匠、泥水匠、堆灰匠(泥塑)、雕花匠(木雕、砖雕、石雕)、叠山匠等。记忆中的很多场景都是过眼烟云,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痕,但有些场景却是流不去的。早在北宋末年,香山匠人就沿着大运河北上,来到开封给皇帝造园子。那带头的朱勔是个造园高手,开封著名的艮岳就出自他的手笔。天底下恐怕没有比那更大的人工园林了,周遭十余里,全用江南的太湖石堆叠而成,再加上楼台亭阁和各地搜集来的奇花异草,端的是人间仙境。连宋徽宗那样艺术素养很高的人都很赏识他,让他担任“苏杭应奉局”的官职,奉命采办“花石纲”。一个造园子的工匠当什么官呢?你只是有点技术和管理才能,老老实实地做个手艺人就是了,一旦沐猴而冠,命运的悲剧也开始了。后来国家危难时,朱勔与蔡京、童贯、高俅等人一起被斥为祸国殃民的“六贼”,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他这种没有什么根底的人自然只有杀头的份。他死后,家境亦一落千丈,但好在子孙都有一门手艺,吃饭还不成问题,他们“游走于王侯之门,俗称‘花园子’”。这比那些纯粹的政客可好多了。例如同为“六贼”的那个梁师成,也曾官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但这种人除去投机钻营,皮囊里什么货色也没有。没有货色便只能千方百计地去附庸。他的附庸有点特别,竟到处吹嘘自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私生子,说是苏东坡的侍妾带着身子嫁给了姓梁的生下了他。《宋史·梁师成传》中说:“师成实无文,而高自标榜,自言苏轼出子(被遣出侍妾之子)。”他说得可能不错,苏东坡在一再被贬的情况下,也确曾遣散过侍妾。但这种事若放在嘴上吹嘘,且大言不惭,就实在没有意思。梁后来被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行到半路,被押送人绞死。他是太监,自然没有后人,这样也好,如果有,也肯定不像朱勔的后人那样有一门手艺可恃。“六贼”中的其他几个人,一旦树倒猢狲散,后代竟有沦落街头为丐为娼的。所以奉劝世人,官场是靠不住的,还不如正经学一门手艺的好。
其实,也不是说工匠就不能当官,同样是香山匠人出身的蒯祥就当得很不错。他是北京明宫城的总设计师兼总工程师,说到底也是靠手艺吃饭的。从永乐到成化,蒯祥一生侍奉过六代君王,最后官至工部侍郎,食从一品。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分别珍藏着一张《明宫城图》,图上画的是明代紫禁城建筑群,崇楼巍阙,金碧辉煌。令人注目的是,在画面左侧华表下有一位纱帽红袍的官员,器宇很轩昂的,他就是蒯祥。顾颉刚先生认为,这张图上蒯祥的“人形特大,与建筑比例不称,盖明帝重其人,所以纪念之也”。皇帝为什么看重他呢?因为他主持营造的宫殿是皇权的象征。宫殿和园林是有区别的,可以这样说,造宫殿是帮忙,而造园林则有点帮闲的味道那园林本来就是供帝王休闲游乐的。若是太平盛世,那倒没什么可说。若遭逢末世,万方多难,最后总要归结到“耽于安乐”这一点上。皇帝自然没有什么过错,那帮闲造园子的就难辞其咎了。也是朱勔活该倒霉,谁叫他生不逢时的 呢?
顺便想起一件不大不小的轶闻,说出来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当初英法联军进京后,在如何惩罚清政府这一点上,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曾发生分歧,英使主张焚毁圆明园,法使主张焚毁大内皇宫,后来考虑到若焚毁皇宫,清王朝有可能垮台,他们攫取的利益亦随之丧失,才最后选择了圆明园。可见在洋人眼里,宫城也是皇权的象征,非同小可的。现在想起来,像紫禁城那样举世无双的大古董能得以保存,确是不幸中的大幸。但一想到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民族所经受的那些耻辱,我倒要狠心说一句:还不如让洋人烧了紫禁城的好,如果它能换取一个腐朽体制的提前垮台和一个古老文明在烈火中重建的话。
烧圆明园,痛;烧紫禁城,亦痛,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注定了是一部血与火的痛史。
流过了京师的胡同、宫阙和园林,也流过了元明清三代的盛衰兴亡,大运河无可奈何地衰老了。现在,它枕着昆明湖上的画舫,静静地品味着北方的京韵大鼓。京韵大鼓是可以和南方的评弹相媲美的,它似乎最适合于风尘女子演唱,因为那曲调中有一种揪人心魂的身世之感。人的身世与河的身世在感情上是相通的,回首南望,四千里风尘,六百载岁月,最终就流入了那份不绝如缕的伤感之中。大运河黯然无语。
黄昏悄悄地莅临了,树的影子拖得很长。大雁掠过长空,它们是大运河最忠实的伴侣,每年的春风秋月中,它们都要追逐着运河上的帆影从南方飞向北方,又从北方飞向南方。也只有它们可以作证,眼下这苍老的河床,当年也曾有过恣肆洋洋的青春,那史诗般浩大的船队,曾多少次让它们迷惘:究竟哪是天?哪是地?哪是白云哪是帆……
时间篇
21庸才时代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二月,江南已很有点小阳春的气息了,但是在北方,春天的脚步却总是姗姗来迟,京师的杨柳瑟缩在料峭的寒风中,枝头上还沾着薄薄的冰花。来自塞外的沙尘把紫禁城搅得浑浑噩噩的,一副灰头土脸不解风情的样子。谯楼上隐隐传来报时的钟鼓声,一声声沉闷而苍老,仿佛来自一个遥远的世纪……
道光帝旻宁一早就起床了,在清朝的历代帝王中,他是资质最差却又最勤勉的一个,一年到头宵衣旰食,因此眼圈上总是带着几分疲惫。盥洗之后,他坐到御案前,先读了一段先朝《实录》——这是他每天的例行功课,从来不敢懈怠的——但思绪却怎么也走不进先辈那辉煌的文治武功中去,他知道是昨晚签发的那道谕旨让他心神不定,便索性丢下《实录》,又把谕旨细细看了一遍,似乎还要作最后的定夺。资质差的人往往谨小慎微,又特别注重细节,总想把什么事都办得滴水不漏。这或许也和他十七岁就被内定为皇太子,直到三十九岁才登基即位有关,漫长的等待是在如履薄冰的拘谨中度过的,把一个帝王本该具备的胆略和气魄一点一点地消磨殆尽。况且漕运关乎天庾正供,兹事体大,不能不再三斟酌的。想到这里,他又提笔在谕旨的后面加了两句:
至江广帮船应否同江浙漕船一体转运海口,俟江浙等帮海运有所成效,再行归并筹办。
写完以后,又看了一遍,觉得很妥当了,才最后下定了决心,叫内臣拿过去用印,天亮后再送到军机处去。
这是一封关于漕粮试行海运的谕旨,确实不同寻常。
清代的历史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康乾盛世”的余辉已日见黯淡,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华彩演出,几乎耗费了它全部的家底和行头,也耗费了它全部的生命精神。既然一切都已经登峰造极,那么等待着它的只能是人去场空的大悲凉。而曾经为那场演出殚精竭虑的大运河也一下子衰老了,如同一个早年操劳过度的村妇,一进入中年就过早地显出了龙钟之态。它蓬头垢面,步履蹒跚,原先健壮饱满的身躯变得松垮疲塌了,仿佛纸糊的一般,再也经不起风吹雨打。那日益枯瘦的运道是它白发下的皱纹,记载着与生俱来的劳碌和忧患。特别是苏北里运河那一段,由于黄河和洪泽湖的轮番侵淫,更是危如累卵,老天爷打个喷嚏也会引出一场塌天大祸的。虽然历朝历代都把河务和漕运作为头等大事,但每年四百余万石的漕粮转运,压迫得大运河连喘气的机会也没有,因此,所谓整治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结果是越补越破。就像道光黄帝裤子上的补丁那样,流感一般传染了满朝文武,弄得朝堂上一片破旧的气象。河漕积重难返,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从嘉庆年间开始就有人提出漕粮改行海运的建议,但事关祖宗成法,每次廷议时都要吵得昏天黑地的。从表面上看,海运与河运只是走漕的形式之争,但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即从传统的政府包揽向招标商办的变革。官办的河漕体制法久弊生,养活了一大批冗官蠹吏,上至中央大员,下至仓胥运兵,一个个都乐此不疲地营私舞弊,把漕运视为自己千年不败的铁杆庄稼。一旦变革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便如同掘了他们的祖坟一般,岂能善罢干休!加之嘉庆道光这两代帝王都是守成之主,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海运之议,遂一再搁置。
到了道光四年,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由于南黄河水骤涨,高家堰漫口,自高邮、宝应到清江浦一线运道浅阻,挽输艰难,到了北方的漕船放空都回不去了。天大地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的好多事情不等到饿死人的时候是不会有人去解决的。如果光是老百姓没有饭吃倒也罢了,问题是运河梗塞,正供无源,若长此以往,恐怕连达官贵人也要喝西北风了。到了这时候,还死抱着祖宗成法有什么用?因此,当江苏巡抚陶澍重提海运时,道光只得同意让他试试。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壬戌进士。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湖南人是很干了一番事业的,咸同年间的几位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差不多都是湖南人,其中左宗棠是陶澍的儿女亲家,而胡林翼则是陶澍的女婿。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崛起,大致就是从陶澍开始的。
道光皇帝让陶澍试试看,但陶澍知道,其实用不着试,海运肯定比河运优越。
陶澍来到了上海。那时的上海,由于海运的发展,已经很有点模样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以来,往返于天津与上海之间的沙船日益增多,商家将关东地区的豆麦运至南方销售,每年的运量都在一千万石以上。然后再将布匹、茶叶等“南货”贩载北上。由于南货分量较轻,且往往不能满载,故称“放空”。为求船行平稳,常常不得不在吴淞口用泥土和石块压舱。现在正好利用这些北返的沙船运载漕粮,既然是“放空”捎带,运费自然低廉,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挣一个是一个。陶澍是个很干练的人,一切都办理得相当顺利,从接到圣谕到漕粮出海,只在兼旬之间。当他站在吴淞口外浩荡的春风中,目送着装载漕粮的沙船扬帆北上时,这位湖南人都想了些什么呢?后人不得而知。好在《清诗记事》收有他当时写的几首七律,从中可以窥见一斑。且看:“申浦重来策骑从,望洋镇日话从容。”何等的潇洒;“指点扶桑云五色,日边好路近长安。”又是何等的自负,那种躇踌满志的心态跃然在目。这里所说的“好路”恐怕不光是指海运漕粮这件事本身,而且也包括自己的官场仕途的。“日边好路近长安”,他说得很含蓄,但无疑又是满怀憧憬的,对眼下的事业和今后的前程都充满了信心。沙船从上海出发,经崇明十水滧而东,再沿南黄海北上,扬帆四千余里,十余日即达天津。接着回空再运一次,五月中旬即两运告竣。由于运期缩短,漕粮霉变损耗大减。加之商船“不由闸河,不经层饱,不馈仓胥”,省去了许多盘剥和周转,较之河运,不仅节约了十余万石的损耗,还少花了十余万两的运费。而对于商家来说,既能弥补北上放空之损失,可又增加收入,自然闻风鼓舞,乐得为之。道光六年春天的首次试行海运,可谓相当圆满。
这样看来,海运确是应当替代河运的了。
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随着海运的成功,反对阵营的鼓噪也随之甚嚣尘上,其中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危害耸听,以“稳定”来要挟皇上,说废除河运将造成数万运丁和水手下岗,这些人的饭碗被敲掉了,必然心怀怨愤,聚集滋事,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他们甚至故意制造谶语,神神鬼鬼地散布什么“木龙断,天下乱”。木龙者,漕船之连樯也,意思就是废除河运将招致天下大乱。这实在是很厉害的一手,对于任何一位统治者来说,最让他们耿耿于怀的就是“稳定”。既然稳定压倒一切,自然也就压倒了变革、压倒了民主、压倒了惩治腐败的正义呼声,也理所当然地压倒了老百姓的肚皮。为了稳定,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可以付出的,只要自己还坐在权力的殿堂里,其他什么都好说。于是,维护稳定便成了贪官污吏们维护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