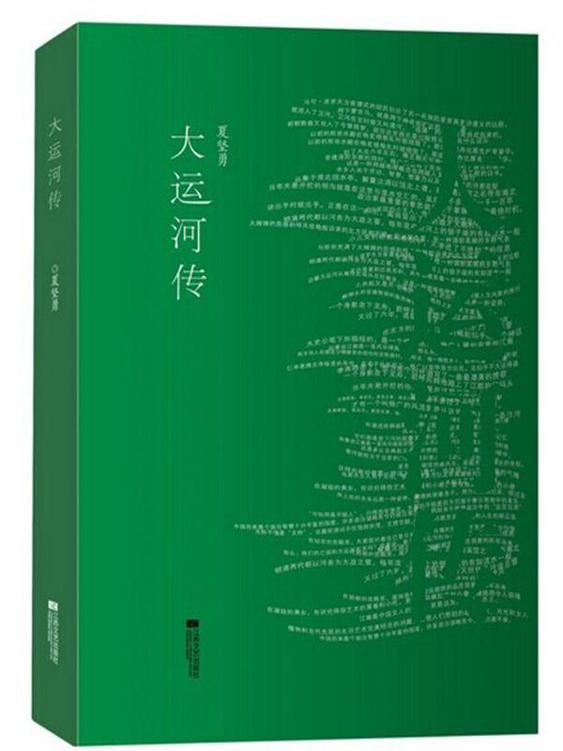大运河传-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龙舟到了邵伯,先头的陵波船已抵达江都,派快马送来消息:江都那边接驾的一应准备已经就绪,地方官奏请北上迎驾,请皇上恩准。
杨广哈哈一笑:不必了!
而这时,殿后的艚和八棹船才到了离江都二百里的高邮。
11雄视四方
江都是杨广魂牵梦萦的地方,这里的市井街衢都是旧时岁月,虽然有些沧桑意味,但骨子里头还是熟悉的。朱门红楼和夕阳芳草的那种哀艳,也是他原先就很欣赏的情调。如今皇帝来了,便每天都有花团锦簇的热闹。皇帝也很定心,有点宾至如归的意思。但虽则是热闹,杨广还是看得出江都比几年前憔悴了不少,像一个落尽铅华、素面素心的女人,显出某种困窘和无奈。他觉得很对不起江都,在他看来,这歉疚是只有多住些日子才能补偿的。那么就多住些日子吧,顺便到四处走走、看看。说是“听取舆论,考察风俗”,其实车驾出了行宫,仪仗警卫便“填街溢路”,往往长达二十余里。在这种场面下,不知他是如何听取舆论,又是如何考察风俗的。好在杨广是喜欢热闹的人,怎样排场也不为过的。既然来了,还得给江都的父老乡亲们一点见面礼。他大笔一挥,赦江淮以南所有的罪犯,又免除扬州五年的徭役,这些都是毛毛雨,乐得为之的顺水人情。当然,国家大事他也没少操心。草黄马肥,大漠穷秋,契丹骑兵进犯营州。杨广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以突厥军队讨伐。但他对突厥人也不放心,又令韦云起为监军。战事进行得还算顺利,契丹人稍一接触就引兵退去。这件事给杨广提了个醒:北方并不安定。在内政方面,他派出十名钦差巡视天下州县,以改变“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弊端。对拥戴他上台,并以世袭特权充斥于朝廊的关陇军人集团,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现在,他开始着手改革官制,并为一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制度——科举选士制度——的出台作好了铺垫。
余下的精力就是游乐,当然还有写诗,且看:
暮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文辞很华美,也有点雕琢,不脱六朝宫体诗的脂粉气,比之于《大风歌》那样即兴喊出来的诗句,总觉得少了点风骨,这或许就是杨广与前代那些成就一代霸业的帝王在人格精神上的差距吧。这首题为《春江花月夜》的乐府诗,令人想起一百年后张若虚的那首同题大篇。张若虚是“吴中四士”之一,在初唐诗坛上很有点名气的,《春江花月夜》亦是他的得意之作。后人认为,张诗的开头四句就是受了杨广的影响,他那四句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流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比较一下,确实可以找出点痕迹的。
大业元年余下的日子,杨广都交给了江都,还连带着第二年那一段春暖花开的季节。
到了三月中旬,他又要启驾登程了。不是在江都住腻了——他和江都有一种天生的亲和感,永远不会腻的——而是想到了北方。这么大一个国家,皇帝也不好当哩,更何况是一个雄心勃勃,处处都要争强好胜的皇帝呢?在很多时候,杨广都处于被两种力量向相反方向使劲拖拽的感觉,这两种力量是:南方和北方。南方是一种诱惑,属于感官和灵性的;而北方则是一种责任,它更多地属于理智。在短短的十三年中,他三次南巡,四次北巡,一次西巡。如果说南巡还带有某种游乐性质的话,那么像青海那样的不毛之地又有什么可以游乐的呢?我们不应该忘记,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亲巡河西的中原帝王。绝域苍茫何所有,平沙莽莽黄入天。深入到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巡幸,即使贵为天子,也仍然是要吃不少辛苦甚至冒不少风险的。好在杨广正值盛年,体魄还不成问题。他喜欢把精力释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这种生命方式至少是值得赞赏的。我们已经看惯了那些坐在深宫里病恹恹的老人,口角流涎,目光浑浊,连画个圈也要别人代笔。因此,远望着杨广在漫天风沙中西巡的身影,精神总会为之一振的。
从江都回程走的是陆路,自然又是另一番排场。先到洛阳看了新落成的宫城,很满意的。又到长安小住了几日,然后便下诏北巡。这一次去的地方是雁门关外的突厥。去年秋天的边境冲突使杨广有了一种危机感,那是些怎样骁勇强悍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啊!他们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征战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长啸如风,马蹄如雨,从来就是他们创造生活的光荣与梦想。曾经的金戈铁马接天盖地而来,将大漠边关踢踏出蔽天的征尘,那张弓搭箭的身影,只有以整个天幕为背景才能恣肆伸展,那草原民族特有的眼神,有如鹰隼一般,注视着南方的子女玉帛。千百年来,他们的马蹄曾多少次踏碎中原王朝的笙歌舞影,又有多少中原男儿在与他们的殊死搏杀中建立了自己的不世功业。“羽檄频年出凤台,边云漠漠战魂哀。”塞外的多事之秋,成了中原天子心中永远的忧患。那么,就摆开架势去怀柔一番吧。所谓怀柔,无非就是夸富逞强,耀武扬威,恐吓镇服而已。对这一点杨广有着足够的自信。
果然,杨广的东驾刚出了雁门关,突厥的启民可汗就带着隋朝的义成公主前来朝见,并上疏“请变服,袭冠带”,他说得很动情:
微臣今天已不是以前化外之地的突厥可汗,而是至尊(皇上)的臣民。请至尊可怜微臣的一片孝心,允许全体突厥人改穿华夏大国一样的服装。
杨广遂在临时搭建的“行城”内召开御前会议,令臣下就此进行会商。公卿们都认为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一致“请依所奏”。
但杨广却认为不可,理由是:“君子教民,不求变俗。”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说法,深层次的意思是:你光是让他们换一身衣服有什么用?关键还是要他们心存敬畏。况我泱泱大国、煌煌盛世,让各种不同的风俗共存共荣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一点上,杨广可要比满朝文武高明多了,他以自己的明智和豁达,表现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尊重,他处理民族关系的这种度量和政策水平,可以说是具有历史高度的。在给启民可汗的诏书中,他说得很恳切:“碛北未静,犹须征战,只要好心孝顺就是了,何必改变衣服呢?”
应该承认,这时的杨广已是一位相当成熟的封建政治家了。
接下来是一系列热烈而友好的场面,互相宴请、互赠礼品,朝廷方面的赏赐更是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光是赐给启民可汗的锦帛就有二千万段,这还不包括下面的部落首领。慷国家之慨,杨广的手面向来是很阔绰的。在启民可汗的牙帐中,他曾洋洋得意地即兴赋诗,其中有“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句子,把曾经大败匈奴单于的汉武帝也不放在眼里了,可见自我感觉相当不错。
这次北巡杨广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重修长城。但是也埋下了一个祸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祸根最后直接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
事情的起因完全是一次很偶然的遭遇。
就在杨广这次北巡期间,高丽也派人出使突厥。高丽出于对隋帝国的疑惧,与突厥暗中通好,这也是很正常的。但问题是,这位使者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当杨广来到启民可汗的牙帐作客时,高丽的使者已先到了一步。这时的可汗已被杨广一路上大摆阔气、大扬武威的声势吓住了,他不敢私下“隐境外之交”,遂引高丽使者入帐拜见杨广。
这件事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偏偏这时候有一个叫裴矩的大臣讲话了,他说高丽自古就是中央王朝的藩国,这些年却既不来朝拜,也不肯进贡,“藩礼颇缺。”以陛下这样亘古未有的盛世,怎能容忍它作境外之邦呢?他这么一怂恿,杨广就板起面孔给人家颜色看了,他要高丽国王马上到长安来朝见,否则,他将率领启民可汗的兵马——接下来他用了一句很含蓄的外交辞令——“巡行你们的领土。”
这话中的意思当然谁都可以听得出来的。
这里得说一说裴矩这个人,因为在杨广一系列对外政策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他的身影。首先,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聪明主要表现在善于迎合杨广的心理,这使得他很受杨广的赏识。其次,他还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他花费了半生的精力,跋山涉水地考察西域各国,写下了厚厚一本《西域图记》,书中不仅对西域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有相当详实的记载,而且文笔也很不错。正是这本书,后来激起了杨广的野心和冲动,“梦想仿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征服整个中亚。”这话是《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说的。当然,作为杨广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臣,裴矩本身也是一个力主扩张的人,因为他个人的权力欲望是寄生在君王对外开拓的事业大树上面的。
祸根就这样埋下了。高丽国王本来就对中央王朝心存疑惧,这样就更不敢来朝见了。他愈是不来朝见,便愈是燃起了杨广的征服欲望。对于隋帝国和杨广的命运来说,启民可汗牙帐中的这一幕,是在不适当的时候,不适当的地方,进行的一场不适当的会见。读到这段情节,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惊栗和无奈。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而历史进程总是隐藏在无数偶然性之中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发问,如果高丽使者不是正巧在那个时候访问突厥;如果启民可汗不那么多此一举,把他引见给杨广;如果裴矩当时不在场,或者不讲那一通极富煽动性的话,后来对高丽的战争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呢?而隋帝国是不是就可以不那么短命呢?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之力,有时只是体现在一些随机性的小情节之中,它们的存在,不只是为历史斑驳的图像添上了几分神秘色彩,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人类精神的某种本质。
但不管怎么说,祸根已经埋下了。一个欲望既然被点燃了,就肯定要烧出疯狂的火焰,这就是杨广。“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是他后来对宫女说的悄悄话,他也把事件的发端归结于“偶然”,可见已有悔意,但那时的局面大抵已糜烂得不可收拾了。
杨广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征辽作准备了。
大业三年春季,杨广第二次北巡,这次的主要目的是巡视长城,安抚漠北的少数民族,好腾出手来对高丽用兵。
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五百余万开凿永济运河,引沁水南通黄河,北抵涿郡。这样,杨广从他常住的江都乘龙舟入邗沟,转通济河,由板渚渡过黄河入北岸的沁口,再由沁口入永济河,循永济河可直达涿郡蓟城。自战国以降,蓟城就一直是北方的军事重镇,杨广对高丽用兵,就是靠永济河漕运军需物资,而蓟城则是他的前敌指挥部。
这是大运河与长城的第一次近距离相望,一次愚蠢的战争,将大运河延伸到了燕赵古长城的视野之内。
现在,中国版图上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朋的“人”字,它的一撇是广通河、通济河和邗沟,贯通关中、中州和江淮;一捺是新开凿的永济河,贯通幽燕河北。这个“人”的脑袋在长安,心脏在一撇与一捺交接处附近的洛阳,而落脚点则是南方的江都和北方的涿郡。它是如此雍容端庄,又是如此峭丽如割。它有着高贵的精神,又有着平民化的品格。它的美是安祥的,也是傲慢的。有了这个“人”,中华民族将更加坚实地站立在世界东方的这块土地上,连同他的黄皮肤、黑头发、方块字,还有那具有独特表现力的诗词歌赋。虽然在后来的千百年中,它的形态还会发生种种变化,变得不成其为“人”,但它的内在精神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建立什么样的功业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杨广遭遇了运河(请注意,是遭遇,而不是寻找),并将自己的激情和才华附丽在运河身上。这激情和才华不可抗拒地漫过来,有一种厄运的味道。大运河的光环太炫目了,它几乎掩盖了作俑者的残暴、荒唐和骄奢淫逸,使得他们都有了某种堂皇的理由。而杨广本人也因此超越了政治动物的范畴,具有了更多的审美意义——在一种华丽的、紧张的、破碎且富于诗意的美丽中,流动着有力量的感伤,让人惆怅不已。这就是杨广和他的那个时代。
12盛世
到了大业六年左右,隋王朝无可奈何地到达了盛世的极顶。
之所以说“无可奈何”,就因为这个“极顶”实在不是什么太美妙的恭维。什么东西一旦到了“极顶”,接下来的就是风光不再,开始走下坡路。因此,这个“极顶”是分水岭的意思,也是衰落前的最后一次豪宴。这时候的场面最盛大,歌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