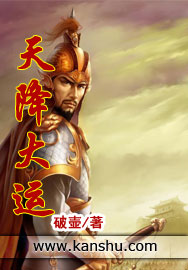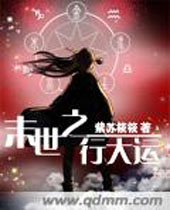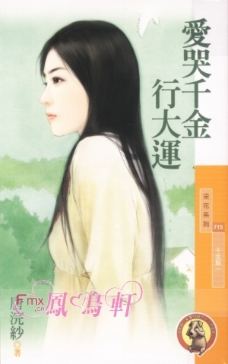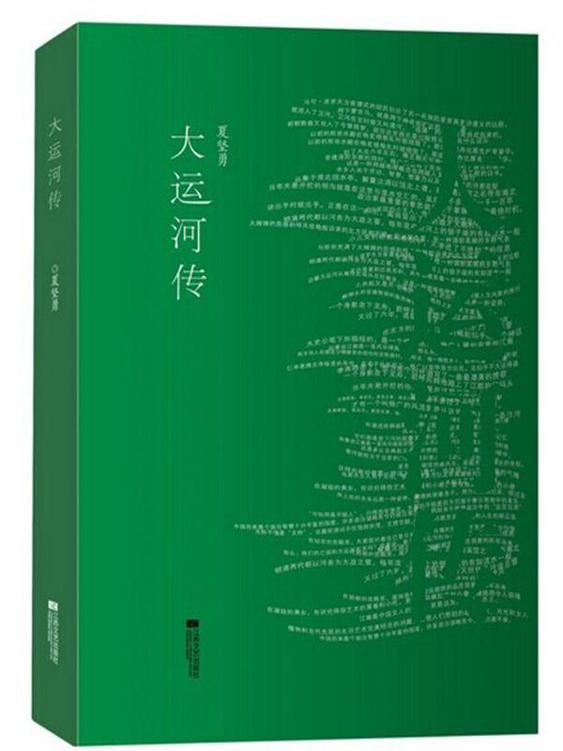大运河传-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方言是地域文化最醒目的标签,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苏州话和扬州话,也是可以体味出一点意思来的。苏州话的甜、糯、软、嗲,可称是吴语的极致,那是一种更适合于年轻女人在绣房里拉家常而不大适合男人们说剑谈兵的语言。所以有人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人说话,大抵苏州的女人们吵架相骂也有如锦瑟银筝一般好听的。扬州话就不同。扬州话也嗲,但那是一种有硬度亦有亮色的流丽,一种活泼泼的婉转,一种既适合于调情也能表现金刚怒目的雅俗共赏。我这里好有一比,如果把普通话比作英语,那么苏州话就是法语,而扬州话则有点类似于俄语。法语是一种可以显示身份的语言,它最宜出现在晚礼服、鸡尾酒和华尔兹之中。而俄语的音色中有一种很华彩的成分,听起来有一种音乐美。但如果认为苏州话更典雅,那也不见得,反倒是扬州话更富于书卷气,那几乎是从《红楼梦》和《镜花缘》等古典小说中随手可以找到的语言。不像苏州话,说的时候流转轻盈,似乎舌头也懒得动,但要写上书面就很费斟酌。至于情调,吴歌中那种欲说还休的缠绵,终也不及里下河歌谣中火辣辣的情感宣泄。
里下河的歌谣,现在流传最广的,一首是《拔根芦柴花》,一首是《杨柳青》,单看这题目,就可以知道里下河风情的主体色调:水、生命和女人。在运河与湖荡的背景上,绿杨和芦苇轻烟一般缭绕,水乡就显出了它那不胜娇娜的柔软,还有一种朦胧的湿润。女人们就生活在这种柔软与湿润之中。她们从小受用的是芦根、鲜藕、菱角和荸荠——这是真正的“水果”。她们也因此而充满了野性的生机。即使是蓬门柴扉下走出来的村姑,也都出落得水葱儿似的饱满。古运河里的过客熙来攘往,这里曾走过皇帝佬儿的龙舟,也走过数不清的名流显贵。冠盖如云,她们看得多了,因此见了什么人也不惊不乍的。提一篮水产或时鲜到集市上叫卖时,她们会锱铢必较地讨价还价,有时甚至能吐出几句很尖刻的话,但脸上的笑容却是灿烂的。她们对生活的理解是实实在在的,并没有多少风花雪月的浪漫色彩,像扬州郊外的饶五姑娘邂逅大画家郑板桥并以身相许那样的情节,她们并不奢望。里下河的沤水田,很多地方只长一熟稻子。每年秋收过后,她们就跟着家人,驾一条小船到外乡去讨生活,到了第二年开春时再回来。走不尽的天涯路,望不尽的春秋潮,唱起道情归去也,又见门前旧板桥。对于这些女人们来说,水是她们永远的生命之舟。她们在水上漂泊,觅偶,成家。生了孩子就用一根绳子拴在舵把上,让他在船板上小猫小狗似的爬。等到稍稍懂事了,就教他们摇橹把舵。那方法就有如马戏团里驯兽一般,大人在舵把前一边放一块烧饼,一边放一只麻团,叫往这边扳艄时,就吆喝一声“烧饼舵”,叫往那边扳艄时,就吆喝一声“麻团舵”。水乡的儿女,从小没有左右的概念,他们是在“烧饼舵”、“麻团舵”的吆喝中成长的。长大了,什么样的风浪都可以闯得。
里下河的女人中,还有一种被称为船娘的,她们从属于有闲者的雅趣和都市生活的金粉气。扬州瘦西湖的船娘天下闻名,她们当然都是些俊俏娘们,一个个身着青布衣裤,系着绣花围裙,头发用香油梳得溜光水滑的,发髻上插着应时的鲜花。所谓的“粗头乱服之美”,是相对于丰容盛的青楼女子而言的,其实她们浑身上下也收拾得格铮铮的。一支长竹篙指指点点,样子很写意。手腕上的银镯子在竹篙上磕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若须得使劲时,竹篙一弯,身体的曲线和竹篙的线条配合得异常匀称,有一种恰到好处的韵律和美感。轻舟拂绿柳、穿青萍,几个弯儿一转,水面便开阔了,对岸的楼台亭阁很招摇地绰约在视线里。船娘那撑船的动作又变得指指点点地很写意,一边便讲些沿途的风物掌故,对这些她们是如数家珍的,故事虽算不得新鲜,但经她们用扬州话不疾不徐地讲出来,便多了一层世俗趣味。乘船的人原也不是要听掌故,而是为了欣赏她那调头中抑扬顿挫的水色,好听得几乎可以入曲的。扬州没有杭州的皇家气派,也没有苏州的自足安闲,它那歌吹入云的风华多少有点暴发户的挥霍色彩。这里的有闲阶级是很懂得及时行乐的,无论是春风和畅还是秋雨潇潇,雇一个容貌姣好的船娘,携上几样小菜和酒,在瘦西湖上盘桓半日,都是既休闲又风雅的赏心乐事。
恣肆浩大的水,活泼健朗的女人,有如乡野歌谣般绰约多姿的风情,这就是里下河。里下河准备了所应该准备的一切,作为大运河的仪仗和排场。现在,大运河来了。
六扬州
风不大,船帆懒懒的,货又装得太狠,水面和船舷几乎平了,航船在水波中一隐一现地跃动,很有几分惊险。忽听得“哗啦”一声大响,船帆自半空翩然而落,打着赤膊的艄公一齐从船舱里弹出来,操起长长的竹篙——要过桥了。那竹篙一头抵住了艄公的腋窝,于是船舷这边便张开了两把饱满的弓:一把是艄公的身躯,他顶着竹篙在船舷上弯腰前行,从头颅到脚跟恰好成一道绷紧的弧线;一把是竹篙,在艄公的挤压下鼓起来,那映在水中的影子一扭一扭的,水珠洒在古铜色的胸脯上,勋章一般闪光。两把弓合成一股力,航船,笨重而艰涩,向着与艄公相反的方向缓缓移动。待过了桥洞,老远便听到篷索在桅杆顶端的葫芦中“呼啦呼啦”地穿行——帆又扬起来了,却仍是懒懒的,一路渐去渐远……
这是下水的航船。
上水船又是另一道风景。岸上的纤夫永远是一种姿势,微微斜侧着身子,用力向前倾过去、倾过去,但长长的纤绳却总是绷不直(间或有水鸟站在那上面,悠然自得地修啄自己的羽毛)。最精彩的是摇橹的那一帮,推艄扳艄,俯仰进退,身姿极其优美,从浑圆的胳膊到柔韧而有力的腰肢一直到虎虎势势的小腿,都显出一种雕塑般的力感。因为运动,那肌肉和皮肤也随着紧张而绷紧,闪出动人的光泽。那中间或许有一个穿小红袄的女孩,总才七八岁吧,她当然还够不上橹柄,只能抓着扳艄的棕绳,却也一样的进退有致,踏着舞步一般。那纤夫中有人耐不住寂寞,冷不丁“哥呀妹子”地吼了一声,引出同伙的一阵哄笑。这笑声多少冲淡了长途跋涉的枯燥和辛劳,也使他们僵硬的身姿稍稍伸展了几下。受了这感染,船上推艄的汉子也“欸乃”一声喊起来,随后是扳艄的一齐跟着应和。欸乃一声山水绿,航船便在这粗犷的船夫谣中一点一点地逆水上行。
这就是里运河,浩阔、畅达、洋洋大观。虽然它也和乡村里所有的河汊一样,河坡上长满了松软的茅草和盘根错节的马背筋,诱惑着你想在上面打个滚。但它那雍容坦荡的气度,那粗犷而富于韵味的船夫谣,还有那桅杆顶端优美的弧线,甚至大橹下那个着小红袄的轻盈的身姿,无不凸现着生命最原始的质感,让你为这些朴实的美丽而心醉神迷。
经历了与长江的激情碰撞和浪漫欢舞,大运河由瓜洲北上,进入里下河地区,这段运河习惯上亦被称为里运河。里运河全长近四百里,其旧道就是当年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存在大运河的全程中,它无疑是资格最老的一段。
瓜洲的话题总是与运河有关的。历史上的楼船夜雪和铁马秋风就不去说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样的凄艳故事也不去说了,光是那些缠绵凄恻的闺怨诗,就足够瓜洲品味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北方的怨妇们倚楼南望时,是把瓜洲作为地理极限的,再往南,她们就看不真切了。其实,瓜洲本身的历史要比运河晚得多。在历史上,长江口和海岸线曾经历了一个不断东移的过程,汉代辞赋家枚乘笔下的广陵潮是那样惊心动魄,以至吴客与楚太子闲话广陵潮时,竟能一下子治愈他的痼疾,可以想见当时的扬州(广陵)是临近长江口的。几千年以后,当广陵潮化作一支琵琶弹奏的古曲时,站在扬州城上,不仅长江的入海口已渺不可及,运河的入江口也南移了几十公里。而原先横亘在大江中的那片叫瓜洲的沙渚,也已经和北岸连成一片,成了运河入江口的锁航津渡,“际沧海,禁大江”的南北冲要之地。因此便有了“人到扬州老,船到瓜洲小”的说法。瓜洲有如一只巨大的漏斗,在大运河的四千里航程中,没有比它更大的漏斗了,不管你是来自吴越闽浙,还是来自江西湖广,都要从这里进入运河北上京师;而北方的河淮汴泗诸水,也要借助运河,由瓜洲进入长江。帆樯云集,艨艟连翩,这是瓜洲最寻常的景观,它永远凸现着大运河性格中宏大的一面:气势、动感和不舍昼夜的吐纳功能。
里运河从瓜洲北上,仿佛一支辉煌的乐队,一开始总是起得平平。进入苏北平原后,运河的水势渐趋平缓,但长江赋予它的激情还在,河水仍带着浑浊的风尘之色,那是掺杂了江水不安分的色素。河道平直而宽阔,水面呈现出恣肆汪洋的浩大气象。舟楫如织,却只是洋洋洒洒,并不见拥挤。船帆张得很满,有一种高瞻阔步,旁若无人的气概。两岸坦荡着一派田园风光,散散淡淡的,却又错落有致。茂林修竹间掩映着一座座茅屋,炊烟就是从那矮檐下飘散出来的。村路逶迤,有如老祖母脸上温柔而忧郁的皱纹。鸡鸣狗吠朦胧而遥远,仿佛来自童话的世界。高大的皂角树上盘踞着喜鹊窠,那是人类和其他生物和谐共处的标帜。比之于江南的精巧和妩媚,这里的景观显得疏朗多了。里运河徜徉北去,有如闲庭信步一般从容。从瓜洲到扬州,这一段的河床是松软的沙质土。长江从它的上流带来了淤泥,淤泥沉积成滩涂,化为绿洲,这种过程从大运河诞生以前就开始了,至今仍在进行着。江岸的淤积与崩塌,曾使古城瓜洲几度进退。考古学者有时在这一带挖到一艘沉船或一座古墓,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其实用不着细看,几乎可以肯定它们都是唐代以后的遗物。若是晴和日子,出瓜洲往北不久,就能望见扬州高昱寺的天中石塔。大运河的沿途有许多极富盛名的寺庙和宝塔,我不知道当初建造时,除去宗教目的,有没有导航的因素。想来也应该有的。宗教的一个大宗旨就是普度众生,所谓的禅宗四大丛林,除宁波天童寺外,其余三座——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皆坐落于古运河畔。宗教哲学与世俗需求的趋同,天上人间的接近与和谐,是宗教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过程。“光彩射楼塔,丹碧浮云端。”“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古运河畔的塔影和钟声,不仅给行吟诗人提供了灵感。对于南来北往的船夫来说,则是他们长途跋涉中的坐标和心灵深处的希冀。
过了高旻寺,扬州城里的文峰塔便遥遥在望了。
扬州的姿色在于水,这是毋庸置疑的。这里的水不同于苏州,苏州的水是细水长流的水,没有多少波澜,也不大左顾右盼的。整个苏州城都浸润在一张不动声色的水网中,很受用的样子。那水网也是棋盘一般的格局,把苏州分割成一方一方滋润的小日子。所谓小桥流水人家,那水都紧贴在人家的屋檐下,檐上的黑瓦映在水里,是冷色调的,有点浅酒轻寒或细雨兰舟的意味,是居家过日子的清静和精致,并不是故国山河的大悲凉。龚定庵诗云:“谁分苍凉归棹后,年来花草冷苏州。”他这里也说到一个“冷”字。扬州却是喜欢热闹的,大运河穿城而过,是这热闹的推波助澜。它还孕育出一个瘦西湖,那更是一个热闹去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那“春风十里”的繁华都是傍着古运河而铺展的。苏州比之于不喜张扬的水巷,运河的气派要大得多,那是很浩荡的气派。它大大咧咧地流过两岸的绿树芳草和红楼粉墙,还有那长留着玉人身影和香艳脂粉气的二十四桥,波光里也映照着明艳的时尚。扬州真是热闹,这是一座辐射着生命热力的都市,也是一座弥散着世俗气息的销金窟。任何人一到这里,就会撕去平日里遮遮掩掩的面具,变得赤裸裸地真实起来,文人的放浪形骸,商人的挥霍无度,女人的风情万种,一切都会走向极致,人性的觉醒和物欲的横流共存共荣。苏州的人事都是似曾相识的,连同那里的园林精舍和花花草草,还有小巷深处淡淡的斜阳,一切都是前朝遗物,千年不变的,却又是不褪色的。而扬州则不同,它每天都亮出新的行头。这不一定都是扬州在翻花头,而是看花头的人天天在换。扬州是农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