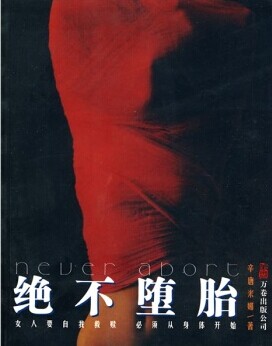决不堕胎-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见我不说,也不再多问,忽然指了指路左的地下通道。
我马上心领神会。
我们都看中了地下通道入口的那个半圆形的玻璃掩门,上面积了一层厚且干净的雪。
他先攀上苗圃,伸手拉我上来。
我们站在苗圃里,看着面前的雪,呵呵笑着,伸手在上面写字。
我写他的名字:和其。
他写我的名字:乔米。
“再写什么?”
“你猜!”他笑,伸手只顾画。
几秒后,一个笨拙的心将我们的名字牢牢地圈在里面,我愣了一下,心里腾起喜悦的火苗,喜形于色,却说不出话来。
他的手却并不停,又在龙飞凤舞地写着字,仔细来看,却是:友,谊,天,长,地,久。
他抬起头看我时,看到的是我的笑脸,没有看到前一秒我怅然失落的表情。
“要不要再写什么?”我问,强笑。
“写我们最近比较关注的人的名字吧!”他提议。
我想了想,在和其的名字上写下两个字:“错错”
我希望和其会将我的名字重复写一遍,但是这个念头一闪便过去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他正在写:卢小雅。
那个雅字笔画相当多,占了很大的位置,正好将乔字压住。
我在心里暗暗叹气,从苗圃上跳了下来。站在街上,脚心一阵麻,幸好和其的手及时伸来,要不然差点摔倒。他扶着我,有些责怪:“这么大的人,怎么这么不小心。”
他离我那么近,我可以吸到他呼出的一团白色的气,但是我却感觉他离我是那么远,不但遥不可即而且隔着重重白雾,让人望而生畏。
我跺跺脚,笑:“没什么!”
仍然将手放进他口袋里,与他一起走。
不知不觉中,天已暗,路灯通明。路灯昏黄的灯光将夜空染成了橘红色,连雪都是橘红色。橘色,是卢小雅的颜色。我无奈地想。
“你还难过吗?”他忽然问我。
我吓了一跳,以为他看出了我的心事,慌忙摇头。
“那就好,别为那些事情烦,你是名牌,不用和那些鱼目混珠的人计较。”他宽慰地说。
我才明白他说的不是关于情感的事情,松了口气,心却仍然很沉。
“是不是到我家喝杯咖啡?”我发现我们不知不觉中走到了我家附近,征求他意见。
他点头:“好。”
进了房间,他便向对面的窗口看,我站在门口,大衣还拿在手上:“要不要我帮你叫她!”
他居然腼腆地笑了起来:“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写稿。”
“可能没有,这几天错错来了,她白天陪错错玩,晚上错错在我家睡觉时她再写稿。”
“那她什么时候休息?”和其的关心溢于言表。
“你问她自己好了。”我没好气。
给卢小雅打电话,错错接的电话,听是我的声音马上雀跃:“乔米妈妈,你回来了?”
“是的,今天乖不乖?”
“我有不乖过吗?”
“小雅在不在?”
“她在洗澡!”
“要不要到我这来?”
“好的呀,我这就来。”
“等一下,你告诉小雅,和其来了,让她也过来。”
“谁是和其?”
“乔米妈妈的朋友!”
几分钟后错错敲门,我开门将她抱进房里,将她的鞋子脱掉,从沙发下取出一双崭新的童拖鞋给她换上。
“喜欢这双鞋子吗?”前几天错错来我家都只好穿大人的拖鞋,走路一跌一跌让人看着不放心,所以我专门去买了童鞋,让她温暖舒服。
她在我脸上亲了一下,以示满意。
她看着和其,伸手去摸摸他的鼻子:“他的鼻子很好看。”
“他帅不帅?”我逗她。
她摇头:“不帅,我喜欢仔仔!”
仔仔是现在正在走红的一个影视演员,在我们这些成年女人眼里,他显得过分天真和奶油,但是在错错眼里,那便是天下最帅的男生。
和其可能是生平第一次听女孩子讲他不帅,他摸摸鼻子,苦笑。
“错错很可爱。”他讨好错错。
错错向我怀里靠,表情不以为然:“每个人都这样说。”
卢小雅的孩子就是卢小雅的孩子,说起话来都一套一套的。
卢小雅打来电话:“你们到我家来吧,我刚洗了澡,出门怕会感冒。”
“我还有图要做。”我拒绝。
“那让和其过来吧。”
我看着和其:“她让你一个人过去,你去不去?”
和其想都不用想:“好的,告诉她我很荣幸被邀请。”
他走后,我紧张地看着窗外,伸手向茶几上摸烟。
错错将烟推给我,帮我擦燃火柴,我拍拍她的手表示感谢。
“你怎么不去工作?”她依在我身边问。
“我坐一会儿便去。”
“我在这儿会影响你吧,要不我先回去,一会儿让和其再陪我过来。”小人精毫无心计地说,但是她慧黠的眼睛仿佛告诉我:乔米妈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和其很快便从卢小雅家过来了,他说错错睡觉了,卢小雅要写稿,所以他便早早告辞。
我看着他,似笑非笑:“你喜欢卢小雅?”
他仿佛有些紧张,笑得很刻意,他说:“我是喜欢她,不过,我也喜欢你啊,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喜欢你们两个。”
这次书市在郑州,社里安排了一些人参加,莫名其妙地将我也算在内。
社长看我一脸不开心,温和地问我:“可以回家,为什么不高兴?”
我的家在郑州,他安排我去参加书市,想必是专门为我制造一个回家的机会,但是他不知道,我三年不回家,并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因为逃避。想忘记那份让我挣扎了四年的感情,却因为无法忘记,所以不得不选择逃避。
打电话告诉父亲,父亲居然激动得叫了起来,喊着母亲的名字让她也来听电话,他说:“小米要回家了。”
小米要回家了。
我的眼泪差点哗哗地流。
“回来过年吗?”妈妈抢过话筒问。
“可能不会。我是公事去郑州,顺便回家看看。”我轻描淡写地说出“顺便”两个字,虽然现在我想家想得痛苦,但在家人面前,我仍然要掩饰对家的思念与向往。
思念是等长的,如果一方过于绵长,另一方势必也会延伸。也许我的坚硬,能削弱他们对我的牵挂。我这样想。
我向和其告别,他没有问我会出差几天,只是说:“郑州天气冷,多带些衣服。回去多陪陪老人。”
错错有些想流泪的样子,可怜兮兮地问我:“乔米妈妈,你走了,谁陪我玩?也许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回外婆家了。”
我亲吻她的小脸蛋,向她保证我会快快地回来,并答应给她带一只大大的泰迪熊。
卢小雅正在写作,她从电脑前抬起头来看我,她说:“快去快回,我会想你。”
她的表情很认真,让我有些于心不安,看样子,她是真心将我当朋友,而我却因为和其对她的好感,在潜意识里一直将她当做我的敌人。
出了站台,看见父亲的身影,我开心地几乎要跳了起来,向他跑了几步,到他身边时,才发现自己已不能像小时候那样跳进他的怀里,吻他的脸,被他用胡子扎得乱扭。
我说:“都说你不用来接我的。”
他专注地看我,拍我身上的雪花:“住酒店里哪儿有住家里舒服!”
家!
这个字眼真温暖。
告别了同事,我跟在爸爸的身后坐上车。
看他的侧面,发现耳边的头发已斑白,像柿饼表皮洒上的一层面粉,触目惊心的白。
“郑州变化大吗?”他问我。
我忙转头看窗外,眼睛有些热,我揉揉眼,声音尽量自然:“和三年前没有什么区别!”
长沙与郑州离得并不远,而我居然三年没有回家。如果换作我,苦心养育女儿的结果是因为爱情失败所以连亲情也一并忘记,我会不会还会像父亲疼爱我这样疼爱我的女儿?
妈妈听到车响便迎了出来,她看着我,没有抱怨,没有责难,只是挑剔着皱眉:“你瘦得不像话,连胸都快没有了。”
我笑了起来,拥抱她。原来害怕回家后面对父母会有些难堪,却发现,父母永远是站在身边无私爱着我的人,就算我犯一千次错误,他们也会一千零一次地原谅,甚至会根本忘记有过的伤害。
家里多了一只狗,它不认识我,警惕地在我身边嗅来嗅去。
妈妈说:“它是大卫。儿子,来,她是乔米!”
看她亲昵地抚摸大卫,我鼻头一酸,感觉自己连一只狗都不如,它听见妈妈的召唤还能摇头摆尾,逗她开心,而我却只会给她带来不快与不安。
妈妈帮我将箱子里衣物拿出来挂好,她看我的胸罩,又皱眉:“你看,五年前你还穿三十六a,现在成了三十四a了,每天要多喝牛奶,丰乳。”
我从背后抱住她,将头埋在她的头发里,闻着属于她的香味,心里安定温暖,仿佛回到了在她怀里安然入梦的儿时。
“还有二十天就新年了。”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灯光照在她低垂的脸庞上,我看到了一些细微的纹路,像精美的瓷器出现了细碎的裂纹,不易觉察,觉察之后便满眼都是那些纹路,让人心里发堵。
我内疚地抬不起头,我说:“妈妈,对不起,书市结束后,我还得回长沙,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回来过年。”
“没有什么,我和你爸也习惯了。孩子大了总有自己的天地,天天和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一起会无趣死的。什么时候带个人回来?”她自己给自己找托词,轻描淡写地问。
“我带个孩子回来好不好?”我忽然说。
她将我从身上拉开,瞪我:“如果要带孩子的话就将她爸也带回来,如果你只带个孩子,我会将你们两个都关在外面。”
开明如我妈妈尚不能接受未婚妈妈,卢小雅的父母不知道是何等神圣,能接受并抚养错错这么多年。
想到卢小雅,我又想起了和其,他应该会让我妈妈非常欢心。妈妈喜欢一切美的东西,漂亮的物什,漂亮的男人。记得小的时候,她就开玩笑:“乔米,将来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男人做老公,哪怕他一无所有,就当他是花瓶,放在家里做摆设,看着也舒服。”
和其,他会不会和卢小雅在一起?我心一紧,忍不住给他打电话。
“和其?”
“你到了?一路还好吧。”
听到他的声音,我反而吞吐起来,故做释怀地笑:“还好,睡了一夜。现在回到家里了,看到父母,很开心。”
“那就好,与父母好好聚聚。”
“嗯!”
两人都沉默起来。
“乔米?”
“怎么?”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终于问我的归期,这句话像一道闯进黑暗的阳光,让我顿感明朗起来,忍不住微笑:“我刚走就问我什么时候回,不会这么离不开我吧。”
他也笑,然后说:“我们都在等你回来。”
我们?除了他还有谁?卢小雅?
卢小雅像一片浓云,将我又笼进了阴霾之中。
挂了电话,靠在枕头上想着心事。
妈妈坐在我身边,摸我的脸:“在恋爱?”
“常恋常失,但是志气不改,打算常失常恋。”我强笑。
她哈哈笑:“我的女儿就应该这样。给我讲讲这个男孩子!”
我叹气:“没有什么好讲的,如果有缘分,我会将他带回家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卫真找你多次。”她说。
卫真!这个名字唤起了我几乎忘怀的伤痛。那个成熟温柔的男人,那个寄托了我所有青春梦幻的男人,那个让我义无反顾离开郑州逃到外省的男人。
我还记得我上火车的那一天,爸爸送我到站台,我四处顾盼他的身影,可是只等来了他的电话。
他说:“好运!”
我说:“告诉我你没有爱过我?”
他想了想,说:“我不能说那个字,我只能说我喜欢你。”
我挂了电话,将手机卡从手机里拿出来,从车窗里扔了出去。我爱了他四年,他是我的老师,我的爱人,我们热吻,我们做爱,但是四年来他一直不说他爱我。
到了外省,手机号一定得换,我爱的男人也一定得换。我在火车上发誓:我会爱上第一个对我说我爱你的男人。所以,当我听到鲁北说“我爱你”的时候,在心底发出一声低低的叹息,义无反顾地投进他的怀里。
妈妈看我出神,同情地拍拍我:“给他打一个电话吧,这三年,他身边一直没有别的女人。”
睡了几个小时,我起床梳洗。
爸爸给我点了一支烟,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你的手指有些黄了,以后记着用烟嘴吧。”他笑。
我感激地看着他,很想与他聊点什么,但是三年来头绪太多,一时无从下口。我借口去书市看看我们社的展厅,拎着包在他的目光中走出门去。
我去的方向是金博大商场,我知道那儿有一个泰迪熊的专柜。我答应了要给错错买一只泰迪熊。
一只穿粉红色棉袄的泰迪熊吸引了我,我让小姐将那只熊给我。
小姐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