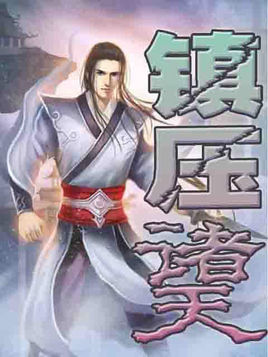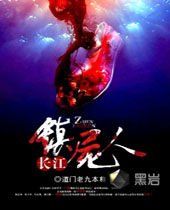枫叶镇-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伤你,才让你那么容易跑了。”
我的心像被某种锐器扎了一下,疼疼的感觉强烈不堪。我艰难地继续问:“那么你呢,会不会轻易伤害别人?”男孩摇了摇头,我就问他,“那为什么要给我们浇汽油呢,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害死人的?”
“我不想伤你,虽然你很讨厌。我爸爸恨那个男的,爸爸说,他是个杀人魔,他犯下的罪迟早要连累到我们。我爸爸对我说,别人没有伤你,你就一定不要伤他。”
我的喉咙干涩,有点难受。思考一下,自己确实挺难缠、蛮令人讨厌的,如果我乖乖地留在禁闭室,哪里也不去,兴许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老良或许也不会死。
至于男孩所说的“那个男的”,肯定是指铁锤男了。男孩很乖,说的都是大人教的话;男孩很听话,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悲伤地拍了拍他的肩,就这样与他说再见。我愣愣地看着他跑开,痛苦地想到,这个男孩知道他爸爸的死讯后,会有多么痛苦。不知道老良有没有教他,怎么面对亲人的生死。
老良果真是个好人,好人此刻正悲哀地躺在街道的某处,冰凉的身体甚至感觉不到晨光的普照。
好了,烈火就快要燃尽,拿回那把钥匙,解开这些束缚,是不是可以离开这座小镇?于是我站起身,挪动着身体走向铁锤男的尸骨,带着一脸冒犯的歉意,将他的那把钥匙拿起。解开了脚镣的束缚,我又伸手拿出水果刀,灵巧地划开捆绑着双手的绳索。最后我转过身,对李若蓝他们说:“我们可以走了吗?”
李若蓝脸上还有一些情绪,那全是对我的不满,怪我刚才太偏激地求死。不过很快她的不开心就烟消云散了,带着喜悦之情,微笑说道:“事情大概已经圆满,我们是该走了。”而王小井,此刻的神色却变得特别,他紧锁眉头,满脸的不安与恍惚,他朝我们说:“不,事情还没有结束。”然后他便看见我们的疑惑表情,他吃力地解释:“刚才那个女人,是我的母亲,不过现在已经不是了,那样的亲情最终的结局不过是一刀两断。”他咬了咬牙,很肯定地说道:“我决定了,我要亲手杀了她。”
他的声音在整个教堂飘荡,他所表达的让我恍惚。我不禁想起之前所见的母亲雕塑,她慈爱的眼神呵护着婴儿吃乳,自己却残缺了右手。母亲对孩子的爱能有多深,哪个孩子又忍心亲手屠戮他的母亲呢,她究竟犯了怎样不可饶恕的罪过。我沉静地说:“走吧,趁我们还能逃走的时候。”李若蓝的表情也不自然,她却是没说话,显然是被王小井的想法惊吓到了,她正在努力承受。
我像对待一位朋友一样,去拉王小井的胳膊,试图将他拉走,“走,我们上车。不管犯了什么错,她都有生存的权利。”但他没有答应,刚开过火的□□再次拿起,这次却是指着我。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李若蓝大叫,她气呼呼地走过来,开始谴责我们,“刚才是你不走,宁愿被锤子砸、被火烧,都傻呆呆地不肯走;现在是你,王小井,刘阳要走了你又不想走。我凭什么看你们在这儿闹情绪呀,你们自己慢慢折腾吧,我才懒得管,我这就走!”说完李若蓝将手里的枪随意扔在我手上,真的上了大街。
“你们谁都不许走!”王小井身子后退几步,站在教堂那处,枪口朝着我和李若蓝这边。李若蓝早已诧异地回过头,定定地站在那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低声问王小井:“你究竟想做什么?”
“李若蓝你一定很奇怪,从你关到禁闭室开始,那几天我几乎没和你谈过自己,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是怎么进去的?”李若蓝点了点头。王小井又望向我,“不用说,你这种满脑子想法的人,一定也很想知道。”我略微思忖一番,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他叹了口气,终于决定不再隐瞒自己的故事,淡淡说道:“好吧,现在我就讲给你们听,听完之后,你们是去是留,我都不会强求。”
于是,我们一行三人,重新走进此刻冷清的教堂,坐在宽敞的座位上,某人准备叙述,某两个人打算聆听。此刻气氛是从未有的严肃与认真,我预感到,整件事情的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二十二、回忆
“我是枫叶镇的人,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是再美好不过的小镇。后来我去C市读书,大学毕业后在那边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原以为自己的人生也就如此,直到我收到父亲逝世的消息……”王小井顿了顿,他此刻一脸哀伤,眼角有不易察觉的湿润。
他继续说:“那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回到了枫叶镇,带着失去至亲的悲痛,回去见我的母亲。我乘坐的出租车开进这里,却发现曾经热闹的地方变得荒凉,街上几乎没什么行人,即便是有,也不过是行尸走肉。这把出租车司机吓坏了,他甚至是直接把我丢在街道上,连车钱都不收,就拐弯一溜烟儿跑了。
我的心情很糟糕,带着恍惚的陌生感胡乱行走,路过教堂,听到里面人声鼎沸,我就莫名其妙地推了进去。你猜这时候我看到什么……你们猜猜看……”他情绪再次失控,我轻拍他的肩膀,那原本坚实的身子骨此刻柔弱无力。而旁侧,李若蓝虽是在低头聆听,却也在悄悄抽泣。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那个主讲台上,”他指着眼前的主讲台,此时无人宣讲,显得特别安谧。“我的母亲就像今天这样,郑重其事地站在上面,拿着稿纸大声宣读,她说我父亲生前犯下罪孽滔天,上帝英明给以责罚,终于病倒家中,今日神明在上,在此焚烧罪人肉体,以儆效尤,希望众生牢记,切忌效仿。我的父亲就躺在过道的红地毯上,他身子瘦弱不堪,可怜地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四周的那些人、那些混蛋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冷漠地看着我的父亲,甚至不愿帮我父亲合上眼睛。我的父亲已经死了,我的母亲却这样对待他,她是个恶魔,她拿着火把,走到我父亲身边,亲手将他焚化。我,你们知道我当时在干什么吗?我口干舌燥地站在教堂大门外,冷静得不能再冷静了。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我他妈就那么懦弱地站在那里,看着我可怜的父亲死了又死。我甚至不愿意和我母亲争辩一句,我转过身跌跌撞撞地跑,拼命地跑,好像下一个被烧掉的人就是我。我所做的这一切,永远不会得到父亲的原谅,绝对不会!”教堂上方的大钟响起,总共“咚”了七下,如一声声悠远的悲鸣,震彻人心。
“我躲在家里,钻进卧室的被窝里,哪里都不敢去。我以为自己长大了,却还是那么年幼,我不懂事,甚至连父亲的不幸都不敢面对。我就这么和母亲躲着,从那天起,我们就像陌生人一样,在一座屋子里面,却隔绝在两个世界。你无法体会到这种感觉,生我养我的母亲就像另外一个人,巫婆或者恶魔,她就在附近,一次次地从我身边走过,她的衣角能触碰到我的手,她甚至不经意地对我微笑,我的心却冰冷得要死。”
“我想过死,每天晚上我都做噩梦,梦见我的母亲一次次地把我父亲点燃,像点根火柴那么轻易,梦见我不认识的母亲对我说,‘孩子,过来,天气这么冷,来这边取取暖吧。’我自己呢,我被那场景吓醒了,身子缩在墙角瑟瑟发抖,我不敢开灯,开灯只会看见焚烧父亲的熊熊火焰,我又怕漆黑,我的母亲随时会从黑暗中走出来,对我微笑,给我端来一碗冷粥。我怕看到任何一切,于是就想一死了之。我就用脑袋撞墙,歪着脖子朝冰凉的墙壁撞啊撞啊,终于撞得脑袋混乱一片,好不容易流血了,我的母亲却大力地把房门推开,拖着我知觉错乱的身体,把我拖出房子,拉到镇上的诊所——那间诊所你们肯定不知道,它就在警局的附近,那里充满死人的味道,那个庸医一定害死了不少人——我甚至怀疑我的父亲就是被他害死的,不,一定是他和我母亲联手干的。”
“我母亲力气很大,她就那么拽着拉着把我弄了过去,我的腿脚、我的后背被路面磨蹭得满是伤痕。庸医粗鲁地把我抱上病床,给所有的伤口胡乱滴一大堆药水。我的母亲就在旁边和他聊天,他们聊得很开心,甚至还会无所顾忌地搂搂抱抱,她和他肯定有一腿,我恨死他们了。我的母亲高兴地看着庸医给我脑袋缠上粗麻布,缠得像粽子的时候他们才满意,两个人一边说着肮脏的笑话一边抬我回家。我没有死成,也不想死了,我发誓一定要杀了庸医,为我父亲报仇。”
“我一直不知道我母亲每天做些什么,她很少呆在家里,也很少有谁来敲我家的门。但那些人都愿意每天在我家门口等着她出来,然后一起走掉,几乎每天都是,他们就像忠心耿耿的狗。时间过得很慢,但还是到了春节。大年三十那一天我印象深刻,镇中心的路口在举行火葬,我的母亲硬是把我拉到那里,逼着我去观看。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被绑在临时搭起的十字架上,下面堆满了木柴,四周占满了观众。我不知道我的老师究竟犯了什么错,□□着身体,头发被扯得乱糟糟的,她的眼睛悲哀地看着我们,没有任何情绪。”
“开始行刑了,有人首当其冲,把木柴给点燃了,老师的身体迅速在烈火中绽放,她说话了,她撕心裂肺地叫喊,她说:‘血腥的贪婪迟早会受到惩罚。’我回家了,母亲没有拦我,我冷漠地步行回家。我知道了,母亲每天都在杀人,她的手上沾满血腥;我知道,她是个有欲望的女人,为了某种目的,正在不择手段。”
“我就是那样过完春节的,没有烟花爆竹,没有亲戚朋友,更没有喜庆感觉。打那天起,我决定为无辜的人报仇,决定亲手杀了我母亲。我就躲在我的房间里面,拿着厨房里的切菜刀,伺机行动。那天家里面安静极了,我的脸贴在门上面,耐心地等她的脚步声。很晚,很晚的时候她才回来,她用钥匙打开了门,沉重的高跟鞋将地板踩得咯咯作响,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了,打开一瓶红酒打算享用。就是这时候我拉开门朝她冲过去的,拿着那把刀劈向她的脑袋,她的红酒惊慌失措地掉地板上,砸了一地碎片,殷红的液体四处流窜。她简直就是个恶鬼,她阴森森的目光冷冷地看着我,额头毫不躲闪地对着我的切菜刀。她甚至没说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击垮了我。我不敢杀她,真的不敢,真的……”
☆、二十三、精神病院
“王小井!”我疼惜地叫他一声,此刻的他表情混乱,身子不停地摇晃。我尽量确保平心静气,对他说道:“王小井,要不我们不谈这些了,我们现在不走了,留下来陪你。这样好吗?”真的,他这样讲,不仅会重新把伤痛再经受一遍,而且我们也徘徊在悲伤与恐惧的边缘。我宁愿他停下来,由我们亲手结束这一切的根源。
“不,千万别拦我,你们不听完,绝不会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鬼地方!”王小井稍微平静下来,他摇摇头,嘴角浮现勉强的笑,“好吧,我尽量说得简短一点,嗯,我尽量。”他悠悠地叹了一口气,打算再次融入不堪的回忆。
“那件事情之后,她做出一个决定,和几个帮手把我五花大绑,扭送到C市的一家精神病院。我猜那家医院和他们是一条船上的,真的,我发誓!那里的院长甚至没问我有什么毛病就将我安排到506房间。那个残忍的女人走了,她的头发发白,所做的一切却连坚实的年轻人都不敢下手,她从506房间走出去,复杂的脑袋甚至没有转回来看我一眼。从那一刻开始,我彻底否认她是我母亲,她不过是个女巫,不过是住在我所在的屋子,不过是强行将我驱逐到这里。”
“精神病院里所有的房间就像监狱,没有铁栏,但它拥有仅有一个门的封闭空间,除了苍白的地板和墙、和天花板,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无所谓,我不在乎,晚上的时候我就躲在角落里,沉闷的空气反而令我安静。我就这样住了下来——除了每天吃饭时间,能在餐厅见识很多奇怪的人。他们有的喜欢将饭盒扣在脸上,然后一点一点将饭菜吞掉;有的站在餐桌上跳舞,结果身子搭在吊扇上面摇曳个不停;也有的……有的蹲在我的座位后面亲我的屁股——但我看来他们都很正常,比枫叶镇的人要正常多了。我和他们聊天,虽然大多是自己在自言自语,我说我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来给你们出个脑筋急转弯。我说蛤螽哈’一下之后是什么,他们说是‘喽’,我兴高采烈地笑了,确实高兴得要死,我说错了错了,‘哈’之后是‘嘛’!哈哈,你们说他们笨不笨……”